

1978年,陈翰伯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室。

1961年初秋,陈翰伯和家人在北海公园。
两天前,中国最古老的现代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迎来了一批皓首老人,他们当中有来自新华社的新闻工作者,也有来自不同出版社的一批老出版人。老人们聚在一起,是为了陈翰伯,一位似乎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出版家。
其实陈翰伯的百年诞辰,是在今年的3月14日,但出版界的纪念大会,却到10月16日才举办。迟到的原因不好揣测,但这小小的细节,确实说明人们于陈翰伯这个名字,多多少少还是觉得陌生的。作为一位出版人,这大概也是另一种成功,那么多人在读他主持出的书,却少有人知道他是谁。
青春办报,皓首出书
陈翰伯,他到底是谁呢?先抄录他晚年的自叙小传吧。
“我祖籍江苏苏州,于1914年3月出生于天津。在天津上完小学、中学,在高中二年级‘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参加了一些天津党的外围工作。1932年我到北平,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冬,在党的领导下,我和几个同学共同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1936年2月,我在燕大入党,后来在党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之职。1936年夏毕业后到上海。在全国学联参加过短期筹备工作。1936年11月到西安,在东北军张学良将军所办《西京民报》任编辑,后任总编辑。1937年3月到杨虎城将军所办《西北文化日报》任副刊编辑、国际新闻编辑,并担任社论撰写工作。1937年5月,陪同美国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前往延安约1个月。1939年春在成都《新民报》专管写社论工作。后在我党和民主各党派合办的《全民通讯社》主持发稿工作。1942年在重庆《时事新报》任新闻版编辑。1945年任重庆《新民晚报》副总编辑。1947年在上海,与几个同志创办党领导的公开发行的、群众性报纸《联合晚报》,我任总编辑。
全国解放以后,我在新华通讯社总社任编委,并兼国际新闻部主任,后来党把我从新华通讯社总社调到新闻出版总署,具体负责创办北京新闻学校,任副校长。1954年,新闻学校工作结束,我被调到中宣部,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具体工作是《学习》杂志责任编委。1958年春调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十年动乱以后,我担任过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
综上所述,我是青春办报,皓首出书,接触面虽较广,于学问上毫无专长,在事业上也无建树。聊以自慰的是,做了一枚对人民有点用处的螺丝钉。
1980年秋患病,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我已告老,但尚未还乡,现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看看摊子。入党那年,我22岁,是一匹驹。而今垂垂老矣,但愿还能作一匹骥吧。”
“青春办报,皓首出书”,这份自叙,谈青春多,谈皓首少。但短短几句话里,却有说不尽的惊心动魄处。陈翰伯从1958年开始的出版人经历,后来对汉语世界的阅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者可以说,在他手里,一些关于读书的基础建设工作,最终得以完成。
从学术书到辞书
陈翰伯1958年到商务印书馆主持工作,这段经历,他曾有一篇《从小读者到老编辑》中说道,“我非常羡慕金灿然,中华书局搞成功了,我这里得到的支持较少,工作比较困难”。
有难处的情况下,陈翰伯的主意是读四史:世界通史、西方哲学史、经济学说史、政治思想史。后来他在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基本上便以此为纲,列出数百种书目。但其中有些是近现代的资产阶级著作,就不无风险了。“我们在两个方面做点“保险”工作,一是在译本前加上批判性序言,一是把好发行关,采取自办发行或由书店内部发行。”后来读者的记忆当中,常常有关于“灰皮书,黄皮书”的激动书写,但对当时印这些书的出版机构来说,压力其实还是相当大的。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后来成了学者的标配。就影响与赓续而言,陈翰伯当年组织定下的书目,其实绵延至今,比如前几年才翻译出版的《琉璃宫史》便出自最早的规划,而蒙森的《罗马史》,则到2014年才出齐。
汉译名著之外,和陈翰伯有关的第二个项目,是辞书的出版。辞书人人都要用,但却又不会投之以太多的注意力,是真正最基础的文化建设。在陈翰伯百年诞辰纪念会上,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82岁的林尔蔚先生说,他去国外看最专业的辞书出版社,涉及的语种可能也不如商务印书馆多,在这方面,商务印书馆可能在全球都独一无二,而奠定这一基础的,则是陈翰伯。
陈翰伯推动编纂修订了几部大型的辞书,《现代汉语词典》是人人都要用的,自不必说,《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则代表了汉语的底蕴。这几部大型辞书,分别由陈原、许力以等出版家主持其事,其中《汉语大词典》,则由陈翰伯本人主抓,于1976年在没有主编的情况下匆匆上马。这部辞书到1994年编成,陈翰伯本人都已经辞世六年了。
从少儿书到《读书》
在陈翰伯诞辰百年纪念座谈会上,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宋木文发言,引用出版界对陈翰伯的评价,“没做大官,却做了大事”。陈翰伯曾经在“文革”后主持过出版工作,职务是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至于他做的大事,宋木文着重提及“全面推进了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为出版工作在新时期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的破冰,可能是从少儿出版领域开始的。“1978年10月,陈翰伯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全国少儿出版会议,以解放思想、批判极左、勇闯禁区、繁荣出版为指导,制定全国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推动我国新时期少儿读物出现繁花似锦的新局面。”(据宋木文发言整理)如今四十来岁的读者,很有可能能回忆起小时候读到的《娃娃画报》之类杂志,不要小看那一格一格的连环画,它代表的是阅读生活的一种可能性。此后,陈翰伯又推动突破了地方出版社的地域限制,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调动了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特别为后人称道的,则是他在陈原,范用的协助下,领导创办了《读书》杂志。
早在1970年,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时,就曾经设想要办一本读书杂志。八年后,书禁初开,陈翰伯主持出版事业,范用提出由他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主办《读书》杂志。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原名为“打破读书的禁区”,后由范用改为“读书无禁区”。在叫好声中,也引起了数不清的质疑。
1981年4月,《读书》两周年,时任《读书》主编沈昌文向陈翰伯报告了“读书无禁区”发表后的反应,希望他能就此文表个态。于是,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砭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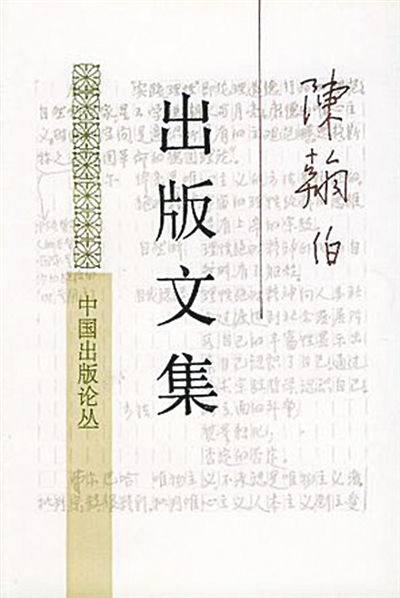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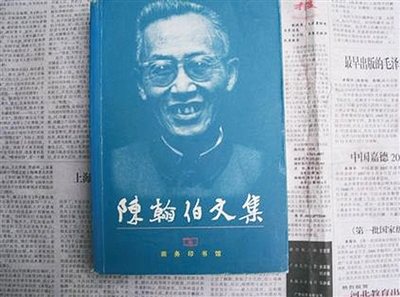

1981年,陈翰伯与胡愈之等出版界老同志。
他所开始的,并未结束
陈翰伯曾经有一段文字,谈政治与出版的关系。“政治宣传可以舆论一律,学术理论著作则要百家争鸣,而不能舆论一律。多年来,由于忽视或违背书籍的特点,在出版与政治的关系上造成了混乱。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出发,陈翰伯推动了出版的革新,冯亦代曾评价他“把中国的出版业从濒临衰境,挽救了过来”。
在陈翰伯诞辰百年座谈会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高度评价这位出版前辈,“早在1979年,他就注意到了出版体制问题,并提倡载入宪法的出版自由和依法管理,组织了出版法的草拟,并整理、修订了包括《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稿酬制度等在内出版工作各项规章,发出了新闻出版改革的先声。”如今几十年过去,“陈翰伯同志生前念念不忘的出书难、图书品种少,人才少、学术质量低,印刷慢、出版周期长,发行门店少、排队买新书等等问题,已经在改革发展中迎刃而解。”(据柳斌杰发言)但以书本身的文化价值为依归,让出版人做好出版这件事,依然是出版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本文所引用发言稿由商务印书馆据陈翰伯百年诞辰研讨会现场整理)
■ 记者手记
当“中国好编辑”遇上陈翰伯
在“陈翰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桂晓风发言,称陈翰伯是编辑的榜样,并叹息当下的出版编辑资格考试,没能在确立编辑榜样方面下工夫。巧得很,就在这个纪念座谈会之前一周,由百道网发起,凤凰传媒投入百万元资助的“中国好编辑”评选启动,出版界正在开始寻找自己的“当代英雄”。
“中国好编辑”的评选背景,是电子大潮对传统出版的冲击,是人们阅读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的大转变。面对这样的变局,出版业也有种种应对的创举,但在很多出版人那里,还是面对变局的惶恐与迷惘,“未来的读者还需要书吗,还需要我们吗,还需要一个出版行业吗?”
问题看上去现实而尖锐,但很可能,这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伪问题罢了。
上海世纪集团副总裁施宏俊有一个观点很值得出版人省思,“现在的问题不是未来的读者要不要书,而是现在的出版人有没有把书做好”。很可能,传统出版行业最大的对手,根本不是电子生活的冲击,而是未能真正实现自己应有的价值:把书出好。如此看来,传统出版的转型,也并不是简单地去搞新媒体或者电子化,而是要真正去做到价值出版——从传统出版到价值出版,这其中核心的生产力,当然就是编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好编辑”的评选不仅仅是要确立榜样,它所指向的,更是一个行业的自省与革新。
既然说到价值出版,就不得不提前代出版家的努力。以陈翰伯为例,出版界称他“大德无言”,因为在新闻出版界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以价值论,当代中国的读者们,却也不得不承认受惠于他的努力——成体系的辞书,成体系的西方思想名著译介,还有对读书禁区的突破,都堪称壮举。不夸张地说,陈翰伯实现了一个好编辑,一个出版人可能得到的最大价值,默默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因为现实条件的不同,今日的编辑,即便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大概也很难像陈翰伯那样,成为时代精神的幕后影响者了。毕竟,陈翰伯不仅仅是出版家,他更在一个时期成为出版业的领导,对各种资源的调动统合之力,非他人可比。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位“皓首出书人”对文化价值的发现之力与传布之忱,这也是在今天成为一个好编辑最需要的内在基础。因为电子化冲击而惶惑着的出版人,其实很难体会陈翰伯那代出版人的艰辛。这里不妨引用一段陈翰伯写于1968年的认罪材料(转引自沈昌文演讲录音),看看对于出书这件事,需要怎样的坚持。
“我1959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想把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作为研究项目,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65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1962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
人的际遇不同,行业的命运也在变迁,每个人都可能遇上好时代,也可能遇上坏时代,但所谓价值,却总在那里。陈翰伯和他的同代人,遇上的是百废待兴却又密不通风的时代,他们建立了体系,打破了壁垒,完成了可能的历史命题。而今日的“中国好编辑”们,遇上的是转型的时代,创新的时代,与其叹息,不如努力。中国正在迎来文化基础教育背景最好的一代读者,出书的人,有什么理由恐慌呢。请相信,只要你能做出好书,就一定会有人读。
■ 链接
陈翰伯谈编辑
上世纪40年代我就知道有个进步的国际问题评论家叫梅碧华,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身材魁伟的陈翰伯。
到80年代初,我有幸在他领导下编杂志。刚到编辑部不久,便见到他的一个亲笔意见,文如下:
这里无甚高论,仅供改进文风参考。
一、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
二、不要穿靴、戴帽。
说明:戴帽指文章第一段必须说上“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如何……”。穿靴指文章最末一段必须说上“为什么什么而奋斗”、“……而贡献力量”。当然这不是说不要宣传党的中心任务,而是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全文中去。
三、不要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不要用“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朱委员长”;不要用“英明的领袖华主席”。
四、有时用“毛主席”,有时用“毛泽东同志”。注释一律用“毛泽东”。
五、制作大小标题要下点工夫。不要用“友谊传千里”、“千里传友情”之类的看不出内容的标题。
六、引文不要太多。只在最必要时使用引文。有时可用作者自己的语言概括式地叙述。
七、尽量不用“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之类的话头,有时可用少量第一人称。
八、可以引用当代人的文章,并注明出处。此类注释可以和有关经典作家的注释依次排列。
九、署名要像个署名,真名、笔名都可以。不要用“四人帮”横行时期令人讨厌的谐音式署名。不要用长而又长的机关署名、不要用“大批判组”。不要用“××××编写组”。
十、行文中说“一二人”可以,“十一二人”、“一二百人”也还可以。但千万不要说“一两万人”这一类空话。
十一、不要在目录上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这十一条,现在看来似乎稀松平常,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却是了不起的大事,应当说条条都是针对“文革”中盛行一时的风气而言。例如第八条,在当年,如果注释的上一条是陈布雷的文字,下一条引了毛泽东,两条注文出处(仅仅是出处)先后并列,这就可以被人上纲为混淆敌我,立场错误(尽管在内文的叙述中敌我立场是很鲜明的)。可以说,这也是《读书》杂志转变当时文风时尚的第一个文件。 □沈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