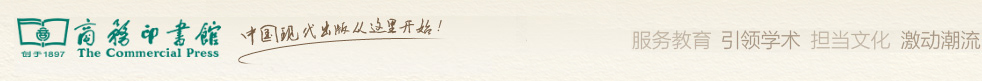
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 系列讲座(第一季)第三讲
时 间:2012年7月7日
主讲人:陈智超,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嫡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今天很高兴能来到这个地方和大家进行交流。我是陈垣先生的孙子,在血缘上我们有祖孙的关系,但今天我想除了作为一个后人对前人的追忆之外,还作为一个学者对前辈学者进行评介。
十年苦读《四库全书》
陈垣先生1880年11月12日,也就是清光绪六年十月初十,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棠下镇石头乡富冈里。祖父出生在一个经营药材生意的商人家庭,他是多年来家族中第一代的读书人。新会这个地方盛产柑,新会产的柑皮是名贵的中药材,也是很好的调味品,是正宗地道的“陈皮”。我的高祖父海学,也就是我祖父的祖父,是怎么起家的呢?他就是在家乡收购这个陈皮,到广州贩卖起家的。27岁的时候由于经营有方,他就在广州开了一个中药铺,叫做“陈信义”。我的高祖父有9个儿子,这9个儿子都继承父业做药材生意。
我祖父5岁跟着父亲到广州去,住在药材店当中,入私塾读书,12岁基本上读完四书五经。偶然在他老师的书架上发现一本书,就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打开一看觉得眼界特别开阔。因为《书目答问》不是特别复杂,就是讲什么书有什么版本,所以他12岁就按照《书目答问》买自己想要读的书来看。13岁他就开始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眼界就更加开阔了。到他14岁的时候广州大疫,发生了流行病,这个时候私塾就解散了。因为学馆解散,所以他就有时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打下了一生做学问的基础。
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买书、读书是得到了他父亲的大力支持,因为他要买的书不仅仅是应试教育的书,而包括很多方面,特别是史学方面。原来家族里面长辈对他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因为好不容易出来这么一个又聪明、又用功的子弟,所以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希望他能够得到功名,可以光宗耀祖。最后看到他买那么多在他们看来是杂七杂八的书,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失去了大家对他的期望。但是,他的生父不仅不责备他,而且只要他要买的书从来不吝啬,花了100多两银子买了《二十四史》,据他回忆,他花了上千两银子把当时广东出版的书大部分都买了,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他父亲大力支持,他不可能打下他后来一生学问的基础。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今天,他那个时候是14岁,如果今天一个14岁的少年,有一年不用上学他会做什么?对陈垣先生来讲,他就利用这么一个难得的可以自由读书的机会认真的读书。
到了17岁的时候,他就到顺天(今天的北京)来参加顺天的乡试。虽然他读那么多书,但是他包括他父亲也有这么一个期望,就是让他得到功名,所以让他参加乡试。科举考试分三级,第一级是童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是会试、殿试。当时他父亲用八两银子给他买了一个国子监生的资格,他可以跳过童试的阶段;又因为顺天乡试录取的比例比广东高,他就到北京来参加乡试。他原以为凭他的学问必取无疑,但因为作文不合八股程式名落孙山。他回到广州以后,从18岁开始,一方面他就自己到私塾当老师,因为当老师就可以有收入,他觉得辜负了家人对他的期望,他从此要经济独立。另外,他利用这个时间熟读八股文,他读的办法是什么?把在这之前10次考试中试试卷都买来,买来以后他先读一遍,把他认为不错的留下来。然后再从头到尾读第二遍,又筛选一批。最后剩下100篇是他认为最好的,就反复琢磨应该怎么做这个八股文。做了两年以后他认为没有问题了,他再去考童试,最后中了一个秀才。当时叫做廪生,廪生就是有助学金的,每个月大概有多少助学金。以后他填的学历就是前清廪生,就是得了一个秀才。
再过了一段时间,科举考试就是考策论,另一方面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他就放弃了科举的道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什么促使他转变的呢?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一段中国的历史。就是1895年甲午海战,1900年辛丑条约,还有八国联军。所以这个时候列强一步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占领了朝鲜,也把我们的宝岛台湾割为它所有。这个时候我祖父就投身革命,他对革命主要是做什么呢?就是从事反对列强、也反对清朝的文字宣传,就是办报纸,他先后办过两个报纸,一份叫《时事画报》。《时事画报》是1905年创刊的,他的筹备是1904年开始。这个《时事画报》既有文字,也有图画,图画的主持人叫潘达微,是中国最早的漫画家,也是革命的志士,我的祖父主要是负责报纸的文字部分。
当时在广州,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你要用文字宣传反对列强侵略、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反对清朝的专制统治,你不能够直接的表达出来,所以他就采取了迂回的办法。大概是两种办法:一个是借抨击元朝影射清朝,因为元朝跟清朝都是边疆的少数民族取得了中央政权,他就用元朝的民族压迫、专制统治来影射清朝。另外,他收集了很多当时清朝皇帝发布的“上谕”,他就把这些剪下来,分类编了好多册,利用皇帝自相矛盾的话,来揭露清朝的专制统治、民族压迫。
而且他也参加了一些实际的革命活动,包括当时从香港这个地方运武器到广州准备武装起义,他做了这些工作。而且家里还有手枪。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讲过,在我父亲8、9岁的时候,他跟他弟弟翻我祖父的抽屉,就翻出手枪来,结果一比划就走火了。这个事情很严重的,因为发现你家里有手枪马上就要处死,但是还好家里面比较深,声音外面没有听见。所以由一个我祖父一辈的堂兄弟把这个枪带到珠江边上,买一张船票上了船,等快要开船的时候把枪从船的厕所里面扔进了珠江。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当时他不仅是做文字宣传,也参加了一些准备武装起义的这样一些实际工作。因为这样一个原因,1912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1913年他当时33岁,就因为他在辛亥革命前做过这么一些工作,所以他是以一个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众议员。众议员当时是专职的,是拿薪水的,所以他1913年到了北京,就在北京定居了。
到北京,对他一生来讲影响很大。首先,北京是文化中心,他在北京结识了不少学界有名和很有成就的学者,他的眼界开阔了,交往也频繁了。此外,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了解国外的学术情况也比较方便。还有一点,他到北京后看到了他在广州很想看但看不到的书,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就是《四库全书》。他是1913年到北京的,1915年的时候,政府把原来存在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从承德运到了北京,在当时的京师图书馆。
我祖父从1915年开始大概花了10年时间钻研《四库全书》。当时看一次《四库全书》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住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当时天安门广场一带还是禁地,所以要绕一个弯才能到东北角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去看书,单程要两三个小时。所以他每天很早要走2个多小时,在开馆之前到达京师图书馆,在闭馆以后才回家,中午带点干粮在那吃。前前后后10年左右,当然,不是10年时间就只做这个事情,是这个事情经过了前前后后10年。有人说陈垣把《四库全书》全看了,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不需要这么做。他已经了解了《四库全书》的价值和它的问题,《四库全书》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清朝是 边疆少数民族取得了全国政权,修《四库全书》的大臣们怕因为提到边疆的少数民族会影射到皇帝,皇帝会不高兴,所以碰到原书里面的“夷”、“狄”、“虏”等都改,甚至篡改了原书的意思。
所以我祖父说凡是《四库全书》在外面已经有刻印的就不需要看,他要看的是《四库全书》里外面没有刻本,而且跟他研究有关的书。另外,他看《四库全书》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一般地去看,而是对《四库全书》是怎么编成的、怎么开始征集图书、征集到北京以后怎么去审查、怎么把妨碍清朝统治的书毁掉、或者某一部分有妨碍的内容改掉,他把这些内容弄得清清楚楚。1921年他带着7个助手把文津阁的《四库全书》每一册、每一页都详细地做过检查。为什么做这个工作?因为当时有一个计划,就是把《四库全书》影印,这就要计算总共有多少页,需要多少成本。他利用这个机会把《四库全书》的实际情况同通行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简明四库目录》对照,看哪些有不一样的地方,写成一本书名叫《四库书目考异》。而且当时藏在故宫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他也去看过,所以他是第一个亲身看过文渊阁和文津阁两部《四库全书》的人,而且是对四库全书做过仔细检查、深入研究的人。
那么我就可以总结一下他的读书生活,14岁时候一年自学,然后是18岁以后两年熟读八股,到北京以后10年研究、苦读《四库全书》,这就可以概括他前半生的读书生活,可以看出是多么刻苦。当然,从这以后终身读书是没有停止过。这是他的读书生活,所以他能够通过自学而成为一代宗师、一个大家绝对不是偶然的。
弃政从学
到了北京后,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22年,他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他是广东人,当时是交通系梁士诒当总理,因为同乡关系,到了北京以后他参与了交通系的一些政治活动,1921年底到1922年中当过6个月教育次长,就是教育部的副部长。当时教育部部长是黄炎培,他没有到任,而且教育部的副部长只有一个,所以他实际上主持了半年左右的全国教育工作。
本来他到北京来是抱着很大的理想的,但是在北洋政府统治下面他的抱负不能实现,而且自己也卷进去了,所以他就逐渐脱离政界而转向学术。1917年,他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叫做《元也里可温考》。二十四史中的《元史》多次出现“也里可温”这个词,也里可温不是一个汉文的名词,也不像蒙古文,那么这个也里可温究竟指什么?过去一直弄不清楚,直到道光年间才知道这个是指基督教,但是究竟怎么回事还是弄不清楚。《元也里可温考》就是把也里可温是什么、怎么传到中国来的、在中国有些什么活动、跟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关系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国内和日本学术界的重视。
1922年以后他就彻底离开了北洋政府,彻底离开了政界,完全转入学术界和教育界。从1922年开始先是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做导师,从1926年开始担任辅仁大学的副校长、校长,后来又在燕京大学当了国学研究所的所长。在1929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两年以后在北大当名誉教授。新中国建立以后,1952年北京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他就继续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一直到他去世。1954年开始,他一连三届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一届、二届、三届的人大常委会委员,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71年6月2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用三句话概括陈垣的一生
第一句话,他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位自学成才的杰出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历史学家。那么他这个声誉我们可以怎么来看呢?二十年代他是公认的和王国维齐名的,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开始,史学界就有“史学二陈”“南北二陈”这么一个广为人家传称的称号。“南北二陈”的南陈是指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是江西人,生在长沙,我祖父生在广东。为什么把陈寅恪先生称为南陈,把陈垣先生称为北陈?因为我祖父1913年以后主要都是在北京,陈寅恪先生后来在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一直在广东,所以前面是王国维和陈垣齐名,后面叫南北二陈,可以看出他在中国的史学界和学界的地位。
第二句话,他是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的大教育家。过去因为他作为史学家的名声很高,对于他教育家这方面大家就有些忽略了。我粗略的统计了一下:他教过私塾;做过孤儿工读园的园长;他当过小学老师,他在广东宣传革命时候,清政府要抓他,他回到家乡当了半年的小学老师;他当过中学老师,还当过中学校长;当过大学的教授,而且当了大学校长。他一生大概从教74年,大学校长47年。特别是当了47年大学校长,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
第三句话,他是一位坚定的、热烈的爱国者。我觉得从这三个方面来概括,首先最重要的还是他是一个爱国者。那么他的爱国思想、爱国主义是怎么样形成和发展的呢?一个是他的家乡新会,包括广东对他的影响,他在新会生活了6年,在广东生活了33年。他青少年时期家乡对他的爱国精神形成的影响是很深的。新会在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最西端,珠江三角洲从全国来讲是最早受到列强侵略的地方,鸦片战争就是爆发在珠江三角洲,所以最早受到列强侵略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最早沐浴到欧风美雨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西方的启蒙思想、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也比较早地传到了珠江三角洲。所以这样的地域有这么一个特点。
另外一方面,在新会这个地方发生过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279年在新会的崖门发生的宋元的大海战,1276年元军占领南宋的都城临安,把小皇帝给俘虏到了北京,后来当了和尚了,在元军进临安之前,有大臣护送小皇帝两个弟弟,一路沿海从温州到福州,一直到了今天的中山,本来是想到越南南部去的,结果元军已经封锁了琼州海峡,最后又回来到了崖门,就是新会靠海的一个地方。当时崖门是一片海湾,宋朝的大批船只驻扎在海湾当中。1279年大海战,结果宋朝彻底失败了,丞相陆秀夫背小皇帝跳海殉国。宋军的统帅张世杰当时已经冲出元军的包围了,他准备再冲回来时候遇到台风,牺牲了。十几万南宋军民殉国,海水一片血色。崖门海战对我祖父影响极大,从辛亥革命之前开始,一直到他最后一部著作,1946年完成的《通鉴胡注表微》,十几次提到崖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新会、珠江三角洲对他的影响。
第二点是他沐浴了欧风美雨,他很早看到西方的启蒙思想著作,对他影响最大的一部是卢梭的《民约论》,现在译作《社会契约论》,它讲到总统是人民的公仆,祖父在文章中就引申说,皇帝也应该给老百姓做事而不是奴役百姓,这是清朝统治时期他在广州写的文章里面讲到这个问题。以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升华,上个世纪20-30年代,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包括胡适,包括傅斯年,包括陈寅恪,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汉学中心从西方、从日本夺回到中国来。他们用这样一种目标这样一种思想,一方面教育青年、引导青年,我祖父是从二十年代初期一直到三十年代,在不同的学校针对不同的学生用不同的语言讲这个话激励学生,另外他们自己也率先垂范,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取得了中外学者公认的成果。
书斋做战场,纸笔做刀枪
今天是七七事变75周年,我特别想讲一讲抗战时期陈垣先生是怎么做的、怎么度过的。
七七事变以后很快日本全部占领北平城,当时他是没有离开北平,没有南下。那么为什么他不离开北平?他留在北平做了些什么呢?他的最好学生之一柴德赓就分析:说一个原因是他有一些书,他是做学问的人,南下以后他没有书就不可能再做学问,这应该是一个原因,但是这个还不是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对于那些离开北京的人,包括他的朋友、晚辈,他是很支持的,他说你们能离开就离开。当时他的子女,也就是我的父亲、叔叔、姑姑这一些人,除了像我父亲和我一个叔叔原来就在南方以外,我的一个叔叔和两个姑姑都被他送到了南方读书,只有我第二个叔叔留在北平,那么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第三个原因是他觉得有责任留在北平。留在北平干什么?他为什么坚信他能需要在北平,而且能够做很多事情?这里面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什么信念?
第一个,他坚信侵略者是不能持久的,日本的侵略者肯定是要失败的。抗战时期他写了好几本书,这几本书是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战斗的著作,在书里面他讲了好多话。你看他有一本书叫《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本书里面他说“自永嘉(晋朝的一个年号)以来,河北已经被外族侵占很久了,但为什么最后中国会恢复呢?中国的人口还越来越多呢?就是千百年来先民艰苦培养而成的这么一种民心。”这里我要强调,当时他只能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来比喻抗日战争,因为民族斗争也是有是非的,也是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的。南宋与金朝,岳飞与宋高宗、秦桧,是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的。这不是牵强附会,而是援古证今。这是第一点,他坚信侵略者是不能长久的。
第二个,要考虑现实,就是沦陷区的人民不可能都跑到后方去,包括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都跑到后方。看抗战时期的政治地图就可以看到,日本占领了多大一块地区!东北是满洲国,华北大部分地区一直到华南都是日本占领的,国民政府统治区就是西北、西南,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当时讲有19块,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敌后,范围很小的,所以让沦陷区的人民全部跑光是不可能的,大部分必定会留下来。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包括老师、学生,你让他们都跑到大后方或者解放区去教书或者上学也是不可能的。这样,沦陷区在各个战线上就需要有人主持正气,他就认为他自己应该是其中之一。另外,他在《明季滇黔佛教考》里面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云南的和尚,在当时南京一个寺庙当住持,清朝说寺里有人“通贼”,就是和反清的力量有联系,要把寺里“通贼”的人抓走,把寺庙封掉。这个和尚就用尽办法跟敌人周旋,结果保住了这个寺庙。这就是他自己的自况,而且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各个地方、各个战线都需要有人主持,那么他就是其中之一。
第三个,当时有的汉奸说“我们当汉奸不假,但是你们没走就也是吃这个地方的粮食,你们跟我们有什么区别?”他在《通鉴胡注表微》里面有一段话专门针对当时这些汉奸的言论进行严重的驳斥,他说:“虽然是沦陷区,但这是我们中国的国土,我们住在中国的国土上面,吃我们自己种出来的粮,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他有一套理论、一套信念在坚持,最后他说我要留下来就是要竖立一面旗帜,他有两句话叫“正人心、端士习”。“正人心”就是端正人心,“端士习”,端也是正的意思,士是讲知识分子,要教育青年劝告朋友一定要保持民族气节。当时有这么一件事情,1944年1月已经到了抗战后期,辅仁大学一个姓周的校友,冒险从大后方来到沦陷区北平,看到我祖父的情况很艰难,他就说“我愿意陪你到后方去”,我祖父怎么回答他呢?他说“如果我南下,辅仁大学几千个青年有什么人能够代替我来教育他们呢?沦陷区的正气有什么人来代替我来支持倡导?”所以这个校友听了很感动,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他就在开封的《正义报》 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平沦陷期间探险记》,详细记录我祖父当时的情况。
我祖父在1944年的时候有一封信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收信者叫方豪,他是天主教的神父,又在浙江大学教书。我祖父给他写的信怎么讲?因为在沦陷区写的信,所以他不能讲得很明显,但是了解情况的人都懂得什么意思。他说,关于史学,这里的风气也在改变。原来讲钱大昕的考证之学,事变(指九一八)之后,趋重实用,采用顾炎武的《日知录》做教材。现在(指七七事变之后)讲全祖望的文集。他说:“我不仅仅是为了教学生怎么考证,就是为了让知识分子坚持民族气节。”
但是要实践起来并不容易,怎么去实践呢?他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维持辅仁大学;第二件事,教育学生;第三件事,以自己的书斋做战场,用纸笔做刀枪,写了一系列有战斗性的著作和敌人做斗争。做这三件事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举一个例子:1943年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东洋史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近日北京学界”。这个作者为什么发表这个文章?他讲陈垣先生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超人的活跃,而且形成追随陈垣、形成一种学风,非常壮观。然后这个作者笔锋一转说:“辅仁近日遭到厄运,文学院院长失踪了。”他是沈兼士,所谓失踪是因为敌人要抓他,他当时是国民党地下工作负责人,撤退到后方了。孙楷第他们也被捕了,作者就写到“今后甚希望陈垣等自重。”这篇文章在幸灾乐祸之中带有恐吓之意。这位作者生于1914年,前几年还是健在的,如果他活到今天是98岁了,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他写这篇文章是29岁,后来他在史学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我想如果他健在或者到他晚年回忆到这段历史的话,他曾作为日本侵略的一个马前卒,我想他也会后悔的。学术界是这样,其他方面的压迫更可想而知了。
1945年9月2号日本宣布投降,9月3号辅仁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我祖父说:“辅仁大学已有八年没有举行开学典礼,因为国旗拿不出来,国歌不能唱,说话都要受到限制。而且日本占领徐州,强迫各个学校都要庆祝,挂出伪满的旗,所以我们干脆就不举行开学典礼和不举行升旗”。1946年他给北平教育局一个公函,讲到“为了保存沦陷区教育的一线,所以做了一些委曲求全的事”,比方说当时伪教育总署屡次要学生的名册,他不得不敷衍一下。
那么为什么要把辅仁作为一个阵地?
第一,辅仁大学原来是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主办的,除了派人,还要经费上的补助,这是1923年。到了1933年的时候,本笃会经费出现了问题,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当时教皇就委托德国的圣言会来接办辅仁大学,所以从1933年开始德国圣言会接办。1937年七七事变,很多大学南迁,唯有两所大学的学历得到当时国民政府承认的,一个就是燕京大学,因为它是美国教会办的,一个就是辅仁大学,因为是德国教会办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燕京大学也办不了了,所以1942年以后沦陷区只有辅仁大学一个学校能够继续办下去,3000多学生是辅仁大学最盛的时期。整个学校主要的校务是由教会的代表,所谓的校务长来主持的,但学校也需要有一面旗帜,如果没有陈垣校长,那你讲中国文化人家也不会来,老师也召集不起来,所以教会需要这么一面旗帜。祖父也利用辅仁这么一个阵地把它维持下来。辅仁大学里面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有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国民党在北平的抗日据点就是在辅仁大学,所以当时有人说辅仁是抗日堡垒,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之间是共同斗争,为了抗日出一份力。
第二,维持辅仁就有了这么一个阵地、一个堡垒,那么就要教育学生,有了这个阵地就要做事情。怎么教育学生?利用一切场合教育学生。1942年4月份,已经是抗战第5个年头,辅仁有返校节,返校节照例开运动会,我祖父就在运动会上面讲话,说“今天不是开运动会么,我给大家讲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孔子怎么开运动会?《礼记》有一篇讲到孔子主持一次射箭比赛,说有三种人不能参加今天的运动会,第一种是败军之将,不能很好保卫国家的,第二种是为敌人做事的,第三种是认敌做父的,这三种人不能参加运动会。”宣布第一条有人走掉,第二条又有好多人走掉,第三条也有人灰溜溜走掉了,也就是说当时那个场合有很多汉奸在里面,他是警告汉奸。还有就是在课堂上,他尽量选择那些能激发学生民族气节的教材。这时他经常教育学生把名节放在第一位,学习放在第二位、第三位。
第三,他自己以书斋做战场,以纸笔做刀枪,写了一系列有战斗性的著作,一共7本。这些书里面都是借着讲宗教、借着讲历史,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斥日寇,斥汉奸,责当权”,这个当权就是不好好抵抗日本侵略、不好好整顿自己的政治的当权者。他的这些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光有义愤是不行的,是站不住脚的。他的这些书都是经过广泛的收集材料、经过严格的考证写出来的,有血有肉、有根有据、有针对性的这样一些著作。所以不但在当时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而且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成为各该领域的经典著作。
《通鉴胡注表微》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
提问1:第一个问题,陈垣当初捐了很多东西,现在据我所知一部分在国家图书馆,一部分在首都图书馆,他捐的东西现在有目录吗?第二个问题,您重新整理的《陈垣全集》会有什么更新的资料吗?
陈智超:陈垣先生去世是1971年6月21号,那是在“文革”期间。他虽然没有直接受到冲击,但是这样一个大环境他感受到了。他最后唯一的报国之道就是把他一生几万册的图书、几千件文物,还有他一辈子的存款4万块钱,就全部捐出去了。当时我记得运文物和书就是四大卡车,要求我们一个礼拜运完,我们就照做了。
这个书跟文物原来是在师大,不知道后来中央哪一位领导说搁在师大不好,还是把它送到北京图书馆,所以书和一部分文物就到了北京图书馆。北京文物工作队是现在首都博物馆前身,就把他们认为最好的挑走了,100多件。4万多块钱就作为党费了。当时手稿也拿走了,有一部分据我所知很仓促地拿回家了,但是两家没有很好的保存地方,结果他们把手稿也拿走了。现在这个简单的目录是有的,包括手稿、文物、后来的书籍。但是原来我们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得到好好的保管,特别能够集中在一起,这个恐怕现在没有做到。
提问1:还有第二个,就是《陈垣全集》又有什么新资料和新东西吗?
陈智超:实际上从陈垣去世开始,我已经注意搜集我所能够搜集到的材料,包括陆续出版了八九种他的著作。《陈垣全集》23册,大概有一半左右是他生前没有发表的,生前没有发表的东西很多,有些是已经成稿但没有发表的,有些是半成品,所以说《陈垣全集》里面是有相当一部分是过去他生前没有发表的新的资料。当然,《陈垣全集》发表以后又陆续有人告诉我好多信息,发现一些佚文和信件,这个我都记住了,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出一本。
提问2:有文章说陈垣先生是基督教新教的教友,如果是这样的话陈垣先生怎么做辅仁大学的校长?
陈智超:我祖父曾经是基督徒,1926年曾经受过洗,给他洗的人是司徒雷登,这是确凿的。那么他怎么会信基督教?他有一段回忆,就是家里面是开药铺的,而且在老家请了一位中医。这个中医是干什么的?就是药材有些是从家乡采过去到广州,广州的一些边角材料不能卖的也运回老家,老家就请这个医生利用这些药材在当地给老百姓义务的看病和吃药。后来我曾祖父得了膀胱结石,结果这个中医怎么弄也弄不好,我祖父就说了,他本来对西医是一点好感没有,但是这时候中医医不好了,而且发作起来非常痛苦,只好到博济医院去开刀,开刀取出来了一个像鹅蛋那么大的结石,后来就好了。因为这样,所以他就由原来不相信西医,到了觉得西医很神,所以他就改学西医了,到博济医学堂学习。因为学西医,就跟很多教会的人接触到基督教,是这样相信基督教的,而且就写中国基督教史,后来就到北京来了。这是受洗这一段。
他是基督教徒,马相伯、英敛之他们是知道的,所以胡适后来讲,当时天主教的大学要请基督教徒当校长,可见它是很包容的。马相伯、英敛之创办这个大学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神职人员要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辅仁大学是以学习了解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理念,这样就要有一个有学问的人来当。所以他们虽然知道他是基督教徒,但还是请他当天主教的校长。但是慢慢他的宗教信仰就淡了,而且他说不能站在护教卫教的立场,要把宗教作为历史文化研究,所以他研究的时候完全摆脱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提问2:您祖父是非常出名的教育家,您能从您本人的经历来讲一讲他是怎么对您言传身教的么?另外,您一直以您祖父作为研究对象,他对您一生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陈智超:我祖父讲过一句话解释什么叫“教”、“育”。“教”就是教;“育”是熏陶而不是教,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受到熏陶,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受到启发,所以他从来不强迫子弟学什么。我祖父有11个子女,有一个夭折了,这11个子女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是研究历史的,而且他开始时候并不是研究历史的。1918年我父亲16岁,还有我的叔叔比他小2岁,我祖父把他们两个送到日本留学,我父亲学的是经济学而不是历史学。当然,他也让我父亲在东京的时候给他抄一些历史材料,所以我父亲留学时候学的是经济而并不是历史,从这也可以看出来我祖父并不是要他到日本去学历史。那么后来他回国以后当过教员,研究中日关系。所以我父亲也继承我祖父的这个传统,他也没有强迫我要学什么。
我16岁高中毕业,那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所以我高中是理科,我考大学不会考历史的,我后来去学地质,因为我觉得祖国物产丰富,但是我毕业以后去报名参加土地改革了。后来我生病了,回来以后在南京,有一个交通部的干部学校,是比较短期的,像今天的中专一样,要一批交通建设的人才,我就到那去学习,后来分配我到云南,在最基层最边疆的地区,一直到今天中缅边界、中老边界。最后因为这个工程局没有任务了,就把全班人马全部从工地调到昆明附近一个地方去学习,后来就搞运动。原来我几次要报考大学,但是那个领导不批准,说现在工作需要不能走。没有任务以后我再申请他也不能不同意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后来还是选择了历史。我当时报的志愿第一是北大历史系,第二是北大中文系,第三是北师大历史系,我报的北大中文系是浪费掉了,因为如果北大历史不取你你也不可能到中文系,但是到北大中文系可以当作家。
我考北大都没有告诉我父亲,考取了我就发一个电报,说我考取北大了。我回到北京以后他很高兴,他平常不怎么动感情的,但是他这一次很高兴。但他并没有强迫我,就是这么一种熏陶,从小让我抄书和帮他做一些工作,就这么一些熏陶。所以我祖父老是引用孔子的话,就是要启发,不要强迫。我想我就是因为受到了宽容的祖父、宽容的父亲的熏陶,最后走上这条历史的道路。
(正文由倪咏娟据讲演记录整理,经作者审订,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3日B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