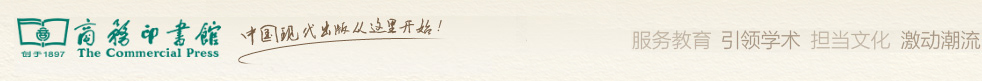
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 系列讲座(第一季)第四讲
时 间:2012年7月21日
主讲人:
李之檀,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美术工作部研究馆员。曾任沈从文先生的助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主图绘画者之一。
王亚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高级工程师,文物修复专家、织绣专家。曾任沈从文先生助手,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插图的绘画者。
沈从文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又是一位历史文物研究者,今年他诞辰110年了,我们满怀深情地怀念这位老人。沈先生从1948年46岁到1978年76岁,这30年都是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和生活的,在他的一生当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我与沈先生同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和他老人家接触比较多,可能知道得多一点,冒昧地介绍一些情况供大家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正。
1955年秋,我毕业后,被国家统一分配到历史博物馆美术组。我的宿舍是东堂子胡同51号院后院的东屋,和沈先生是邻居,沈先生住在北屋,有三间房子。沈先生常带客人到家,大都是老朋友。我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学时,教我们中国美术史的老先生王逊先生就经常到他家做客。王逊先生在西南联大教逻辑学时便和沈先生相识,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学术,每次都谈得火热,友情很深。沈先生的客人中,也有很多是向他求教的年轻人。沈先生对人热情、诚恳,尽量把自己知道的,对别人有用的东西告诉别人,使人受益匪浅。
北京历史博物馆从1907年起就一直在故宫午门外大院里,午门楼上和东西朝房都是陈列室,朝房的南端和北端以及端门前的一部分房子是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参观故宫的人每天川流不息,经过午门前广阔的大院。我工作的美术组,当时叫做陈列部技术组,位于午门前的西朝房最南端,组长是画家潘絜兹。沈先生所在的陈列部内容组则在东朝房的最南端,和我们的办公室遥遥相对。沈先生当时因为有一些社会工作,不坐班,但还是经常来到馆里,他大多都是乘公交车或者步行。当时,沈先生对我们美术组的工作非常关心,当他知道我是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馆里工作的时候,特别高兴。他告诉我,在博物馆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沈先生经常拿他征集到的一些文物,到美术组来给我们看,他在外面见到的好东西也常常讲给我们听,并且时常拿来一些好的资料、好的古代图案让我们临摹,有时候还介绍给我们一些好书看。在他的影响下,我养成了搜集历史形象资料的习惯。一次,他从外面借回来北魏宁懋石室石刻的拓片、唐代的石刻线描人物拓片,让我们画下来做资料。另外有一次借来一批敦煌壁画的临摹本,大概有十多张都是原大的,要我们临摹以丰富博物馆的壁画摹本的收藏。通过这次临摹,提高了美术组临摹壁画的水平。在此之后,我们经常利用休息日去故宫绘画馆临摹古代人物画,勾描画稿。记得有一次我临摹故宫陈列的宋代李公麟画的《维摩演教图》中的人物,还临摹过山西宝宁寺明代水陆画的人物,沈先生看了特别高兴,同时还拿给他的夫人张兆和女士看,夸我画得好,给我很多鼓励。
沈先生在“整风”“反右”当中没有被划成“右派”,为什么呢?第一、他没有权利的欲望,而是一心去做学问。另外呢,他对人特别好,群众关系特别好,非常热心于社会工作。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建新馆,要做一些历史文物的画像、塑像,因为历史博物馆的历史画像不能像画小人书一样随便,要有科学根据,当时沈先生做了这个工作,帮助画家解决历史画的一些服装、道具等问题。后来,社会上很多拍电影电视剧的、演出绘画的人为了解决历史真实的问题,都到沈先生这里来咨询。像北京人艺也是请沈先生来讲课,当时沈先生开了一大笔的书单子,去博物馆借出来给演员们讲课,介绍古代的一些情况。因为找他咨询的人太多,有时候甚至应接不暇,所以沈先生就有了把古代的服饰资料编成一本书的念头,这样可以减轻社会咨询的压力,同时也把知识普及下来。另外呢,沈先生认为,中国老祖宗的事中国人应该最清楚,而当时介绍中国古代服饰的书很少,只有日本学者编写的唐代服饰,还有西域壁画上所看到的古代服饰等,这些就是当时主要的学术资料。沈先生认为研究中国服饰,还要去看外国人的书,这是一种耻辱,应该洗刷,我们要有自己的学术成就,要超过外国人,要研究得更深入、更扎实。沈先生给很多领导同志写信表达这个愿望。后来,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看戏,发现在演出中古装戏服饰情况很乱,有些情况像相声说的关公战秦琼,唐代的、汉代的都搅在一起,周总理就问谁在研究中国的服饰,齐燕铭说是沈从文。周总理说,能不能编写一本书,把中国服饰的情况整理一下,外国有很多他们民族的服饰博物馆,中国没有,这些事情都应该做起来。有了周总理的指示以后,文化部党组决定把编辑中国服饰史的任务交给历史博物馆来完成。博物馆也更加重视,充实了人力。当时,沈先生拟出了一个目录,大家反复讨论选择最精彩的,定下来后就开始画图。当时画图的有我、范曾,有陈大章先生,还有戏剧学院的钟林轩先生。当时出版社是把出版这本书作为一个向国庆15周年献礼的项目。我们画的每幅图,都经过照片放大,然后一根一根地修去每根线条上的毛刺,印刷工人也尽了很大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受到批判,这本书被迫停下来了,我们画的那些图被出版社贴在大字报上,作为批判的材料。后来这个出版社宣布解散时,他们的副社长通知我们:“还有一些稿子和图版,你们要不要?我们已经装在麻袋里准备卖废品了。”我们赶紧到出版社的库房里,把这些稿子和玻璃印版都找出来,拉回博物馆。以后就是依据这些版重新制版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好多博物馆被认为是“四旧”,关门了,有的是怕学生去“破四旧”而毁坏文物也关门了。博物馆就闭馆了将近十年。但是博物馆长期闭馆也说不过去,只好修改陈列,准备开馆。我们这些美术组的同事,都全面地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当时沈先生这本书的出版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人力,因为跟开馆有矛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院长等同志的关心下,沈先生调到了社科院历史所,再以后就是王亚蓉女士、王同志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经过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这本书得以在香港的商务印书馆出版。
有时候我在想,服饰的书为什么是沈先生而不是考古学家写出来的呢?这是个学科交叉的问题。沈先生不仅懂得美术,而且懂得文学,他看了很多古代文献,还重视对图像的观察,同时也非常关心考古发掘的成就。知识的广泛性使他能够编写这本书,并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沈先生的成就绝不只在服饰方面,他在文物研究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另外,我想说的是沈先生的为人、他的追求。他曾经对我们说,一个人不应该去追求权利,追求金钱,一个人追求的应该是怎么样发展你的智慧,而发展智慧就需要增加知识,你的知识增加了,你的智慧才能够发展。他为我们的人生指出了一条很正确的道路。
王亚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成书历程
李老师已经讲了很多,时间有限,我就大致讲一点,沈从文先生是怎么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跟每一项科学研究一样,这本书的写成充满了艰辛。写关于中国服饰的书,是从沈先生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开始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沈先生都在做这件事情。那时候,中国领导人出访,尤其总理出访,礼品图书就是商务印书馆的《新华字典》,而且到各个国家去,人家都有服饰博物馆或蜡像馆。总理在一次特别会议中讲,中国有这么悠久的文化,我们应该编一部礼品书。1964年受总理委托,历史博物馆请沈从文先生开始编写这样一部书,还批给了沈先生八名助手的名额。这部书是通过图像来研究古代服饰,沈先生原计划是十卷本,先出试编本,选了200幅图,请历史博物馆同事帮他完成。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本书被定成歌颂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书,也就搁浅了。
沈先生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多次抄家,房子也没有了,但他一直坚持工作。我是一个学美术的,当时在做一些美术设计工作,找资料时碰到一位沈先生的老朋友,当时人民大学的杨先生,他觉得我很奇怪,说:“人家都在干革命,你怎么天天在这儿翻杂志?”我跟他讲,我要找什么资料,他很热情地说:“如果你信得过老头子,就把你电话告诉我,我认识一位在这方面非常有成就的人。”通过杨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沈从文先生。那时博物馆暂停给沈先生配助手工作,也停止了他的工作,他非常痛苦,只能自己一边写一边画,就因为这样工作停滞不前。沈从文先生希望我协助他画,我认为自己的条件不够,他就说你试试吧,每天给我一点工作,逐渐工作有了一些进展。他希望把我调到历史博物馆,可是那时候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人只要分配工作,都是终身制,工作调动很难。当时沈先生的另外一个助手王先生,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的主任,和我在沈先生家认识以后,他一直想让我调到考古所。沈先生说:“不行,得调到我身边。”后来当历史博物馆同意我进馆,但不允许我协助沈先生工作时,我拒绝去那里工作。沈先生说没有工作、医疗关系不行,还是往考古所调吧。调到考古所以后,我和王先生白天做考古所的考古工作,晚上下班到沈先生家继续跟沈先生做,除了服饰研究以外,还有很多专题,像扇子的演进、妇女坐具说等方方面面的专题。但这种状况很难把非常大的工作完成。而且那个时候,沈先生家里的藏书已被七分钱一公斤卖掉,稿子也被烧掉了。后来的稿子是沈先生当时在五七干校时默写出来的,并且他不断地看资料,不断地在增加。
1978年社科院实行一个科研政策,叫先请菩萨后立庙。“文化大革命”中,社科院受的创伤很重,很多科学家已经不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些有研究能力的专家请进来。胡乔木、刘仰桥等同志了解到沈先生的情况,就把他请进来,胡乔木问沈先生要什么条件?沈先生说我就为了完成这部书,希望要一个可以展开工作的地方,把这些资料摊开,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把王和王亚蓉调给我做助手。胡乔木先生说,你可以到考古所,也可以到历史所。沈先生住在历史所后面,因为近,就到了历史所。
社科院为沈先生成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室,历史所当时的条件很紧张,就破例在西郊的友谊宾馆租了两套房,我和王先生,还有沈先生、沈夫人,我们在一起把工作摊开。当时的玻璃印版什么的都收走了,沈先生自己又重新写一遍,而且增加了非常多的内容。开始只选了200张沈先生认为是学界有争议的图作为试点本,1972年考古所成功发掘了马王堆汉墓,中国两千多年前的丝绸和服饰震动了世界,也给这本书增加了很多内容,各类考古图增加了将近700幅。这本书的出版颇有周折,先是日本的出版社想出,沈先生说我们中国人的书要中国人自己出,最后由香港商务印书馆把这本书完成了,有豪华版和普通版,豪华版样书,沈先生在第一本样书上签了名,送给邓颖超,中国外交部买了20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确实成为了礼品书,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它被作为国礼送给尼克松;另外胡耀邦访问日本的时候,送给日本天皇;还有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访华时,也作为国礼送给她。沈先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完成了周总理的嘱托,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沈先生这本书,大家都知道,是以有争议问题的方式来写的,把历代一些有争议的绘画里面有关服饰等诸方面问题阐述,先拿出来做个试点,下面还有9本,计划都做好了,但是他来不及了。这次商务印书馆,出版了1981年版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简体缩印本,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非常感谢有这么多人喜欢沈先生的书。
沈先生不是专门研究文献的,而是以实物与文献对照来考证的。他没来得及做完,我们有幸,还继续做着这项工作。从1972年发掘马王堆以后,又于1982年由王先生主持发掘了湖北江陵马山楚墓,沈先生为此事撰文刊在《人民画报》称,这个墓打开了战国的丝绸宝库,海外的服饰研究专家对它的图案非常推崇,认为风格和设计既抽象又具象,评价这是中国2300多年前的毕加索设计出来的。一般来说,中国人的服装是平面剪裁和平面制作的,西方是立体剪裁。这些衣服,因为在腋下有一个嵌片,从而通过平面剪裁做出了立体剪裁的效果。1991年第一次由古代服饰学会办的中国古代国际服饰研讨会在湖北荆州召开,就是在那个墓的发掘地。我们用古人的方法重新做出来的一件衣服,展示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大地方,只能铺在地上,那时候有100多个国外的来宾学者,那些教授在旁边跪成一圈仔细观摩,这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感动。考古是实证科学,这么多年,包括法门寺的唐代丝绸、新疆尼雅的一些墓,还有阿斯塔纳纺织考古新发现不断出现。我们考古所到现在的所有纺织品文物资料,都是我们,也可以说是沈从文先生这个团队参与发掘的,很多资料都等待发表,我们计划从下半年开始有些就要陆续出版。沈先生走了24年了,王先生也因为尿毒症于15年前过世了,沈先生的工作班子没有了,但是我们一直在坚持,虽然我都过70岁了,但是可以说一直在考古第一线上,带领一批后学努力工作着。
大家可能都知道,2007年到2009年有十大考古发现,都是历朝历代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沈从文先生那么好的文笔,做得太慢,让大家着急。另外一个原因是墓发掘出来以后,得好多年才能把清理和研究工作做完。比如2007年的江西靖安出土的一件文物,乍看因为是黑红的,感觉好像漆器,我拿手触摸一下子就化了,当时电视台都在问,我说不是漆器,但不知道是什么,后来经过放大镜一看是织品。它太细密了,一公分里面有经线240条,一毫米有24根,非常令人吃惊的数据。你想2600多年前,这么细这么均匀的丝织品,反映出的中国的服饰文化,从养蚕缫丝一直到织造都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高超技艺。这些发掘整理工作需要很多时间。现在我们在首都博物馆有一个工作室,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有一个工作室,在湖南省也有一个,另外一个在吐鲁番博物院。我和我的学生助手们一直沿用着沈先生的方法继续工作。
另外我要介绍的是,沈从文先生一直提倡的为人民服务、古为今用。咱们现在,十几亿中国人民都不穿中国衣服,他特别遗憾,他认为中国人应该穿有中国元素的衣服,颜色应该多样,这是沈先生的夙愿。现在我特别欣喜地看到,好多人都在提倡汉服,我们经济实力强了,有能力考虑我们国家的整体形象。我觉得最汗颜的是作为中国代表团,面对世界的时候,连柬埔寨、朝鲜、越南这些国家都穿戴整齐,而中国代表团站在一起,穿着的就是国外品牌的杂牌军。阿拉法特,一辈子穿民族服装,一看服饰就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这是自尊自重的事。沈先生就希望现在有代表咱们国家形象的衣服,中国的衣服自古以来就是多元的,所以不管是休闲的还是礼服什么的,都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质,这是咱们大家一个共同的课题。
沈从文先生对于咱们中国的美术教育和服装教育,也跟我们谈过,他曾对每年春天很多美术院校的学生到公园里写生画牡丹有一个看法,其实中国传统服饰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历代沿袭特别优秀的传统图案。如果设想一个学美术或者学设计的学生,一进校门就有一定的课程来临摹历代最好的形象,到毕业时,差不多将近两三千张了,这种固定的、传统的,经过历代画师们努力的都是精华,这样将来搞设计,举手投足出来的都是中国元素。而且他很反对把国际设计大师请来通过翻译传授,翻译本身不易准确,他们讲的中国人理念、中国人习惯、中国人传统包括一些对于服装的要求又和我们都不相符合。沈先生说有时候不能怪设计师和学生,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训练。
希望有志趣的学者和同好为了再次振兴和发展中国的服饰文化,学习沈从文先生认真、忍耐、务实的工作精神,尽心地努力工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
主持人:艺术人生这一路走来给我留下了非常多宝贵的知识和财富,我们今天讲座有一些内容,还没有说。大家有问题可以提问。
提问1:请问王老师哪儿有卖这个书的啊?
王亚蓉: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有卖的。
提问1:书店也有卖的吗?
王亚蓉:有,网上也有卖的。
提问2:您好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刚才听到您说,沈从文这套服装研究不是一本书,而是10本书,这个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能请您稍微详细说一说吗?接下来的书会不会有机会出版?会不会继续有后人来做?
王亚蓉:沈从文没来得及做完,沈先生他不是专门研究文献的,他是以时政来考证,我们比较有幸。社科院考古所从1972年发掘马王堆以后,1982年由王先生,我们主持了湖北江陵马山楚墓,而且沈先生在《人民画报》写了一篇报道,这个墓打开了战国的丝绸宝库,这个东西非常多,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工作,而且在国外非常推崇。它的图案被海外的服饰研究专家认为说是,风格和设计既抽象又具象,说这是中国2300多年前的毕加索设计的。而且它的一些服饰,我们发表论文以后呢,也是得到非常好的评论。像在国外一般的中国人的服装是平面剪裁和平面制作,西方是立体剪裁。2300多年,因为那些衣服,在腋下有一个嵌片,通过平面剪裁做出了立体剪裁的效果。而且在外面的时候,被他们称颂,我就觉得外国人对咱们中国的学术和各方面都是看不起的。但是他们对于咱们中国古代文化,可以说是膜拜。
在1991年,第一次中国古代服饰协会,中国古代国际服饰研讨会在湖北荆州,就在那个发掘地。我们把研究成果用古人的方法重新做出来一件,当那件衣服展示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大地,只能铺在地下,那时候有100多个国外的来宾,那些教授们在旁边跪一圈,当时考古队的队长和荆州博物馆馆长就跟我说,说王老师你知道什么叫五体投地吗?当时真是古文化的感动,而且沈从文先生坚持这个事业,一直做这方面的研究,考古是实质的科学。这么多年,包括法门寺的唐代丝绸,新疆的一些墓,还有阿斯喀纳一些墓不断地出现。但是沈从文先生第一本拿出来以后呢,等于说沈从文先生这个团队,我们考古所的到现在所有纺织品,都是我们组织发掘的。而且很多资料,在待发表中。现在就是我们的计划了,从下半年开始有些就要正式出版,而且我想非常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很多人认为沈先生过世了,走了24年了,沈先生的工作班子没有了,王先生也是因为尿毒症也很早过世了,但是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虽然我都过了70岁了,但是可以说一直在考古工地第一线上。
大家可能都知道,2007年到2009年有一个十大考古发现,江西赣州有一个大墓47个棺材,东周出了一批丝绸品,而且出现密度最大的,另外就是说现在不断在做,我们做的辽宁的,因为都是第一手资料,都是历朝历代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沈从文先生那么好的文笔做得太慢,让大家着急。自从做了老山汉墓以后,在首都博物馆我们有一个工作室,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保护中心有一个工作室,在湖南省也有一个,另外在吐鲁番,我和我们学生助手们一直沿着沈先生的方法,我们不是在评判。像2007年的靖安,当时出现的时候感觉好像漆器一样,因为是黑的红的,我拿手触摸一下子就化了,当时电视台都在问,我说不是漆器,当时我也不知道,后来经过放大镜一看是织品,因为它太细密了,一公分里面纺织品有多少经线,多少纬线这是纺织品的密度。一公分里面有经线240条,一毫米有24根,非常令人吃惊的数据,你想2600多年前非常均匀的,这么细的丝织品,反映中国的服饰文化一系列的从养蚕抽丝一直到织造,这都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而且这个墓还有很多都是女性,死掉以后,大部分三个墓都是用竹席来裹,其他都是用纱来包裹,而且这里面出了动物纹样有很多,这些工作一个墓出来以后,得好多年才能把清理和研究工作做完,这个对我们工作效率慢,也是比较抱歉,但是大家都在努力。
另外,沈从文先生提倡的为人民服务,古为今用,他特别遗憾,在咱们现在,十几亿中国人民都不穿中国衣服是非常大的遗憾,他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应该中国人穿中国衣服,中国颜色应该多,这是沈先生的宿愿。在和我的这些小同事们大家都在努力,现在我特别欣喜地看到,在网上看,好多人都在提倡汉服,我们经济实力增强了,我们有能力考虑我们国家的整理形象。像陶大姐跟我讲,觉得最汗颜的是作为中国代表团,面对世界的时候,连柬埔寨,朝鲜,越南这些国家,站起来虽然不好看,但是非常整齐,中国代表团一站起来,国外品牌的杂牌军。现在我希望大家喜欢沈从文,尊重沈从文,希望在这方面,中国人穿中国衣服,大家是共同努力,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服饰,包括领导人。你看阿拉法特,一辈子一看服饰就是他的国家,这是自尊自重的一个事,沈先生就说希望有代表咱们国家形象的衣服,中国的衣服自古以来都是多元的,也希望现在,不管说是休闲的,是礼服或者是什么,都是咱们大家共同一个课题。
主持人:还有其他问题吗?
提问3:我和我的师妹来自北京服装学院,我们都是非常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关注中国古代服饰的爱好者和学生。我们一直很感动于沈从文先生和几位老师所做的这项工作,包括沈从文先生他在他的故乡凤凰的五采石的墓碑上的16个字,“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所以每一次在讲中国服装史和讲这本书的时候,都会提到沈老师这些话,也一直激励着自己。在这儿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我想请问,王老师还有李老师,都可以,因为在现在很多高校,像北京服装学院,或者中国美院都有服装史的专业,讲授服装史的课程这种模式和老师所做的工作都是有差异的,我们特别想知道,对于老师这个角度来讲,什么样的方法就是更能够让今天的学生有更多的服装史的认知,同时也能够把文献,实物图像还有文学作品,这几项分析的功力都集合在一起的方法,怎样能更好推动服装史的研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推广?
王亚蓉:先不说我们自己了,沈从文先生对于咱们中国美术教育和服装教育,他跟我们谈过,他就认为,尤其对于每年春天很多美术院校的学生到公园里写生画牡丹,他有一个看法,其实中国传统服饰,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历代都有特别优秀的图案。而且就是说,如果设想一个学美术或者学设计的学生,你让他一进校门以后有一定的课程是临摹历代最好的形象,如果到毕业以后,差不多将近两三千张了,将来这种固定的传统的,因为他也经过历代的画师们的努力,就是得到都是最精华的,这样将来不管搞设计,举手投足出来都是中国元素,而且他很反对把国际设计大师请来翻译,本来翻得不准,本来他们是把和中国人理念、中国人习惯、中国人传统,包括一些我们对于服装的要求完全相不符合的东西,灌输给孩子们,有时候讲的中国服饰,沈先生说有时候不能怪设计师和学生,他们没有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训练,甚至沈先生讲,实际上不及格的老师教不出来一个好学生。
北服的院长是我同学,他请我跟王先生做一些讲座,后来说,你们这么一讲我们讲中国服饰史怎么讲啊?当然现在就是说师资和需要,还有一些麻烦,我们是因为是做科研工作的,对于教育这方面也不了解。但是国内艺术院校讲课,我刚从台湾回来,台湾艺术大学服饰研究所,就请我去讲中国传统的服饰文化,我从中国传统的纹样,还有中国纹样进行实际的织,比如说刺绣是见得最多的,历代的刺绣情况,因为古物维护,因为现在很多私人收藏家有丝织品和纸制品,丝织品虽难保存,一千个墓有几个能保存下来非常少,整个中国服饰文化,还是属于凤毛麟角。台湾到这儿来参观,邀请去讲,从出土现场碰见的怎么提取?怎么现场保护?保护回来以后怎么清理?怎么研究?一直到研究如何跟现代文化应用。我觉得现在就说是,因为我们跟教育完全脱节的,这儿有一些情况我不好讲。但是说,有的还是注意到了。
李之檀:我觉得中国服饰文化是一个非常博大精深的学科。特别是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也有56个民族,这个民族的服饰里面的遗产更是丰富。所以我觉得系统地深入地整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遗产,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我觉得,要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而且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把它很好地做到。我觉得服饰文化就是老祖宗传承下来,是通过多种角度传承下来的。一个就是古文献,古文献里保存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的记载。另外呢考古发掘,我们从地下挖出来很多很多的东西,还有呢就是传世的文物,包括各个博物馆,保存下来的传世的服装。另外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皇族他们都没有了薪水,他们把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卖,来维持他们的高水准的生活水平,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沽衣业,沽衣业非常繁荣,当时很多好东西都被外国人买走了,所以外国人传世下来的服饰的文物也是我们非常之重视的东西。
另外就是说,古代保存了很多图像,包括绘画、雕刻、版画等等,在这里保存了非常多的图像可以进行研究,另外呢,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师父带徒弟,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服装制作的收益。沈先生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服饰研究的开山之作,他给我们开辟了这样一个领域,这个领域非常广大,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人继续来把这些老祖宗的东西很好地传承下来。我觉得沈先生的书出版以后,出版的关于服饰的书是非常之多的,但是我也觉得缺乏更深一步的研究,更深层次的研究。所以呢,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去努力,现在就是说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决定出版一套《中华大典》,《中华大典》里面包括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其中又包括艺术。《艺术卷》里面有一个《服饰》分典,现在让我来做《中华大典》服饰分典的主编,来负责整理古代的文献。就是古书里面的文献记载,凡是有关服饰方面的都要把它整理收集起来,然后按照新的需要,重新编排起来,我现在正在做这个古代服饰文献的整理工作。这个工作已经进行了五年,恐怕还要有三年才能够完成,我们一共有五位同志参加这个工作。
我们觉得古代文献的记载是非常丰富的,将来王亚蓉同志是侧重于考古发掘材料的研究,另外我们还需要把传世的文物很好地研究,要把古代留下的图像,各种形象很好地研究,这个是沈先生给我们开拓了非常广阔的领域需要我们去做。另外,我觉得现在的服饰研究工作常常有不同的出发点,比如服装学院,我感觉它现在的需求很大,就是什么呢?关于演出服饰的设立,包括奥运会的,什么晚会的,什么民族汇演的这些服装,都要设立,就要找传统的因素,把这些因素拿过来为新的设立需要来进行创作,我觉得服装学院是比较侧重于这个。戏剧演出单位又不同,为了戏剧演出的效果,还有一个舞台效果,不但有历史真实的问题,还有舞台效果的问题。而作为历史博物馆,历史研究所,他是把服装发展的历史看做是周围历史发展的一个侧面,就是服装的历史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水平、生产水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另外服饰反映了很多民族关系问题、中外关系问题,他们的领域是开阔的,只有通过大家的努力,多角度多方面地来研究中国服装史的研究,才能够更深入下去!
主持人:谢谢李老师和王老师精彩的演讲!我们今天的活动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两位嘉宾!
(正文由卢晓军据演讲记录及李之檀讲稿整理,经王亚蓉审订,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7日B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