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图书
-
社会法与市民法¥68.00
从市民法到社会法的开拓之路
2024-02-08作者:刘清生刊发媒体:法治日报•法治周末浏览人数: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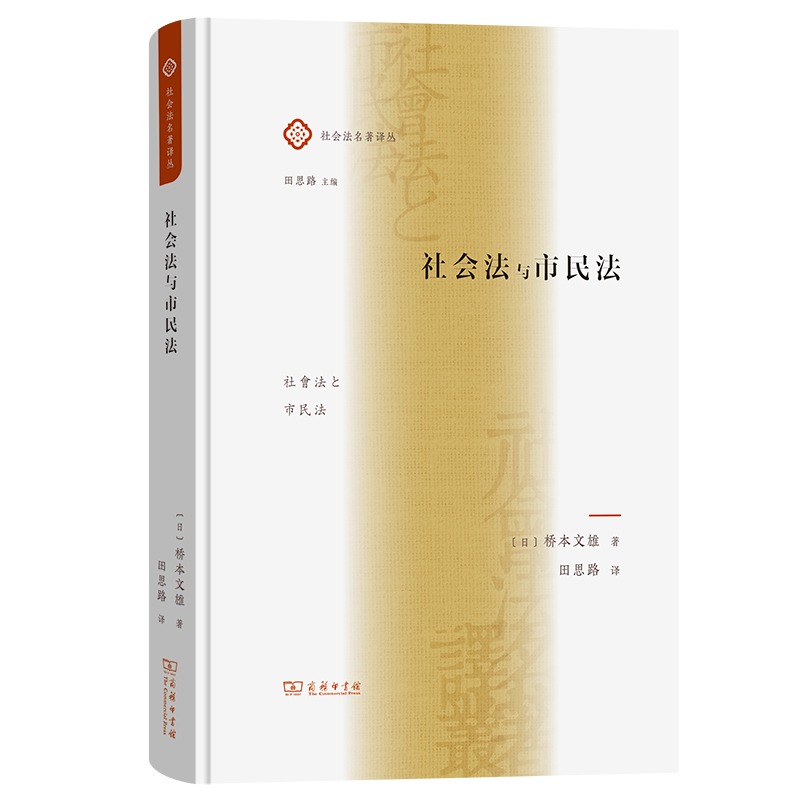
《社会法与市民法》(商务印书馆2023年出版)
犹如桥本文雄所言,“社会法的特征存在于与市民法的对照性之中”,他在社会法与市民法的比较中阐释社会法,可以说是抓住了社会法的根源问题。
究竟何谓社会法?这个近代才真正进入人们视野的问题,至当代似乎仍无形成基础性共识的迹象。
从经济法、劳动法到民法
学界或将社会法理解为社会保障法(含社会救助或社会福利内容),或将其理解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之法(关涉社会生存权、发展权等内容)。相应地,社会法的权利主体或被理解为弱势群体,或被理解为集体或社会,而义务主体则被解释为国家为主、非国家为辅。然而,学界对于弱势群体的理解实质上回归为弱势个体,而对于集体或社会的理解也实质上回归为集体中的个体或社会的个体,群体都最终被化约为个体。
权利是国家赋予的,奴隶制国家不赋予奴隶以权利因而常被视为客体物,无法称为主体人。个体作为社会法中的权利主体、国家作为义务主体,社会权具有可诉性的结果是,国家将可能成为每一个公民的具体被告。这种推论结果难免不尽如人意。但这是当前学界研究现状的可能推理结果。
纵观学界研究,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即研究社会法的学者要么是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者或经济法学者,要么是宪法学者,其他法学的学者研究社会法的鲜有,我国尤甚。桥本文雄虽为经济法学者,但他的《社会法与市民法》并没有站在经济法角度而是从民法、商法乃至诉讼法角度阐释社会法。这可谓是以市民法研究社会法的开拓者。当然,1872年德国学者赫尔曼·罗斯勒在《德国行政法》中曾站在个人法角度理解社会法。
从章标题到专著精神
桥本文雄以“社会法与市民法”作为专著的标题,而在第十四章则以“从市民法到社会法”作为标题。这体现了作者的内在心理:专著并不将主力集中于“市民法到社会法”的动态发展,而主要聚焦于“社会法与市民法”的静态比较。徐国栋教授认为,将市民法概念翻译为国内的民法概念为不忠实翻译乃至属于错误翻译。质言之,民法即市民法。
在第十四章中,桥本文雄以物权法、债权法、商法、身份法和诉讼法的变化阐述市民法与社会法的不同,诸如从个人主义的家族法到社会的身份法、从个人主义的所有权法到社会化利用法、从计划性企业法到社会化经营法或经济法、从债权交易法到社会行为法、从个人主义的私人诉讼法到社会的诉讼法。其基本精神内核是,社会法来源于市民法而不同于市民法,市民法体现个人主义精神,社会法体现社会化需求。或者可以提升为,从市民法到社会法是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精神内核的变化。
纵观专著整体,可以清晰地看到桥本文雄对市民法个人主义本质的定性。如第六章“近代市民法的成型”对亚当·斯密承认利己主义思想、狄骥的个人主义、德国民法典草案关于契约自由等内容的讨论,无不体现对市民法推崇个人主义精神的认识。当然,桥本文雄也给予了社会法的群体主义属性。第九章、第十章对社会法缘起与萌芽的讨论中,其所论及的日耳曼部族法、伙伴忠实法、庄园法、封地法乃至行会法、商人阶级团体法等也无不体现非个人主义精神特色。他将这些法律与社会法建立关系,足见他眼中社会法的团体属性。
综合可见,专著虽名为“社会法与市民法”,但其精神实为“从市民法到社会法”。犹如桥本文雄所言,“社会法的特征存在于与市民法的对照性之中”,他在社会法与市民法的比较中阐释社会法,可以说是抓住了社会法的根源问题。
经济法学界、劳动法学界都将经济法、劳动法的起源或缘起归于工厂法或劳动者保护法等。桥本文雄也将社会法的萌芽归于此,并且将社会法的发育和形成也集中在劳动与社会保险法上。显然,这种社会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化”与社会法的团体属性并不完全吻合。当然,他在论述“日本的社会法”时,虽主力在劳动与社会保险法,但仍有少许内容扩张到了公益企业法、日本社会立法体系等内容上。社会立法实践被称为法律的社会化实践,实质是市民法的社会化即以社会公益为目的对市民法内容的限缩。显然,市民法的社会化并不等质于社会法。
从个人个体到社会整体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市民社会中只有私人即市民,人都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所有私人都以自己私利为目的。由此,他人是自己的工具,自己也成了他人的工具。市民法就是市民社会这种私人社会的反映,如专著所言“作为私法的民事法的市民法”。在市民法中,个人享有权利能力而成为独立的权利主体,人作为独立的个人获得法律保障。可以说,没有市民法,个人就没有作为独立个体、作为权利主体的法律根据。从这一意义上,市民法是自然人的“生存之法”。
在市民法中,私人都是孤立的个体、分立的原子,都受利己主义支配。但私人的需要能力和理性能力等因人而异,利己能力因此千差万别。利己主义支配下的个人之间难免出现“弱肉强食”之果,但这就是市民法所承认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市民法可谓是“适者生存之法”。在这种“适者生存之法”中只有作为私人的个体,因而其人际关系也只有“我”与“你”、“我”与“他”、“你”与“他”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我”与“我们”的关系。“我”“你”“他”的个体利益获得推崇,“我们”的整体利益难觅其踪。质言之,社会公共利益会成为市民法的牺牲品。
人不只是个体性的自然生物,更是群居性的社会生物,人的“类”存在才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体现。人的“类”存在显然不是自然的个体存在,而是社会的整体存在。作为自然个体存在,需要有“我”“你”“他”的个体私利,作为社会整体存在,需要有“我们”的社会公益。因此,如果说市民法是私人(或称个人)的个体性法律,那么社会的整体性法律就是社会法;如果说市民法是追逐个体私利的法律,那么社会法则是谋求社会公益的法律。由此,社会法有着对市民法的制衡作用——对适者生存的制衡。同时,社会法对市民法也有着协同作用——实现人的自然性生存的同时实现人的社会性生存。
究竟何为社会整体?这就是桥本文雄所引用的拉德布鲁赫的“社会人”。与市民法中自然人概念相对的是社会法中的社会人概念。自然人就是经济学中追逐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桥本文雄言,“市民法不承认作为个人的劳动者因无力与企业主对抗而结成劳动者团体的连带性”,这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视野。因此,“不能着眼于单一的个人,还要观察劳动者的团结性与雇主的经营性”。其中,劳动者团体、森林、劳动者的团结性体现的是社会人的整体内涵。社会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个人,而是联合的社会共同体如婚姻共同体、家庭共同体、劳动者团体、因环境因素形成的环境共同体等。
社会人即各种社会共同体整体性地享有某种社会公益、社会权,其中的社会成员则分享着社会公益中的“个人利益成分”、分享社会权中的成员权。在社会人整体中,成员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而仅作为整体的构成部分而存在。如婚姻共同体中,夫妻并非作为各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而仅作为婚姻共同体成员而存在。社会人与成员之间、社会权与成员权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非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彰显了“身份”在社会共同体中乃至在社会法中的回归,因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近代过程是从“身份”的极端走向了“契约”的另一个极端。
(作者系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键词阅读
- 人的私利与社会道德2023-09-04
- 翟学伟:时代发展太快,如何重建中国人的社会信任2023-02-08
- 保持多元社会特质与超越差异2023-02-01
- 保持多元社会特质与超越差异2023-02-01
- 私人生活的法律社会史2022-12-07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