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图书
-
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52.00
李公明 语言的毒性与……SOS呼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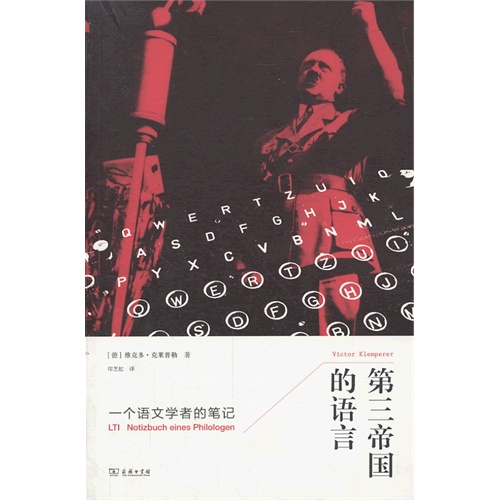
关于第三帝国所使用的语言问题,不少德国史研究论著都有所论述,但是像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印芝虹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这样的专著,在中文出版物中恐怕还是不多见。对思考语言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的读者来说,这个论题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不言自明。然而,这本书并没有期待中那种对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的时候常有的流畅与明晰。相反,正如弗瑞利希的“代后记”所言,“LTI是一本多层面的书,也是一本艰难的书,它在诞生之际已经为其作者制造了很多难题,他既无意视它为辞书,也不想当它是语言学作品,而愿意以之为经历之书。”(第385页)因此,应该首先思考这种“艰难”的内涵与缘由。
首先,“这本书来自于对日常观察的记述,自然包含许多自传成分”(同上)。那么,了解这位语言学家的经历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他的生平经历,最详尽的资料就是他本人坚持写了六十年的日记。这些日记在1995年正式发表即引起轰动,不但使《第三帝国的语言》重新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对它的看法。弗瑞利希认为由于这些日记的发表,“学者们认识到,仅仅局限于‘第三帝国的语言’的阅读过于肤浅,这本书更应该理解为‘社会语言学分析’的最初尝试。……对于作者来说,一切都是国社语言,无论是纳粹的言语表达还是非言语的表述。因为将非语言的事物纳入意识形态传播,克莱普勒成为一种新的语言和文化分析的先驱”(第390页)。在此之前他还指出,克莱普勒把全部日常环境都作为观察视域:政治演讲,致意的新方式,文章和广告,收音机里的战事报道,行进的队列和国社举办的其他的大型活动,也包括高速公路和庞大建筑,甚至议会大厦之火——“这一切都是第三帝国的语言”(第387页)。这种语言与非语言的交织分析,的确是本书非常吸引人的地方,但同时也是时遇艰难的地方。当然,无论如何了解他的经历,由于个人的经验总是缠绕着各种具体情境,语言在其中的发生、运用充满了往往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的奥秘之处。
其次,认真阅读全书后,我认为它的“艰难”不仅来自于克莱普勒的经历的混合,也不止弗瑞利希所指出的克莱普勒将对第三帝国语言的观察置于他的语言观念主义的和民族心理学的思考中心,同时更在于作者以其文化史、思想史的素养追根溯源地研究第三帝国的语言现象。比如,作为艺术史研究者,我很感兴趣的是,作者在论述了印象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区别之后指出:“突出意志的和风暴席卷式的语言形式,是第三帝国的语言从表现主义那里继承来的,或者说,这是它们共享的语言。”(第62页)又比如,关于第三帝国的种族主义,克莱普勒在“德意志之根”这一章中认为“那个被幻想成为日耳曼人的特权和人之霸主地位的种族学说,最终成为施予人类最恐怖的罪行的狩猎券,它的根子在德国浪漫派”(第134页),并一再强调这种联系。由此而言,该书也有着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特征。
克莱普勒一开始就强调纳粹宣传的重要特征是依赖最基础的语汇,而非长篇文章或演讲:“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第7页)从他称为最早的纳粹语汇“惩罚性袭击”开始,然后是一长串的语汇:“国家庆典”、“狂热的”、“世界观”、“体系”、“组织上”、“阳光的”、“全面的”……他深刻地指出:“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它们不知不觉地被吞食了,似乎显示不出任何作用,而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毒性就会体现出来。”(第8页)
这些语汇的来源是纳粹化的历史进程的伴生物。“《我的奋斗》,国家社会主义的圣经,1925年开始出版,从此,第三帝国语言所有的基本特征已然确定无疑。当这个政党‘接手政权’之后,这种语言就从一个集团的语言变成为一个国民的语言,也就是说,它掌控了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生活领域:政治,法庭判决,经济,艺术,科学,学校,体育,家庭,幼儿园和托儿所。”(第12页)“纳粹语言改变了词语的价值和使用率,将从前属于个别人或者一个极小的团体的东西变成了公众性的语汇,将从前一般的大众语汇收缴为党话,并让所有这些词语、词组和句型浸染毒素,让这个语言服务于他们可怕的体制,令其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最公开的、也是最秘密的宣传蛊惑的手段。”(同上)
这种语言的风格要求就是贴近民众,用戈培尔在1934年党代会上的讲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必须说人民懂得的语言”(第232页)。在他的宣传口号中,“人民”泛滥:“人民的同志” (Volksgenosse)、“贴近人民”(volksnah)、“心系人民”(volksbewuBt)……作者说这种对“人民”的强调“听上去有某种虚伪与无耻”(第241页)。
克莱普勒是在东德时期完成和出版这部著作的,但“在此期间,克莱普勒似乎丧失了他对语言的所有敏锐,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使用着共产党人的宣传套话,并对斯大林极尽颂扬。而他有些时候一定是十分绝望的,这仅从他战后日记的标题上就不难看出:《我就这样坐在所有的椅子之间》。”(弗瑞利希,代后记,第386-387页)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当刚刚还在如此敏锐、深刻地分析和批判的那种语言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体系化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因素使这位语言学家闭上了他的眼睛和塞住了他的耳朵?
其实,在书中可以发现,克莱普勒在谈到“同一化”和“灵魂的工程师”这些语言现象时曾认为,“两者都是技术用语,但德语的这个比喻指向奴役,而俄语的却指向自由。”(第155页)难以确证这种认识是否发生在他1945年加入东德政党之后,但是或许有助于理解他在此期的思想状况。
在回顾语言的社会政治史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当下语言的某种复辟现象,应该再次思考作者“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的告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应该倾听作者向自己发出的SOS呼叫声——“必须消失的不仅仅是纳粹的行为,还有纳粹的观念、纳粹的思维习惯及其滋生的土壤:纳粹主义的语言。”(代序,第2页)因此,“我们应当将纳粹语言中的很多词语置入群葬墓坑,长时间掩埋,有一些要永远掩埋”(第8页)。
- 吕红周 单红《从语言符号学》到《现代语言符号学》2015-08-05
- 赵亮 语言符号的本体观照和语言符号化的动态考量——评《现代语言符...2015-07-16
- 张颖 评王铭玉《现代语言符号学》2014-11-20
- 李公明 “阁下也是一名……沃尔夫主义者吗?”2014-07-22
- 吴冰 英语语言的小百科2014-07-01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