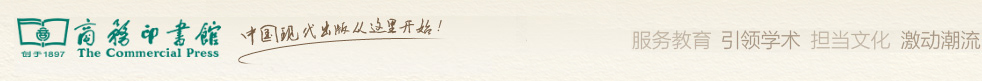

要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认识林纾。
第一点,陈平原教授说,“五四”时期新文化人是少数,保守派是多数,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也很受启发。大家记得吗,深圳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据说,很高级别的领导人去了深圳以后还会痛心地流眼泪,说是深圳除了国旗是我们的,其他都是资本主义的了。一场改革刚兴起的时候,改革者肯定是少数,保守者肯定是多数。而关于保守的问题,我也赞同杜鹏飞教授说的,过去我们把“保守”这两个字当成是贬义的,实际上,保守是保持传统、守住传统,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保守并不是贬义。
第二点,从多数人和少数人来讲,我们去考察一下,现在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主将的主张、作为上,早上陈平原教授说保守是更多的人,那么我们去考察一下,除了林纾之外,“更多的人”到底是谁?“更多的人”产生的思潮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不过是林纾跳出来了而已,其他更多的跟林纾有着同样思想的人没有跳出来,没有跳出来的一部分是文人,还有一部分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们不能写文章。我们从这个方面了解一下,重新来理解林纾为什么反对新文化。
第三点,夏晓虹教授和余英时教授都说了,所谓国学是从日本学来的,日本很早脱亚入欧,他们觉得应该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所以就把传统文化叫“国学”,把西方传入的文化叫“西学”。当年林纾没有去过日本,可是章太炎、郭沫若、鲁迅等一大批人都去过了,他们觉得日本人的“国学”一词用来定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是最合适的。从李鸿章、张之洞开始就着“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这一问题讨论得很激烈,最后觉得还是要用日本这个思路来讲国学。所以,章太炎要开办国学讲习班,要出《国故论衡》和《国学概论》。为什么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会更多地坚持国学,反而没有把国学当作靶子?这些坚持国学的人并没有受到批判,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要从大背景下来重新认识林纾。
最后还有一点,我还是比较赞成王元化先生的一个观点,不知道现在这样提是不是合适,但是我觉得他是对的,就是对“五四”运动的重新思考,他的《思辨录》《九十年代日记》等著作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思想和指导下放开去重新思考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重新认识林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