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两千年来对《史记》的研究中,一些话题被反复讨论,其中即有所谓“互见法”:对同一人物与事件的叙述往往分见不同处,这些叙述多可互相补充,但也有龃龉之处。以《史记》结构之宏大繁复,记述重叠自不可免,但许多学者相信其中一些出自司马迁的良苦用心。
侯格睿所著《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原著Grant Hardy: 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之核心命题即在于此。侯格睿认为,“多重叙事”是导致《史记》碎片化与充满“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不确定性”指由于《史记》叙事不统一甚至彼此矛盾,加以司马迁延续《春秋》“微言大义”传统,寓论断于叙事,刻意隐去作者在场,导致人们难以从书中析出一个明确、普遍、终极的作者观点。
某种意义上,不确定性(“互著”导致的叙述矛盾)、准确性(准确客观地还原历史)和道德寄寓(在史书中寄寓个人的道德评判)构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阻碍人们对《史记》的解读。学者或为其“不确定性”辩解,以为是编纂失误所致;或承认其历史书写的准确与客观性有待商榷;或否认司马迁在书中寄寓强烈的个人倾向。然而,《史记》“互见法”的精心设置、众多史料尤其是近百年考古发掘的佐证、司马迁对《春秋》传统的有意识继承,都让上述否认性观点难以稳固立足。
就此,侯格睿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路径,使三者得以共存:真实世界本身充满不确定性,司马迁忠实还原了这一点,因而“不确定性”未阻碍《史记》的客观性;模拟还原的过程不可避免存在简化,这种简化中蕴含司马迁之历史抱负和道德教化。沿此路径,侯格睿提出“微观世界”概念,延伸而有“青铜世界”与“竹简世界”的隐喻。所谓“微观世界”,指《史记》作为真实世界的复制与模拟,是一个微观的“宇宙模型”。“青铜世界”“竹简世界”分别隐喻(或者说象征)企图死后继续控制世界而模拟宇宙结构建造的秦始皇陵,与司马迁书于竹简以寄托抱负的《史记》文本世界。
一
该书分两部分阐释“微观世界”理论:第二至四章分析为何可将《史记》看作“微观世界”,五至七章指出司马迁如何通过“微观世界”进行道德教化从而改变世界。
《史记》叙事的“不确定性”为西方读者带来了困惑,它“既没有关于历史的统一的认识,也没有关于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的连贯解释”(50页;凡所引用,皆为该书译本页码)。第二章,侯格睿剖析《史记》五体结构,发现其叙事“至少打破了西方传统历史表达的四个关键要求”(71页)。第一,叙述声音不统一,有互相龃龉的情况,也没有一致的观点;第二,《世家》《列传》以外的记事没有连贯性,缺乏前因后果;第三,各部分内容有重叠,需比照阅读多篇才能全面了解一个事件;第四,对同一件事的不同叙述“并不总是一致的”。问题由此产生:“假如司马迁关注精确性,为什么《史记》是一部充斥着不同的叙述、观点和评判的大杂烩呢?”(75页)
对此,前人的解释无外乎以下几种:一、司马迁只是做了材料编纂的工作;二、他自己内心充满矛盾;三、他不追求历史的“统一性”;四、《史记》是半成品,他尚未及完成。侯格睿则作了新的预设,他假定司马迁同样追求“精确性、连贯性、证据和合理性”,而《史记》反映了一个连贯的历史观,碎片化和重叠叙述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从他对材料的安排和具体陈述中看出他的观点和判断”。基于此,侯格睿提出《史记》在重建历史,它是一个历史模型,“一个由文本构成的微观世界”(77页)。
将《史记》视为微观世界,有三个理由。其一,考其背景,先秦两汉时期流行以各种形式的微观世界模拟宇宙,建筑典型如阿房宫,文本典型如《吕氏春秋》等。《春秋》是一个以历史文本形式呈现的世界模型,“将这个世界运转所需要的基本道德法则和历史原则融为一体”(88页)。《史记》延续此传统,代表宇宙的结构,以及微观世界的人类历史总和。其二,《史记》具有综合性,无所不包。其三,《史记》所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开放性正是世界及其历史自身的特征,司马迁“想准确地表达世界及其历史的全部辉煌和混乱”(83页)。当然,《史记》并非全同世界那般混乱,否则写作本身就变得无意义。“模型”的特点在于它会对模拟并还原的事物有所简化与选择。《史记》亦作了某种程度的精炼,来表现“历史的最重要的特征”即不确定性。司马迁“对引用的材料进行考证;使用标准化的年表;选择最重要的史料”,因此“从《史记》中获取意义比从历史本身获取意义要容易得多”(83页)。
具体而言,《史记》如何在结构中表现不确定性,使在不确定性下寄寓历史意义成为可能?
第三章以两个例子说明说明《史记》的各个部分如何一起运作。侯格睿非常重视《史记》的《表》并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切入。通过解读《春秋》三传与《史记》关于州吁事件的记载,侯格睿提出《史记》年表与世家、列传的关系如同经与传。年表“提供了人类历史的上帝视角”,“鼓励读者绘制自己路径的地图”并建立联系和分类,是“司马迁宇宙观的缩影”。《史记》中的叙事则是对表的“传”,“解释了更具普遍性、更具联想性、更具世界性的表”(110-111页)。
在《史记》各部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中,每一卷“司马迁都以略微不同的角度呈现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编辑取舍都反映了他自己的目的”(109页)。侯格睿分析了魏豹叛逃的五个版本,提出导致一个事件发生的原因、一个人的性格,在不同视角下,完全可能是矛盾的,“重要的决定和重大的事件通常具有多重原因”,而《史记》形式“容许一种特殊形式的准确性”(121页)。
在这些“多重叙事”中,事件的重要性并不相同,司马迁通过文学技巧呈现这种区别。第四章,侯格睿分析“项羽刘邦优劣论”,指出他给予事件“意义”的重要方式,就是将事件纳入更宏阔的叙述(即《史记》的大框架)中。而宏观叙述中事件的意义非常丰富,司马迁“不是没有提供答案;相反,他提供了太多,他顽固地拒绝给出一个最终的、全能的观点”(142页)。
总之,《史记》作为真实世界的模拟,“准确地”还原了世界的“不确定性”,同时又作了提纯,使得在其中获取意义成为可能。
(汉)司马迁著,(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
二
“不确定性”与“准确性”的共存成为可能后,侯格睿继而于第五章提出,“微观世界”理论还能回答历史书写“准确性”与“道德教化”的共存问题。
“司马迁想要追随孔子历史编纂的两个原则:完成一部尽可能准确的历史,同时以强调道德教化的方式去写作。”(184页)而他的根本目的在于后者,准确性只是“揭示过去道德意义的一种手段”(245页)。然而,客观准确的历史记录和寓含道德训诫的写作往往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回到我们把《史记》作为世界模型的概念上可能是有用的。我们问一个模型的制造者,模型是代表对象还是塑造我们对它的看法,答案是两者兼有之。模型是一种工具,其功能在于它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以及它简化或突出其客体的某些特征的能力”(184页)。那么,《史记》模型如何简化真实世界,并从中得到了什么意义?
侯格睿指出,通过对史料的编辑安排,司马迁实现了事物的“正名”,其目的是回应现实世界善恶报应不公正的问题,惩恶扬善,从而体现道德教化,重塑世界。侯格睿介绍了司马迁《史记》的十二条微言大义,包括是否收录一条材料、其在卷中的位置与标题如何处置等。“所有这一切背后的认识是,通过正名可以重塑世界。”(202页)
这种“正名”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保留了对世界的“真实性”还原,没有凸显作者的介入:“既可以保持对史料的忠诚,又可以将作者的侵入降到最小化,同时保留了非凡的解释能力和界定因果关系的能力。”《史记》成了司马迁的一种“诠释工具”,其结构并不能作单一解读,如同多重叙述一样,它提供了许多不一致的组织线索,司马迁本人没有明确的观点,他与读者一样试图理解世界(192-193页)。
第六章中,侯格睿通过对《孔子世家》的分析,指出司马迁通过“选择、并置、重复、并行、对比以及情景化”等文学叙事方法,塑造了他所敬仰的孔子形象。这说明在未违背史实的情况下,“文学叙事”可以影响我们理解事件与人物的方式,这使司马迁能够在保持“准确性”的同时寄寓他的道德观。
三
通过准确地模拟世界的不确定性,司马迁寄托了他的道德抱负。那么,司马迁牺牲“自己的名誉、尊严和男子气概”去重建道德的目的是什么?第七章中,侯格睿认为司马迁希望通过“竹简世界”与秦始皇通过暴力建立的“青铜世界”秩序相对抗。
“青铜世界”从三个层次隐喻秦始皇所代表的政治秩序:一、喻指武器,象征暴力统一,这种统一不仅在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上,也在意识形态上寻求统治权,“试图改变人们理解世界的范畴,最重要的是,他(秦始皇)希望自己能够定义世界”(251页)。二、喻指青铜器,象征金石铭文,代表秦始皇进入另一个青铜世界的努力,“一个通过操纵神圣的青铜礼器而建立和维持的概念世界”(262页)。三、喻指秦始皇陵,秦始皇陵“采用了宇宙模型的形式,包裹在青铜保护之中”,象征秦始皇在死后继续控制世界的野心。
在此背景下,司马迁意图“点对点消除秦始皇的意识形态结构”(267页),“借助《史记》篡夺秦朝武力建立的世界秩序。与秦始皇凭借强制和暴力相反,司马迁试图通过重建道德作为管理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基础”(247页)。在司马迁看来,汉武帝如同秦始皇灵魂再世,“青铜世界在司马迁时代的掌权者汉武帝身上复活,他再次走上了扩张的、积极的集权化进程”(273页)。司马迁以《史记》抗争汉武,其“支离破碎的结构本身就是对中央集权的否定”。但他真正的目标不在汉武本人,而是其所代表的独裁统治,“他的真正目标是秦始皇。他的目标是推翻青铜的世界模型”(275页)。他不仅用《史记》谴责秦汉过度集中的权威,而且通过撰写通史的行为,“为各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反叛者提供所需的‘知识弹药’”(278页)。
在司马迁的世界,有两股争锋相对的势力:以秦皇、汉武为代表的暴力统一与政治独裁,以及以孔子为代表,司马迁本人所继承的儒家道德传统。通过史料的分类编辑来“正名”,司马迁将“礼”引入他所建构的世界模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宣扬道德榜样和礼的优越性超过了严格的法律和刑罚,这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的策略。最终,他的竹简世界的变革力量打败了秦始皇的青铜政权”(279页)。
四
书中,《史记》客观性与司马迁的道德寄托之间的矛盾是作者特别关注的一个命题。虽然作者的目的在于证明《史记》寄寓了司马迁强烈的个人理想与道德抱负,但是他也强调司马迁呈现这种寄托的方式非常隐晦。
在前言中侯格睿即指出,与“希腊古典史学传统”不同,《史记》中作者缺席了,“司马迁拒绝用自己的声音和基于自己的判断去重建古史,对西方的读者而言,这是一个严重的缺失”(第3页)。比起对《史记》“互文”的敏感,“作者的缺席”这一点被浸淫中国传统史学的学者长期忽略。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相比其他正史,《史记》缺乏应有的客观性,带有司马迁过于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是一部“谤书”,“无韵之离骚”。而侯格睿基于西方古典史学传统考察,指出古希腊历史学家(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言说”历史,面对的是现世的观众,为说服他们,需要论点与论证,通过合理的推论,接近历史的真实,因而也就具有“我”之色彩,“处处有一个我在”。《史记》则像一个“微缩世界”,在“呈现”历史。笔者以为,如同上古巫史传统,史书是记给“天”看的,历史的写作本身就是抵达天道的方式,司马迁不追求以历史的真相说服何人,而是“藏之名山”,待之“后世”。他的历史书写是为“理解”世界及其历史,《史记》展现了他“表达历史——理解世界——改变世界”这一过程。
司马迁没有一个预设的历史意义,他并不期望《史记》为历史事件下定论。他建立微观模型来自然地呈现这个世界,“不确定性”使这个模型复杂多元,无法被简单、单一地解读,从而引导读者以全新的方式反思和阅读历史,自行发掘其中的规律。历史并非等待解码的编码机,读者的目的“不是积累关于历史的所有事实,甚或得到关于历史的正确解释;没有一个正确的被编码的信息可供发现。这是一个对证据的给予和接受,以及学习阅读的过程,这是历史研究的真正目标”(298页)。司马迁《史记》微观世界之所以堪称伟大,历久弥新,也正是因为其复杂性、多义性、不确定性,“一个连贯的、清晰的且内部一致的模型易于过时,但是一个复杂的、有些矛盾的系统可以适应新发现的事实和新发明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不仅塑造其后二千年的史学传统,而且塑造了人们阅读与理解历史的方式:“《史记》的结构不但要求而且描述了一种特殊的阅读模式,这种阅读模式构成了后世中国人试图理解世界的基础。”(94页)
五
侯格睿在书中所提出的多数观点,分别来看,并无甚新意,其前其后的学者都有所论述。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国内史记学史上最早以章节体全面评介司马迁及其《史记》的专著,书中所言多有与侯格睿该书相合之处。如就司马迁与汉武帝两相对立而言,李书称:“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征服一切的。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士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商务印书馆,2011年,23页)就《史记》之结构如同复杂建筑而言,李书亦有相关表达:“《史记》一部书,就整个看,有它整个的结构;就每一篇看,有它每一篇的结构。就像一个宫殿一样,整个是堂皇的设计,而每一个殿堂也都是匠心的经营。”(同上,260页)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开明书店,1948年
此外,史源问题导致《史记》多说并存,是史记编纂学上的共识,赵生群指出:“传疑缺疑是《史记》处理史料的一个重要方法。史料来源不一,而一时又无法判断其正确或是谬误,故两说或多说并存,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赵生群:《史记编纂学导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146页)就“不确定性”有益后世读者进一步反思历史而言,韩兆琦称之为“矛盾中显真实”,“《史记》的几篇之间,甚至在同一篇里有意地参错其词,留着一些明显的疑窦,让后代细心的读者自己明白其底蕴”(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就不明确表达观点而言,顾炎武《日知录》已明白指出“寓论断于序事”,并被此后学者接受。姚大力在其近著《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中进一步指出:“司马迁所谓‘述故事’,可以说有一点‘让历史自己说话’的意思。但更准确地说,他其实是要让历史按他所理解的方式来自行说话。而支撑着其理解方式的最基本观念,应当就是他对历史过程论的自觉意识……作者似乎无意从这个过程中去寻找某种单一的、简单化的、带有终极原因色彩的变化推动力。”(姚大力:《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143页)姚书对《史记》通过整体结构而呈现出来的历史复杂性亦有论及:“《史记》的贡献,其实并不在于它独创了以上种种记录体裁及其名目,而是在于对它们加以创造性的利用,从而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综合的历史叙事,构成一种有意识地展现其变迁过程的、多层面的、并且包含着不同文化实体的多元历史。”(同上,124页)
侯书的新颖之处在于将诸多对《史记》的零散观点以“微观世界”模型统合,形成了一个连贯的解释。这种留意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的互动,把文本视为一个自在的世界,将其复调结构隐喻为世界模型的思维方式,是属于作者的独特思考,前人万不会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其将《史记》结构问题与司马迁的创作动机联系在一起,更是颇为大胆的想法。通过这样的隐喻或说象征,侯书能够呈现一幅更完整的《史记》画面,解决一些别的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本文所申说的不确定性、准确性和道德寄寓之“不可能三角”。
侯格睿“微观世界”观点的提出,得益于他综合性的学术素养和比较史学的视野。作为美国当代《史记》研究的重要学者,他承续了欧美汉学界特别是沙畹、华兹生、杜润德以来史记学界的学术传统,将《史记》的研究置于中西史学的比较之上。他如此关注《史记》叙事的不确定性问题,就源于东西方史学的不同。由于中国两千年史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自《史记》,其以五体结构和“互见法”等为特征的历史写作对中国学者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西方史学传统如此迥异于这种写法,读者初次面对《史记》时便充满困惑,无法理解这种没有统一的叙事主题、叙事逻辑、叙事观点的历史写作,从而认为《史记》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砌与编纂,甚至怀疑《史记》作为一部伟大历史著作之地位。为了使《史记》之伟大被理解,侯格睿需要指明异于西方史学一贯性与明确性特点的《史记》特点在哪里,应当如何理解它。“比较史学”在杜润德身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在古希腊和古典中国文化的比较中,杜氏就指出:“由于希腊史家意在表达特定的主题或讲述特定的故事,因此他们必须采取统一的结构。与之相反,中国史家扮演的角色更接近编撰者或传述者,他们把原始材料连接在一起,试图激发某种特定的观感。”([美]尚冠文、杜润德:《海妖与圣人:古希腊和古典中国的知识与智慧》,吴鸿兆、刘嘉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164页)虽然他的观点与侯格睿相异,但在研究方法上,可说如出一辙。
Stephen W. Durrant, 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美]尚冠文、杜润德:《海妖与圣人:古希腊和古典中国的知识与智慧》,吴鸿兆、刘嘉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六
整体而言,本书所呈现的“竹简世界”观为解读《史记》拓展了新的视野,不过仍有一些疑问有待解决,譬如世界的“时空性”问题。现实的世界是时空一体的,在空间中活动的人事同样也在时间中变动,不过两者之中,“空间性”显而“时间性”隐,时间本身是无形的。而作为一部史书,“时间性”是其关注的核心,历史就体现在“历时性”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是空间性的,而《史记》是历时性的。在司马迁之前并不存在整体的连贯的历史,从历史中“通古今之变”,寻找变化规律,是司马迁的伟大创造,也是《史记》的“野心”之一。当我们用“微观世界”模型来看待《史记》文本,特别关注于它的结构时,容易忽略它作为一部史书的“时间性”。侯格睿自身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往往有“世界及其历史”一类措辞,并且说道:“尽管绝大多数宇宙模型都代表着空间关系,《史记》努力传达时空连接和社会等级,它也设法将人类经验的基本要素以类似于其他模型的方式融入其中。”(81页)但“世界模型”的比喻无法传递动态的“时间性”过程,从形象上来说囿于静态的空间,或可算作该比喻的遗憾之处了。
其次,如前所述,侯格睿对《史记》的解读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我们看到的碎片化和重叠叙述是司马迁“故意的安排”,但此一假设终究无法确证。至少侯格睿在书中提到的前辈杜润德就不大认同这个观点:“只有那些不顾一切地把司马迁当作一个全方位的历史学家来崇拜的人,才会为他辩护说,这位汉代历史学家曾经用心地考量过,在大部分出自那本‘元国策’的种种巧妙的阴谋故事里,究竟哪些才是经得起推敲、因而值得写进严肃的历史叙述里去的。”(Stephen W. Durrant:The Cloudy Mirror: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p.103-104,译文转引自姚大力《司马迁和他的〈史记〉》,141页)因此,“司马迁想要为我们呈现什么”“他呈现了什么”以及“读者从中读出什么”,本书其实可算回答了后两者,在阅读时不应混淆。
本书的写作聚焦在《史记》文本之中,就横向来说,若能比较《汉书》与《史记》之异同,或许更可见《史记》所蕴含的司马迁个人抱负与道德寄托;若能使用更多的学界考古成果,对司马迁之真实性或有更大的说服力。就纵向而言,侯书对近百年来国内学者的《史记》研究成果引用并不广泛,这也是无可避免的遗憾。目前史记学研究上,中外学界的交流依旧缺乏,外少引中,中不见外,国内学人即使有所关注,亦多集中于日本史记学界(可参张新科:《史记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33-36页)。好在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此问题并积极展开交流,这套“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丛书”就是一个非常必要且重要的努力。
在“微观世界”理论看来,《史记》既不像西方史书和现代史学著作般具有作者强烈的个人观点,也非纯粹的材料编纂,而是处于两者之间;它既表达了司马迁的观点,又“没有”表达;它既是不确定的,又是确定的……总之,处于一个“悬置”的中间状态,这种状态难以把握,稍不留意便失去平衡。从目前成书来看,侯格睿把握到其微妙之处,并将之清晰地呈现给了我们。该书初版于1999年,在欧美汉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倪豪士等学者均有书评讨论(W. H. Nienhauser [2000], Review of 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 by G. Hardy,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2, 155–168. https://doi.org/10.2307/3109448)。现商务印书馆将之收入“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译丛,由学者丁波翻译,对于拓宽海内外学界交流并推进《史记》研究,可谓功莫大焉。
原载于《澎湃新闻》2022年8月23日
作者汪斌系南京大学文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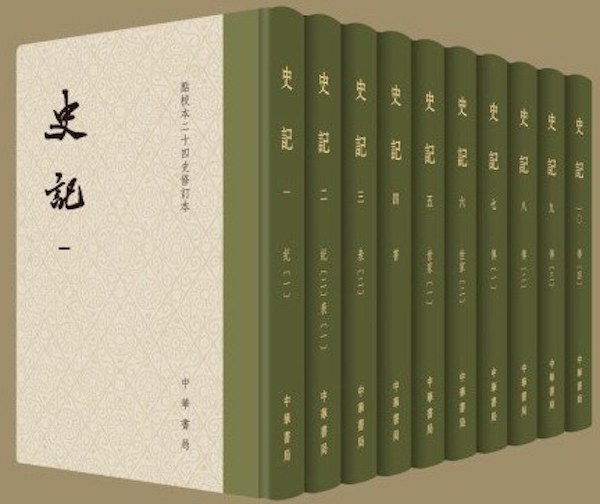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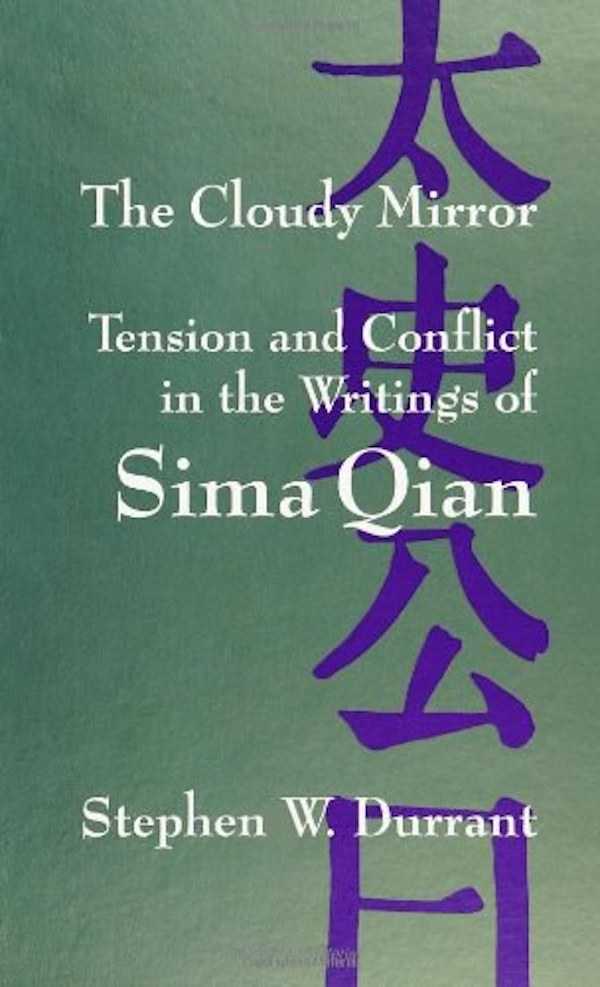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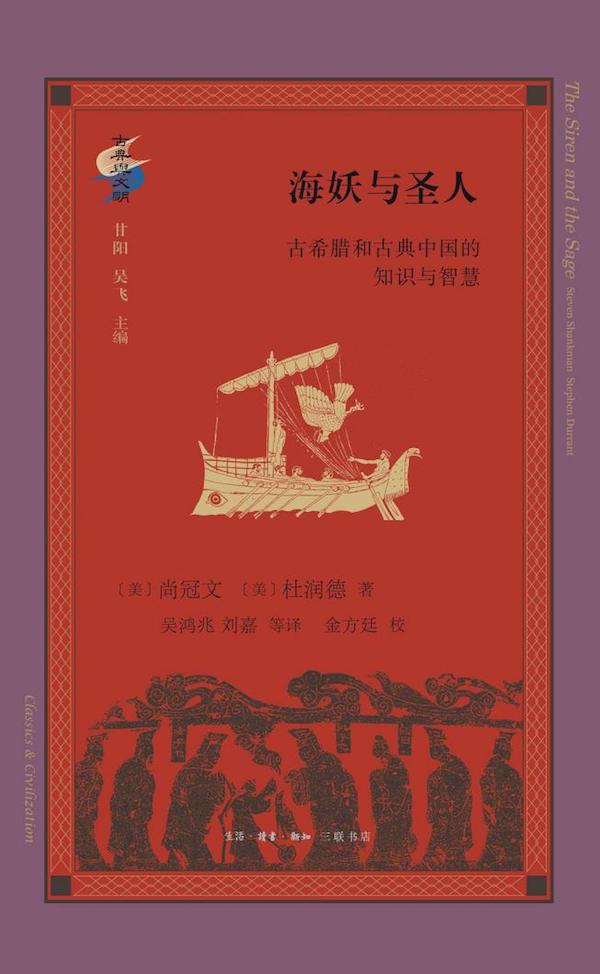
![]()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