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图书
-
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260.00
立于修昔底德陷阱之前
2023-07-11作者:徐之凯刊发媒体:上海书评浏览人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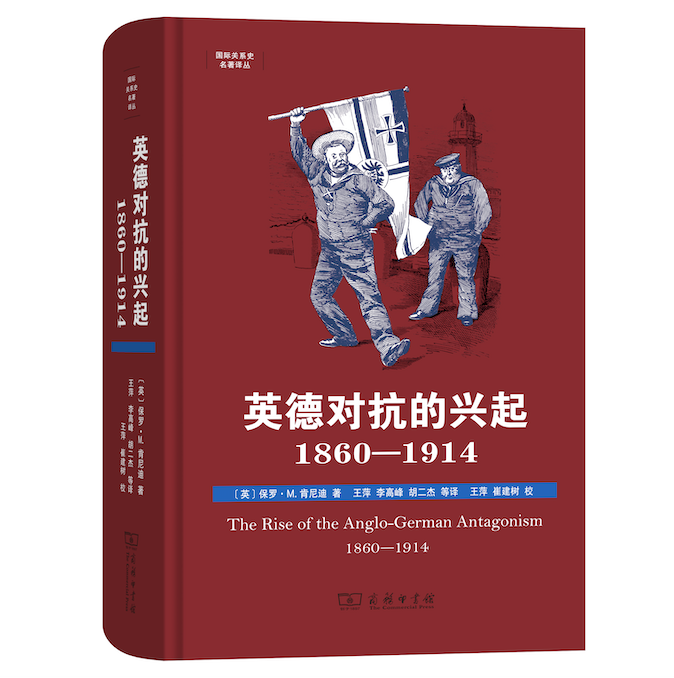
《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旷世名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作如是说。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据此提出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声称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然而,新颖的词汇难掩陈词滥调。对于广大历史学者、国际关系学者而言,这一“创新”论断如此耳熟能详,足以让这样一个名字重新浮现眼前——保罗·M. 肯尼迪。
身兼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与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长,1945年出生在英格兰的保罗·肯尼迪可谓是英美当代国际关系史的中流砥柱,其研究贯穿帝国史、殖民史、海军史、英德关系等。早在1973年,二十八岁的肯尼迪便以《萨摩亚的纠纷:对1878-1900年英、德、美关系之研究》一鸣惊人,此后又连续出版了《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衰》(1976年)、《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1980年)、《外交背后的现实:1865-1980年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1981年)和《战略与外交》(1983年)。其中《英德对抗的兴起》被西方学术界评论誉为“一方面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关系背景的变化,另一方面有力地叙述了个人和杰出人物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说,肯尼迪起自萨摩亚问题的多边关系研究,在英德对抗的互动追溯中明确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与研究视域,最终在1987年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集于大成,跻身当代史学研究大家之列。而商务印书馆2022年编译的这部《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无疑正是保罗·肯尼迪形成中的以大国兴衰、海洋战略、工业实力与全球外交为重的治史观念的深刻体现,在深入探讨了两个大国走向对抗并将世界拖入战争的历程同时,展现了作者对于国家竞争、社会互动、全球殖民、经济整合等永恒时代话题愈加深刻的分析与反思。
肯尼迪的“英德关系”竞合建构
作为一部国际关系史的力作,肯尼迪的《英德对抗的兴起》旁征博引了大量材料,形成了一部鸿篇巨制。得益于英美高校学会背景身份,他能够在七十年代大量接触多国各类档案史料,与历史事件参与者或其后代直接接触交流,更能与书写了《从庇特到索尔兹伯里的英国对外政策基础:1792-1902》的坦伯利、《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的A.J.P.泰勒等史学大家坐而论道。这使得《英德对抗的兴起》成为一战前英德关系研究的集大成者,更是后来研究者难以逾越的权威。书中,保罗·肯尼迪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英国和德国人民在此前从未兵戎相见,而且他们的政治合作传统因王朝、文化、宗教和经济联系得到强化,但为何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渐行渐远,并且在1914年大打出手?基于此,他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把英德关系作为整体进行全面论述之上,希图以大量全新的未刊资料文献超越之前的诸多作品,并通过全新的结构予以呈现。这使得最后诞生的这部作品就传统史学书写来看十分怪异:初段叙述(1861-1880的英德政治关系)首次结构性检验(俾斯麦和格莱斯顿时代的英德关系结构);中段叙述(英德政治关系走向对抗,1880-1906)第二次结构性检验(比洛和张伯伦时代的英德关系建构);以及终段叙述(从对抗到战争:英德关系,1907-1914年)。

保罗·M.肯尼迪
在这一结构下,初涉此研究的读者会对肯尼迪的笔法一头雾水:1861年的普鲁士尚在筹划王朝战争,何来德国?所谓的政治关系叙述与其后的结构性检验又有何关系?一般来说最为浓墨重彩的终篇为何如此简短,在全书二十二章中仅据一章?这要从肯尼迪对此书的目标定位来理解。事实上,标题中的“兴起”一词翻译未竟其意,译为“缘起”更合乎其原旨。肯尼迪要分析还原的,并非一个众所周知的英德对抗的结局,而是两国间渐行渐远的过程,故而一切相关铺垫都被其纳入论述,并在结构性检验中加以条分缕析:经济联系、党派立场、媒体舆论、社会宣传、宗教文化、君主态度、政府政策,不一而足。尤为值得重视的是,肯尼迪特意将比洛与张伯伦在德国、英国执政时期的殖民地政策、海军建设作为新要素纳入论述,显示了他本人在殖民史、海军史方面的重视和特长。
正如肯尼迪本人所言:“历史之网天衣无缝,从中孤立地抽取任何线头都明显会造成历史的扭曲失真。”(58页)本文自然也无意去妄自摘录这部大作中的无数观点论述,而是回到作者的问题意识本身:1861-1880的英德政治关系为何没有导向破裂?作者的解释是虽然竞争导致了“自由主义的衰落”,引发了彼此间的嫌隙乃至仇恨,但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差异”并不足以将其推向冲突。两国的政治强人给时代打上了印记,“俾斯麦主义”“格莱斯顿主义”虽然导致了龃龉,却也抑制了两国滑向战争。而在1880-1906年,“官方思想”(568页)的混乱体现了两国内部决策的派系紊乱与互动应对中的矛盾积累:各方势力过于平衡,导致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政策,不同的分支集团都各行其是,最终只能留下“悬而未决”的烂摊子造成隐患:德国方面,外交部认定的劲敌是外交上长袖善舞的法国,总参谋部军官团眼里的是兵员庞大的俄国,蒂尔皮茨打造的海军则以英国为目标,整个决策集团莫衷一是;而即便在一战迫在眉睫之时,英国阿斯奎斯政府还在是否支援法国的决策上玩“决定不予决定”(decide not to decide)的“再议”戏码。在这种变相摆烂的情况下,两国又都面临工人阶级的兴起,经济压力集团的煽动蛊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势必推行兵临城下的“城堡和平”,以对外战争威胁国内团结,反过来也就会造成与他国对抗的升级:英国捍卫海上霸权与德国“舰队政策”发起的海上军备竞赛正是其中写照。
为什么是德国?
肯尼迪建构了一整套复杂结构来阐述英德竞合关系的长期变化,但也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德国?若谈“世界政策”全球拓殖,法俄不遑多让;要讲“舰队政策”争夺海权,美日未落下风。可为何是德国成了英国的要敌,使得英德矛盾成为引发一战的主要矛盾?肯尼迪尝试从工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找到答案。他认为,经济原因影响最为深刻,但并不意味着是因为两国间直接的商业竞争引发了对抗:恰恰是担忧资本安全的金融家银行家拉住了军火商、极端民族主义者支起的战车。经济的影响是宏观的、长期的、间接的:统一后规模巨大的经济扩张,使德国不仅在欧洲破茧而出,还具备了一个世界大国的早期特征——蓬勃兴起的海外贸易、对国外影响力的渴求、攫取利益的殖民地以及不断扩大的商船队背后的保障——海军。这个新兴的、充满生机的高效军事帝国不是在远东,也不是在大西洋另一端,而是在近在咫尺的北海。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英国自身贸易、殖民与海上地位的削弱,也就需要扩大出口、进一步殖民并建造更多舰船从而保持最初的相对地位(612页)。事实上,通过这一论述,肯尼迪含蓄表达了自己对一战起因的宏观理解:1914-1918年冲突的根本起因在于,英国希望保持自己掌握世界霸权的现状,而德国出于进攻与防御兼有的诸般动机,正着手改变现状,战争爆发不过是这一调整过程的意外和结果罢了。而被迫要进行这种自我调整的不仅仅是英国,而是德国所有的邻国,以适应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随着德国经济潜力迅速开发,欧洲权力政治的平衡将受到不可避免的影响,这也正是未来战争从欧洲开始波及全球的原因所在。
毫无疑问,这一理念恰如“修昔底德陷阱”。但保罗·肯尼迪的不同之处,在于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责任主要在德国一方:“如果德国的领导人没有那么坚决地在1897年之后改变海上均势,并且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不向西发起进攻,那么英德间的冲突原本是很可能避免的。”(615页)然而这一设想无疑是异想天开的,且不论1897年蒂尔皮茨如未上台,所谓的海上“均势”实际是英国海军相对于“法俄双强”标准的霸权;向西进攻本身是德国总参谋部“施里芬计划”应对两线作战的要求,而此时的英国战略重点就致力于让德国陷入两线作战,且早已开始部署英国远征军支持法国与德国交战,以防1905年后的孱弱沙俄在东线崩溃后局面不可收拾。换而言之,除非德国束手待毙,否则必然要在英德冲突中承担“责任”。甚至连肯尼迪自己也认识到牵强之处,解释道英国也并非无可指摘,诚如丘吉尔坦言:“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所有领土,它幅员辽阔、宏伟壮丽,主要依靠暴力获得,并通过武力维持。我们希望不被打扰地安享这些属地,可是这样的要求在其他人看来并没有那么合情合理。”但肯尼迪又为此辩护:英国实际上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帝国,并允许其殖民地对外开放,成功地“使其国家政策同全人类共有的普遍欲望与理想协调一致”。(Arthur J. 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Vol. 1: The Road to War, 1904–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322)在“日不落”“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之下,“德国那种以牺牲邻国利益为代价增强自身的欲望,不能因为其他人早年的不义之举就可以得到原谅”(616页)。然而,既然英国的不义不能掩盖德国的责任,那么德国的罪责也不能免去英国的责任。可是,保罗·肯尼迪并未再就此深入。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保罗·肯尼迪的这部作品也不能免俗。《英德对抗的兴起》于1980年出版,正值冷战苏攻美守之际。一年后苏联剑指欧洲的“西方八一”军演就将震撼整个西方世界,而里根总统也将在同年即任发起全面对抗。《英德对抗的兴起》虽无一字涉及时政,但其中对自由主义的强调,对英国立场的推崇,以及对统一后德国咄咄逼人的刻画,无不显示出鲜明的时代印记。作为英美高级知识分子的肯尼迪在苏联攻势外交、日德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滞胀的阴影之下,完成了这部作品。他对于世界“原有秩序”的怀念与旧帝国前景的悲观贯穿于此后的作品之中,并且在1987年的《大国的兴衰》中达到顶峰:肯尼迪始终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军事实力和在世界上的地位;以此观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无疑正处于衰落之中。这一观点在当时引发轩然大波,也使得作为历史学者的保罗·肯尼迪声名鹊起。《大国的兴衰》出版后,美国时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甚至特意展开了一次亚洲六国访问,并登报申明反驳肯尼迪的美国正在衰落的观点。
很显然,无论是在肯尼迪口中的英德对抗里,还是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大国都不愿接受后起之秀的崛起,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衰败的悲剧似乎从古至今都在所难免。然而,即便悲观如肯尼迪亦承认,在战争阴霾之下,沙文主义呼声之中,英德之间仍不断有努力,试图让世界转向和平发展的自由贸易体系,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和谐世界共同体”(Harmonious World Community)主张的普遍存在维系了世界和平与两国间的合作,在火星遍地之际极大延缓了战火的到来。立于修昔底德陷阱之前,人们需要智慧越过分歧的陷坑,以合作避过猜疑的尖刺。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跳出列强争霸的殖民时代,放下你死我活的冷战思维,已经成了世界各国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人类社会向前迈进的前提。恰如爱德华·伯恩施坦在1903年12月德意志帝国议会上对军国主义者的怒斥所言:“整个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是以怎样的视角看待一方与另一方的关系,是像满怀嫉妒之心、贪婪的氏族部落那样,即双方是抢劫与被抢劫的关系,还是从国与国之间和平交换的立场出发进行考量呢?”(395页)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