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二十世纪重要古典音乐家 “美国作曲家之首”、奥斯卡最佳配乐奖、普利策音乐奖得主艾伦•科普兰,逾三十年音乐思考结集。
艾伦•科普兰被奉为“美国作曲家之首”。他同时也是一位热情的音乐教育家、评论家,一生写作诸多关于音乐的评论、著作,称自己的文字为 “当代音乐的推销员”。他的著作通常深入浅出,许多古典乐听众,尤其是非专业的大众读者都曾因其文字受益。本书是他个人音乐思想之精华,汇集了三十多年的经验与思考结晶,内容驳杂、深刻又不失趣味,兴许读罢你便会得到深入理解音乐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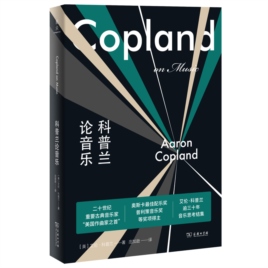
定价:¥58.00
二十世纪重要古典音乐家 “美国作曲家之首”、奥斯卡最佳配乐奖、普利策音乐奖得主艾伦•科普兰,逾三十年音乐思考结集。
艾伦•科普兰被奉为“美国作曲家之首”。他同时也是一位热情的音乐教育家、评论家,一生写作诸多关于音乐的评论、著作,称自己的文字为 “当代音乐的推销员”。他的著作通常深入浅出,许多古典乐听众,尤其是非专业的大众读者都曾因其文字受益。本书是他个人音乐思想之精华,汇集了三十多年的经验与思考结晶,内容驳杂、深刻又不失趣味,兴许读罢你便会得到深入理解音乐的钥匙。
本书是科普兰三十多年来对音乐、音乐家的一系列深入思考之结晶,是他以作曲家视角写成的音乐评论文集。其中回望了过去时代的音乐风貌,也触及当代音乐的若干面向;探讨作为艺术形式的音乐,也带着极大热情勾画历史上重要作曲家,亦有对“音乐”本质的探寻和疑问。科普兰盼望它可以给音乐爱好者,以及音乐创作者们提供更多历史视角,借这本小书,带领读者从其丰富的音乐过往与反思中,汲取灵感和力量。
音乐,人文精神的演绎
Music as an Aspect of the Human Spirit
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我在两百周年校庆庆典上发表即兴演讲,主题是“音乐,人文精神的演绎”。我想大多数作曲家都会同意以下说法:任何一部新作品都是基于某一主题建构而成的、有计划的即兴创作。主题越是宏大,越是危险,越难以在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与表达。今天这个演讲的主题真的很宏大,我几乎没有勇气承担这样的任务。直到我惊讶地发现,事实上,身为一名作曲家,每天困扰我、占据我生活的正是这个主题,即——通过音乐表达人类精神的基本需要。在旁观者的眼中,我记谱时不过是在打了五线谱的空白纸上画些小黑点,仅此而已。但如果停下来仔细琢磨一番,事实上,记谱的过程代表自己正在参与创作,一种身为人类真正独特的成就之一:艺术音乐的创作。回想起来,我参与这项工作已超过三十年,音乐有威严磅礴的表现力,音乐可以彰显人类深刻的精神世界,在音乐面前,我的谦逊从不敢减少半分。
话题如此宽泛,究竟该从哪里着手才好?在此之前,我们或许可以从“什么是音乐”谈起。这个问题已被反复提过多次,却似乎始终没有一个尽如人意的答案。原因很简单,音乐的边界太过宽广,其影响涉及方方面面,变幻莫测,人们很难在单一的定义中函括音乐的一切内容。仅描述“音乐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这一话题,就已十分困难。比如,我该如何向一位聋哑人士描述音乐?该如何解释一个单音与一个和弦所产生的效果差异?又该怎样充分、完整地描述一整部交响作品,确保我们没有遗漏任何信息?我们只知道,基于某种神秘的、不可知的力量,大多数人对有既定音高的、且依照逻辑顺序组织在一起的声音能够感同身受。这些声音或声调,既可以来自乐器演奏也可以来自人声,或单独存在或相互交织,它们促发某种感觉或感情,时而是深沉的感动,时而是单纯的愉悦,甚至有时候叫人烦恼、不快。无论会有怎样的反应,只要认真聆听,几乎没有人会在音乐面前无动于衷。而对于音乐家而言,音乐所诱发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些感觉成为音乐家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絮絮叨叨半日,我深知自己说的这些空洞无味,所触及的实质内容少之又少。人们不可能解释“什么是音乐”,正如不可能回答“生命的本质为何”。如果音乐是超越定义的,或许我们可以因此加以阐释,说明音乐艺术究竟以怎样的方式体现人文精神。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以一种准科学的精神考察自己的创作行为——当我作曲时,我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想法本身有些古怪,因为一个人不太可能在创作的同时跳脱出自我,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自己。这种行为方式的危险在于丢失音乐思想的连续性。同时,我也不能断言自己在作曲过程中有非常明确的想法,通常而言,“明确”这个词用的并不准确。当然,我也并非单纯沉迷于抽象的概念之间,痴想神游。相反,我似乎全神贯注于某种经过提炼的、更趋于本质的情感。我需要强调“提炼”这个词,因为所有这些感受都不是暧昧含糊的。它们总是在作曲家的脑中呈现非常具体的、特殊化的“乐思”。情感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拥有了独特的个性,然而这种个性难以用文字进行界定,任何强大的文本都不能函括它的全部,亦无法将其束缚。这些“原始想法”或经过提炼的乐思(姑且这么称呼)似乎在祈求拥有自己的生命,恳求造物主作曲家们为它们找到理想的封套、理想的家,渴望被赋予外形、色彩及内容,令它们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创意潜能。以这样的方式,人类最深刻宏大的抱负与渴望在不可见的声音织体中得以展现。
奇特的是,声音是无形、不可捉摸的存在,它何以能承载如此多意涵。音乐艺术证明了人类将日常经验转化为声音的能力,这组声音具备连续性、方向性与流动感,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上,以一种有意义的、自然的方式徐徐展开它的生命。音乐永无终结,正如生命本身,可以不停地再创造。因此,人类精神最伟大的时刻得以在音乐的伟大瞬间中彰显。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问,与其他艺术相比,音乐在展现人文精神的过程中呈现出哪些不同?音乐的演绎是否比文学、视觉艺术更富有智慧,亦或者更笨拙贫乏?音乐的存在是否仅仅是为了打动人心?又或者它更多地要求聆听者付出智力劳动,你需要努力去接受理解音乐,而非坐等音乐感化你。我曾经在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中读到一个有趣的段落,宣称美国哲学家担心过度沉迷于音乐会使被动听者萎靡不振。我猜想,威廉说这句话时带着半开玩笑的意味,随后他就此提出了解决之道,“永远不要让自己沉浸于音乐会所带来的情感泛滥中,除非你能在事后以某种有效的方式将这些情感倾吐出来,这跟在地铁里给某位女士让座是一个道理。”与此同时,威廉认为音乐令人萎靡堕落这件事并不作用于音乐演奏者,以及“那些具备极高音乐天赋的人,这些人可以以一种纯粹理性的方式看待音乐。”这个观点可谓赚足了钞票。不过,具有音乐天赋的人真的是以纯粹理性的方式看待音乐的吗?肯定不是!他们聆听自己音乐的方式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只是略有一点差异:他们对音乐及音乐语汇的认知比一个外行听者更为清晰强烈,或许可以说更敏锐些,但也仅此而已。
与其他艺术一样,音乐被设计、创造,旨在完全吸引我们的精神注意力。所有的情感负荷被嵌入富有挑战的音乐织体中,听者必须做好准备,抓住任何需要你特别关注的瞬间去辨识这些情感,如此才不会在音符的汪洋里迷失。有意识的大脑会愉悦地跟随作曲家的创作,如同把玩一粒小球般玩味音乐的主题,从琐碎的细节中抽离出重要的讯息,随着和声的变化上下游弋,敏锐地感知器乐音色的变化,一旦出现全新的色调,哪怕是最不易察觉的色调都能在大脑中反映出来。音乐要求听者具备高度警觉的智识水平,但聆听音乐与智力训练完全是两码事。与音乐相关的精神活动本质上是一场游戏,它确实令一小部分专家或者专业人士着迷不已;然而,如果音乐的节奏型、旋律线设计、和声的张力以及富有音乐表情的音色无法深入、穿透人们最深沉的潜意识,那么一切将不具备真实的意义。事实上,音乐思考促成了大脑与心灵的瞬时结合,正是这种结合直接导向某种情感性的、有特定目的的结果,这也是音乐区别于其他艺术的代表性特点。
音乐的力量如此强大、如此直接,以至于人们倾向于认为音乐在模型建构上相对是静态的,好像音乐一直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样子。如果不把音乐的历史渊源纳入思考的范畴,那么我们几乎不可能意识,也不可能理解西方音乐所走过的非凡之路。音乐学家告诉我们早期基督教会的音乐是单音音乐,也就是说,当时的音乐只有一条单一的旋律线,其中最美的花朵当属格利高利圣咏。试想一番,若在当时有作曲家试图在单个声部的基础上进行多声部写作,那将是多么大胆的举动阿。这个“新颖”的想法大约诞生于一千年前,然而它最神奇之处依然是不断制造惊奇的能力。西方音乐与其他任何音乐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这个方面:我们有能力聆听、欣赏复调织体的音乐,可以区分同时发声却各自独立的声部,以及相互依存的对位旋律线。以全新的对位语法进行音乐思考,追随逐渐铺陈、生长的音乐生命,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体验。顺便补充一句,比起前辈,活在当下的我们更能理解也更懂得欣赏早期作曲家的“反常规”,毕竟我们今天的音乐在节奏与和声上已拥有了极大的自由度。因为有早期对位法作曲家的大胆实验,音乐开始有了情绪与性格,虽然听上去略显僵硬、笨拙,但文艺复兴时代极具丰富性的音乐造型就此诞生。音乐的表达能力在深度与多样性层面不断衍化发展,也变得越来越优雅、迷人。大约到了1600年,欧洲大陆诞生了大量杰出的宗教及非宗教声乐作品,这些杰作标志着鼎盛时代业已降临。需要注意的是,1600年,距离巴赫第一次提笔创作还要早一百年。借由这些多声部音乐,包括人声与器乐的作品,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和声学”逐步得以发展演化。这是极其自然的结果,当独立的旋律线共同发声时便会产生和弦。
随之,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这些合成的和弦以某种恰当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时,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给自足的生命。和声行进好似支撑肉体的骨架,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在音乐作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继而,复调音乐被迫放弃一些线性霸权,与纵向的基础和声相辅相成。两者的关系趋于平衡。
作曲界的巨擎巴赫曾把音乐历史上这个伟大的时刻总结为复调构成与和声驱动的完美联姻。随后的音乐大发展各位都太熟悉了,我们无需在此赘述。我们应当永远记住,音乐的伟大时代并非始于巴赫,而巴赫之后的每一个新时代都为整个音乐历史注入了自己独特的创作视角。巴赫被视为一位集大成者,他对于前人音乐的总结加快了海顿及莫扎特时代音乐风格的确立——一种更为清澈活泼的风格。随之而来的是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狂潮,来自维也纳的音乐大师们轮番登台,热闹非凡;而过去的五十年,人们开始提出“反浪漫主义”,并更多地关注有关音乐技术的话题,音乐在技术层面得以拓展。
沉迷于我们自己非凡的音乐历史不应当蒙蔽我们的双眼,非西方世界同样拥有广博的、丰富多样的音乐语汇,它们大多与我们自己的音乐构成鲜明的对比。非洲鼓激动人心的节奏,近东地区精妙的、情感表达极富戏剧性的歌唱,印度尼西亚叮当作响、铿锵有力的乐队合奏,中国与日本不可思议的鼻音: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我未能提及的音乐,都与我们的西方音乐大相径庭,它们似乎生来就与我们有隔阂,难以理解。然而不管怎样,我们知道,音乐是一面镜子,任何音乐的表达都是在以个人化的方式映射人类意识中的良善。我们大可不必自我设限、画地为牢,更加积极地在我们的艺术与他者的艺术间寻求联络与和解,将使我们变得丰盛;反之,我们的音乐道路必定越走越窄。
同样地,我们也无需将自己的音乐兴趣限定于相对局限的某个音乐历史阶段。平日里我们所聆听的音乐作品大多写于十八及十九世纪,换言之,我们只听这两百年范围内的音乐,除此以外知之甚少。这种情况在其他任何姐妹艺术中绝对不存在,也无法被容忍。与其他艺术一样,音乐艺术包含过去、现在与未来,但与其他艺术所不同的是,音乐世界受困于自身的某些特殊病痛,即——对于音乐自身历史关注的严重失调,所谓的过去是极为狭隘的概念。众多现代听者表现出困惑,似乎他们认为音乐的未来存在于它的“过去”。这种心态必然导致痛苦的、对当下音乐创作的无感与麻木,人们对音乐的现在不再好奇,甚至草率地漠视它的未来。
当今时代,音乐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张的态势,成为大众娱乐的重要领域构成,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相应地,公众对于音乐艺术的态度问题变得至关重要。自从严肃音乐在电台广播中出现,随着广播工业的扩张,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聆听革命正在上演:人们开始习惯通过电台聆听复杂的电影配乐、电视歌剧及芭蕾舞剧。严肃音乐不再是某一小部分精英的特权。尚未有人对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逐步演化作出全面的描述,究竟聆听方式的改变给音乐带来了哪些好处,又有何风险,我们并不清楚。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而风险则源于听者脑中预设的观念。事实上,成千上万的听众被引导、被鼓励将音乐视作避难所,音乐是驱散日常生活无尽忧思的安慰,甚至把最伟大的古典音乐杰作用作抵御“外族”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极力反抗当代现实主义的入侵。厚厚的保守主义阴云飘悬在当今音乐领域的上空。由于无情地过分强调过去几个世纪的音乐,现代音乐表现的自然活力被大大削弱,深陷困顿,音乐的未来将举步维艰,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每个作曲家都只能在他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空间范围内发挥作用,并且回应、满足其观众的需求。基于某些奇特的原因,音乐爱好者们坚持认为最高级的音乐理应是永恒的、超越时间的,不受此时此刻、某一时间段思考的影响。抱持这样观点的人随处可见,然而,这种想法究竟有几分真实性?音乐是作曲家以特有的方式述说自己人生经历的过程,这与任何其他类型的艺术创造者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它所传递出的观点与创作者所处时代的审美观念密切相关。同样地,今天的作曲家必须在创作中把当今世界的种种纳入考量,他的音乐必须尽可能反映它,即时是负面的。如果听者只能欣赏过去的音乐,那么当今作曲家永远别指望仅通过让听者接触自己的音乐就能逆转现代音乐的颓势。如今,这种两难的困境并没有得到丝毫缓解。越多越多新一代的作曲家被孤立,他们日益远离本该属于他们的大众。
这是多么矛盾的情况啊!我们生活在一个能敏锐感知声音媒介的时代。“声波”与“超声波”,对任何学生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两个词,它们常被挂在嘴边,而关于频率、分贝的探讨亦十分普遍。本该引领这个时代的当代作曲家被降格为音乐世界的边缘存在,他们甚至连边缘都够不上,只能说是音乐世界边缘的边缘。以下是一个合理的估算,全世界所能听到的音乐作品中,属于过去时代作曲家的创作比例高达八分之七。音乐作品需要在不断公演中得以成长,音乐爱好者们对于现当代音乐的冷漠态度对当今作曲家无疑是一种抑制。如此环境下,一个人必须拥有多么强大的坚毅与勇气才能坚定地把一生奉献给音乐创作!
尽管缺乏动力与鼓舞,欧洲与美国的作曲家们依然坚持推进对音乐前沿的探索。二十世纪的音乐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表现。尤其是对于全新的表达方式的探求,二十世纪的音乐与其他艺术类型在这个层面上的发展可谓齐头并进。于是,在这张现当代音乐的资产负债表上,我们可以列上以下受益:首先,节奏创意上确立了新自由。先前的时代要求音乐采用温和适度的节奏型,如今它们被更富挑战意味、拥有更多可能性的韵律所替代。原本整齐划一的、依照既定节奏均衡分配的小节线让位给一种有节奏的推进,更为错综复杂、更有活力、更显多样化,当然也更难以预测。最近,有一些作曲家尝试采用不同的音乐创作手法,以节奏控制作为创作的导向,音乐完全建构在对作品节奏因素的严格把控上。显然,这个时代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节奏逻辑,然而,究竟它能走多远,现在断言还为时尚早。
现当代音乐写作极大地扩展了和声的可能性。暂且将教科书里的条条框框放一边,和声建构的前提是,只要安排得恰当且具有说服力,任何和弦的使用皆可以成立。普遍认为,所谓和谐与不和谐只是相对而言,而非绝对的分野。调性体系的原则一再被扩充放大,如今它既有的界定变得模糊不清;与此同时,十二音体系的创作则干脆将调性体系的原则完全抛弃。今天的年轻作曲家们是调性自由的继承者,他们的音乐的确有些令人眼花缭乱,在这场混战中,陈旧的教科书注定要被 “新声”所改写。除却和声实验,人们还致力于重新审视旋律的本质,包括音域范围、音程的复杂性。作为创作中必不可少的“结合元素”,旋律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当涉及音乐主题之间的关系时,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个别作曲家提出一种颇令人费解的概念——无主题音乐(athematic music),即任何旋律素材在作品中仅出现一次,永不再重复。若从更高一级的层面上看待这一切,所有的改变都是对音乐形式建构原则的质问。这显然是必然的结果,新的态度正在引领人们前行。继而,我们可以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长久以来确立的建构原理被弃置,音乐将朝全新的方向迈进。
至于音乐未来可能发展的道路,在我看来,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常常会忽略一个制约性因素:即所使用乐器的性质。有没有可能一天,当我们醒来时,发现原先所熟知的弦乐器、铜管乐器、木管乐器、打击乐器被某新型的电子乐器所替代,该乐器使用前所未有的微分音列,拥有完全不同且变化多端的声音,并且乐器完全由作曲家直接掌控,无需通过表演者进行诠释。这样一台机器将使“节奏”摆脱演奏者大脑的局限,获得更多的自由;并且极有可能对人类听觉能力提出空前的挑战。这是一个突破音障的时代,人们不可能一味遵循先人的方式,继续谱写那些历史悠久的“乐音”。我承认,这是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未来。因为,这真的可能就是未来音乐的样子,瓦格纳终其一生都在琢磨的问题,或许答案就在眼前。所有这一切尚属推测,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管音乐何去何从,音乐与生命的流动将永远紧密相连。只要人文精神依然在这个星球上生长繁衍,音乐必将以某种活态样式生存下去,歌咏人文精神之魂魄,为人文表达注入更多意涵。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