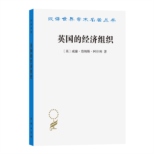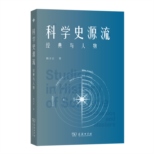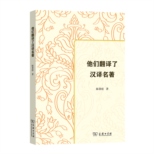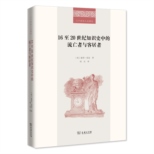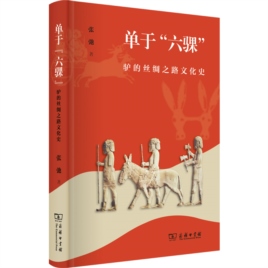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近30年来,人与动物的关系史( histories of human and non-human animal relations),一直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热点。丹·范德萨默斯( Dan Vandersommers)指出,历史学的“动物转向”( the animal turn),是继历史学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之后的又一学术思潮。哈利瑞特·瑞特沃( Harriet Ritvo)认为,动物史( Animal History)研究已经成为欧美史学的主流之一,其“动物转向”的学术趋势包括了环境史、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和全球史等多个史学分支领域。
过去,国内史学界对动物史关注不多,只有少数学者对与动物相关的特定史料感兴趣。近年来,随着科技考古的不断发展,基因组学、分子考古学、疾病考古学、生物力学等成果不断涌现,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动物学、社会学、文献学、语言学等跨学科综合研究范式逐步确立,全球史视阈下的动物研究逐渐成为学术前沿,构成了一种“集体意象”( 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的历史,具有特定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从动物与人类关系的角度出发,史学的主要门类均会涉及与动物有关的内容。动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它们的身影。认识与理解动物,是人类探索自然、创造文明的重要方式。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唐奈(Donnell)调查发现:现代城市幼儿在玩耍过程中,会将动物赋予人的属性,从而实现动物的拟人化;而生长在原始森林中的北美梅诺米尼人( Menominee)幼儿,会将自己想象为动物,赋予自身动物的属性。
任何一种人类文明形态,都构建出对动物界的一种想象场域,而这种场域通常围绕几种重要的动物展开,它们看似比其他任何物种更重要,或是与人类之间的联系更突出。这一关系通常非常紧密,并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因此被学术界称作“动物中心圈”( Bestiaire Central)。“动物中心圈”在人类出现不久,就已存在。史前时代晚期的“动物中心圈”一般由本地的野生动物组成,例如欧亚草原常见的虎、熊、狼、鹿、鹰、天鹅、乌鸦、野猪等。随着定居农业文明的产生,驯化家畜开始进入“动物中心圈”,如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了牛、驴、狗等;东亚地区出现了猪、犬、鸡等动物。
自家驴驯化伊始,它一直是人类社会与动物彼此互动的见证者。大量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表明,驴不仅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是人类思想与情感的载体。家驴的传播研究呈现出全球史的特点,尤其与早期丝绸之路高度重合,拓展了传统史学的领域,成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