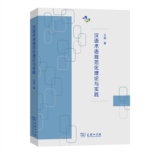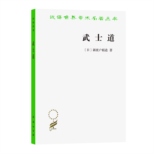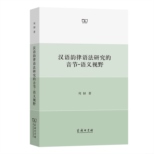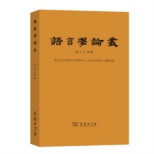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3><STRONG>中译本序言</STRONG></FONT>
我冒昧迻译的这部道德语言学著作是现代英美伦理学界的一部名著。作者理查德•麦尔文•黑尔(Richard Mervyn Hare,1919•3•21—),原是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著名的“怀特”(White’s)道德哲学讲座教授,现为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其代表作除本书外还有:《自由与理性》(Freedom and Reason,1963)、《道德概念论文集》(Essays on The Moral Concepts,1973)、《道德思维—及其层次、方法和视角》(Moral Thinking—its Levels Methods and Points,1981)、等等。
《道德语言》一书在现代西方伦理学,特别是现代元伦理学的发展进程中,确乎享有关键性的学术地位。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本书,进而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递嬗演变,译者拟就黑尔教授有关道德语言学方面的理论观点作一简略导述,以求抛砾石而引玉璞。
本世纪初以来,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已呈现一派崭新格局,显示出迥异于古典伦理学的特征。以非理性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人本主义思潮,以人道化世俗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宗教伦理思潮,和以科学主义和逻辑主义为基本方法论特征的现代元伦理学思潮,一起构成了现代西方伦理学发展态势的三大主脉。后者更是英美等国现代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理论趋向或主体构成。元伦理学(或依现代美国著名的伦理学家C.L.史蒂文森的见解,曰“分析伦理学”、“理论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思潮的兴起相呼应。它的渊源可以逆溯到近代18世纪英国著名经验主义哲学家和情感论伦理学家休谟那里,而它的正式形成则应归功于本世纪英国最著名的伦理学家之一G.E.摩尔。
迄今为止,元伦理学的理论发展经历了三次变革或三个阶段。以摩尔为先驱的“直觉主义”(intuitionalism)是元伦理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所谓“价值论直觉主义”(摩尔、罗素早期)和“义务论直觉主义”(普里查德、罗斯等人)。摩尔在1903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一书首次将伦理学划分为“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和“元伦理学”(meta-ethics),是现代西方元伦理学诞生的标志。3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出现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研究成果,使元伦理学由较为简单的日常语言分析,转向科学逻辑语言的研究层次,随之产生了伦理学的“情感主义”(emotionalism),形成元伦理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卡尔纳普、赖辛巴哈,以及后来的维特根斯坦和罗素(晚期),都从伦理学语言的逻辑分析中,推出了“伦理学只是情感的表达,而不是科学事实的陈述”这一道德情感论的结论。50年代活跃在美国伦理学论坛上的史蒂文森(C.L.Stevenson)可谓道德情感论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品是《伦理学与语言》等)。但由于这种道德理论偏执于情感主义和非认知主义立场,把伦理学推到了一种非科学的危险境地,直接动摇了伦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科学的根基,因而引起了一种道德情感主义的反动,这就是以黑尔、图尔闵、乌姆逊、诺维尔-史密斯等人为代表的新语言分析伦理学派的崭露。黑尔等人一方面加强了对伦理学语言本身的逻辑研究,力图以具体的逻辑证明维护伦理学蕴涵真理的科学性,以反对情感论者否认伦理学科学地位(status)的极端片面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借助于一些新规范伦理学理论(如“新功利主义”等等)来改造和修缮道德语言学的分析范式,使之保持其科学性(事实描述)和实践性(行为指导)的基本特性。这一理论运动构成了元伦理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元伦理学发展的最新趋势。黑尔是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伦理学家之一,而其《道德语言》一书又是确立他这一重要学术地位的奠基之作。
也许正是因为《道德语言》所享有的这一特殊地位,使它不仅成了现代西方伦理学界的名著之一,而且也为各国学术界所倚重。在着手本书的翻译前夕,我已从黑尔教授本人那里获悉,该书现已有德、法、意、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的译本。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迻译此书的最具吸引力的动因之一。然而,更主要的动因还来自本书所提出的独特见解、思考和分析道德语言的独特方法等方面对我的启发,以及它对于我们研究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重要史料价值。
《道德语言》一书,基本上代表了黑尔伦理思想的主要方面。黑尔教授在写给译者本人的信中特别提到,反对现代元伦理学中的非理性主义,特别是史蒂文森的极端情感主义,是他研究伦理学和道德语言问题的最初动机。在该书的开篇中,黑尔就明确指出:“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因此,它决非个人主观情绪、欲望、偏爱和态度的纯粹表达。它既具有“描述性意义”,也具有“评价性意义”;前者使它不同于纯粹的“祈使语气”,后者又使它蕴涵某种祈使意味而与纯粹的“陈述语句”相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道德语言既能陈述事实,也能规定或引导人的行为,指导人们作出各种行为选择和原则决定(decisions of principles)。
道德语言的主要使用形式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人的行为问题,即“我将做什么?”的问题。但人类的语言不单有道德用法,也有其非道德用法。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使用中,这两种用法常常相互交织,并无明确区分,因之难免导致人们对道德语言的认识和应用常常产生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困惑。黑尔运用了各种逻辑的和语言学的分析模式,把道德语言置于一般价值语言的大前提下进行细致而系统的分析。依他所见,价值语言的基本特征是其规定性;人们使用价值语言的目的便是规定或指导各种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语言也即是规定语言。它包括祈使句(命令句)和道德语言两大类。规定不单是评价,也是描述,且两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某一语句通过“价值词”(value-words)表达着人们(说话者)对某一对象的主体评价,又给人们(听者)提供某种事实性描述的信息。比如说,“这是一种好草莓”这一语句,就在表达说话者对该草莓的评价的同时,又包含着有关这种草莓硕大、多汁、甜蜜……等事实信息。
另一方面,黑尔认为,凡规定语言实际上都蕴涵着某种祈使句形式(单称的或全称的)。只要我们依据其逻辑推论程序,就不难发现规定语言的祈使意味,道德语言也是如此。当我说“做A事是正当的”时,我所表达(或希望表达)的,必蕴涵某种祈使句(“请做A事吧!”或“做A事!”)。但这并不意味着规定语言——进而说道德语言——只是一种“说服性”规定,如史蒂文森所以为的那样;或者它只是一种命令。相反,规定语言的这种意蕴,恰恰是与其描述性意蕴相联系着的;否则,它就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总不能毫无<STRONG>理由</STRONG>地<STRONG>说</STRONG>某种规定语言或道德语言,而理由(根据)之必然必须以事实描述为基础。就前例而言,我们说某种草莓好不能凭空而论,必须有事实根据。
然而,规定语言毕竟不同于纯描述性语言,一如祈使句毕竟不同于陈述语句一样。就价值语言和道德语言来说,评价性意义是基本的、第一位的,而描述性意义则是从属的、第二位的,这是价值语言的根本特征所在。价值语言的评价性功能是通过各种价值词来履行的。由此,黑尔在对价值语言的一般逻辑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好的”(善)、“正当”、“应当”三个主要的价值词。他认为,这些价值词均有其道德用法和非道德用法。在这两种用法中,价值词的意义是有所差异的。换言之,价值词的非道德用法较为宽泛,可用来评价各种事物;而它的道德用法则较为严格有限,往往直接指向人们行为或人本身的道德意味。但在日常用法中,两者常常没有截然的分界线。此外,价值词在日常语言中往往较为松散(loose),我们可以探讨以人工的价值词来置换“日常的”(或自然的)价值词之可能性,和这种置换所能达到的程度。但无论如何,不管是在何种用法之中,也不论人工价值词能否完全履行日常语言中的价值词所能履行的功能,价值词和价值语言一样,都不是纯感情的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中,黑尔不单就价值语言和道德语言以及它们的使用“语境”(contexts),分析了道德语言、道德言谈或谈论所具有的描述性与评价性双重特征,而且还就历史文化和教育学等方面分析了这两种特征的相关变化。他认为,人类使用道德语言的用意,在于进行道德判断,而人类进行道德判断的基本前提是某种特定的标准或原则。这些标准或原则本身,也具有事实描述性和价值评价性双重品格。因为它们都是在人类世代更迭的过程中历史地形成和固定下来的。人们在依据它们进行判断、指导或自我修养时,往往因它们的“既定性”而将它们视为事实性或描述性的。而且,某一标准或原则保持越持久,越有连贯性和一致性,其所显示的描述力量就愈大,也就愈有权威性的评价力量;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因为人类历史地赋予它们以既定的事实性意味,仿佛它们确实无疑,因而也就使它们获得了某种表示事实的真理性。
但是,标准和原则的既定与“遗传”也会(且往往易于)产生另一种结果,即形成某种“僵化”、“刻板”和保守的教条。这就需要标准的更新和原则的突破,使之永远处于不断变化和完善的过程之中。人类不断地实践,总是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标准和新的原则。一方面,这种实践在不断地确认和巩固标准或原则的既定性、权威性;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修改它们,突破它们,重构它们;这即是“道德改革”的意义,也是人类道德得以发展的内在缘由所在。从道德语言这一视角来看,上述双重性发展状态主要是通过“教”与“学”这两种相互联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事实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教”与“学”实践,也就是描述性(传授知识、技术)和评价性(指导行为,使学习者接受、认同并按照确定原则或标准进行选择、并在特殊境况中作出自己的原则决定)双重意义上使用价值词的过程。
黑尔教授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远不止上述所示。总体看来,他是在力图清理元伦理学发展中的语言学分析误区的同时,矫正情感主义的偏颇。虽然本书篇幅不大,但视点独特,分析缜密,真可谓筚路蓝缕,爬罗剔抉;其观点和方法开辟了现代英美分析伦理学的新思路:即通过对道德的语言学分析,恢复伦理学的科学品格,使伦理语言所具有的描述(事实)与评价(价值)的双重特性得到系统而科学的确证,从而为他自诩的“规定主义伦理学”(prescriptivist ethics)提供坚实的逻辑基础。仅从这一角度来看,《道德语言》一书的学术价值便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尽管译者付出了艰苦的劳作,仍会有不少疏漏失雅之处,尚待细心的读者,特别是名家高手悉心指正。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但哲学家们又一再告诫我们,语言本身既传达着思想,又限制着思想的传达。人类思维及其表达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者甚多,况且翻译又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一次再转换,永远无法像“摄影”那样原版翻拍,故尔常有偏差文本(texts)的损蚀。这是不少严肃的译者共有的困惑。因之,我一方面在尽力而为的前提下恳求专家学者对拙译多多雅正,以便在有机会的时候亡羊补牢,逐步完善之;另一方面我也因译事不易和译力不逮的客观事实而深感惶惑乃至悲哀,也就因此而弃绝了那种至于完美的梦想。然而这种坦白并不意味着我想为自己译笔不力的缺陷开脱责任,更无意就此自我宽怀。追求本真依旧是我始终的学术承诺,著书立言、教学译介,概莫能外。
最后,我当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黑尔教授。在我请求翻译本书之际,他不仅给予我高度信任和鼓励,而且多次帮我解释一些疑难问题。今年五月,他来北京旅游时还专门来北京大学找我商询译事,可惜因我赴外地开会而未能一晤。不然,他的当面指点和建议一定会使本书的翻译更好一些。另外,因我多有延误,致使中译本未能尽快发稿,多有辜负黑尔先生的良好期望,亦使我惭疚不已。幸亏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不嫌余陋,悉心扶正。特别是本书责任编辑徐奕春同志,更是关心备至,他不仅对本书的翻译出版给予了始终如一的关怀、指导和帮助,而且为拙译作了许多超出职责范围的工作。他认真负责的工作使拙译减少了不少纰漏。没有他和上述这些同志热忱诚挚的扶携,我是很难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的。还有一些朋友也对此书的翻译出版给予了友好的关切和帮助,恕不一一作谢。
谨以本书中译本的圆功作为我献给作者的圣诞礼物!
万俊人
于北京大学园内
<FONT size=3><STRONG>再 版 序
</STRONG></FONT>
在本书第二版中,我作了一些轻微改动,而未对原文作大刀阔斧的改写。倘若我再有机会重写本书,我会把它写成一部面貌不同的新作,因为我现在对那些存有误解和使读者误解的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不过,尽管我的观点某些细节已有改变,但在我认为是基本的方面并无变化。我最衷心地感谢那些通过评论我的各种论点来帮助我廓清这些问题的人们。关于我现在的观点,我必须请读者参阅我的另一部新作,它是本书的继续,我希望这部新作能于近期问世。
R.M.黑尔
于波利奥尔学院,1960年。
我冒昧迻译的这部道德语言学著作是现代英美伦理学界的一部名著。作者理查德•麦尔文•黑尔(Richard Mervyn Hare,1919•3•21—),原是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著名的“怀特”(White’s)道德哲学讲座教授,现为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其代表作除本书外还有:《自由与理性》(Freedom and Reason,1963)、《道德概念论文集》(Essays on The Moral Concepts,1973)、《道德思维—及其层次、方法和视角》(Moral Thinking—its Levels Methods and Points,1981)、等等。
《道德语言》一书在现代西方伦理学,特别是现代元伦理学的发展进程中,确乎享有关键性的学术地位。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本书,进而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递嬗演变,译者拟就黑尔教授有关道德语言学方面的理论观点作一简略导述,以求抛砾石而引玉璞。
本世纪初以来,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已呈现一派崭新格局,显示出迥异于古典伦理学的特征。以非理性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人本主义思潮,以人道化世俗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宗教伦理思潮,和以科学主义和逻辑主义为基本方法论特征的现代元伦理学思潮,一起构成了现代西方伦理学发展态势的三大主脉。后者更是英美等国现代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理论趋向或主体构成。元伦理学(或依现代美国著名的伦理学家C.L.史蒂文森的见解,曰“分析伦理学”、“理论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思潮的兴起相呼应。它的渊源可以逆溯到近代18世纪英国著名经验主义哲学家和情感论伦理学家休谟那里,而它的正式形成则应归功于本世纪英国最著名的伦理学家之一G.E.摩尔。
迄今为止,元伦理学的理论发展经历了三次变革或三个阶段。以摩尔为先驱的“直觉主义”(intuitionalism)是元伦理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所谓“价值论直觉主义”(摩尔、罗素早期)和“义务论直觉主义”(普里查德、罗斯等人)。摩尔在1903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一书首次将伦理学划分为“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和“元伦理学”(meta-ethics),是现代西方元伦理学诞生的标志。3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出现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研究成果,使元伦理学由较为简单的日常语言分析,转向科学逻辑语言的研究层次,随之产生了伦理学的“情感主义”(emotionalism),形成元伦理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卡尔纳普、赖辛巴哈,以及后来的维特根斯坦和罗素(晚期),都从伦理学语言的逻辑分析中,推出了“伦理学只是情感的表达,而不是科学事实的陈述”这一道德情感论的结论。50年代活跃在美国伦理学论坛上的史蒂文森(C.L.Stevenson)可谓道德情感论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品是《伦理学与语言》等)。但由于这种道德理论偏执于情感主义和非认知主义立场,把伦理学推到了一种非科学的危险境地,直接动摇了伦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科学的根基,因而引起了一种道德情感主义的反动,这就是以黑尔、图尔闵、乌姆逊、诺维尔-史密斯等人为代表的新语言分析伦理学派的崭露。黑尔等人一方面加强了对伦理学语言本身的逻辑研究,力图以具体的逻辑证明维护伦理学蕴涵真理的科学性,以反对情感论者否认伦理学科学地位(status)的极端片面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借助于一些新规范伦理学理论(如“新功利主义”等等)来改造和修缮道德语言学的分析范式,使之保持其科学性(事实描述)和实践性(行为指导)的基本特性。这一理论运动构成了元伦理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元伦理学发展的最新趋势。黑尔是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伦理学家之一,而其《道德语言》一书又是确立他这一重要学术地位的奠基之作。
也许正是因为《道德语言》所享有的这一特殊地位,使它不仅成了现代西方伦理学界的名著之一,而且也为各国学术界所倚重。在着手本书的翻译前夕,我已从黑尔教授本人那里获悉,该书现已有德、法、意、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的译本。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迻译此书的最具吸引力的动因之一。然而,更主要的动因还来自本书所提出的独特见解、思考和分析道德语言的独特方法等方面对我的启发,以及它对于我们研究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重要史料价值。
《道德语言》一书,基本上代表了黑尔伦理思想的主要方面。黑尔教授在写给译者本人的信中特别提到,反对现代元伦理学中的非理性主义,特别是史蒂文森的极端情感主义,是他研究伦理学和道德语言问题的最初动机。在该书的开篇中,黑尔就明确指出:“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因此,它决非个人主观情绪、欲望、偏爱和态度的纯粹表达。它既具有“描述性意义”,也具有“评价性意义”;前者使它不同于纯粹的“祈使语气”,后者又使它蕴涵某种祈使意味而与纯粹的“陈述语句”相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道德语言既能陈述事实,也能规定或引导人的行为,指导人们作出各种行为选择和原则决定(decisions of principles)。
道德语言的主要使用形式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人的行为问题,即“我将做什么?”的问题。但人类的语言不单有道德用法,也有其非道德用法。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使用中,这两种用法常常相互交织,并无明确区分,因之难免导致人们对道德语言的认识和应用常常产生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困惑。黑尔运用了各种逻辑的和语言学的分析模式,把道德语言置于一般价值语言的大前提下进行细致而系统的分析。依他所见,价值语言的基本特征是其规定性;人们使用价值语言的目的便是规定或指导各种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语言也即是规定语言。它包括祈使句(命令句)和道德语言两大类。规定不单是评价,也是描述,且两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某一语句通过“价值词”(value-words)表达着人们(说话者)对某一对象的主体评价,又给人们(听者)提供某种事实性描述的信息。比如说,“这是一种好草莓”这一语句,就在表达说话者对该草莓的评价的同时,又包含着有关这种草莓硕大、多汁、甜蜜……等事实信息。
另一方面,黑尔认为,凡规定语言实际上都蕴涵着某种祈使句形式(单称的或全称的)。只要我们依据其逻辑推论程序,就不难发现规定语言的祈使意味,道德语言也是如此。当我说“做A事是正当的”时,我所表达(或希望表达)的,必蕴涵某种祈使句(“请做A事吧!”或“做A事!”)。但这并不意味着规定语言——进而说道德语言——只是一种“说服性”规定,如史蒂文森所以为的那样;或者它只是一种命令。相反,规定语言的这种意蕴,恰恰是与其描述性意蕴相联系着的;否则,它就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总不能毫无<STRONG>理由</STRONG>地<STRONG>说</STRONG>某种规定语言或道德语言,而理由(根据)之必然必须以事实描述为基础。就前例而言,我们说某种草莓好不能凭空而论,必须有事实根据。
然而,规定语言毕竟不同于纯描述性语言,一如祈使句毕竟不同于陈述语句一样。就价值语言和道德语言来说,评价性意义是基本的、第一位的,而描述性意义则是从属的、第二位的,这是价值语言的根本特征所在。价值语言的评价性功能是通过各种价值词来履行的。由此,黑尔在对价值语言的一般逻辑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好的”(善)、“正当”、“应当”三个主要的价值词。他认为,这些价值词均有其道德用法和非道德用法。在这两种用法中,价值词的意义是有所差异的。换言之,价值词的非道德用法较为宽泛,可用来评价各种事物;而它的道德用法则较为严格有限,往往直接指向人们行为或人本身的道德意味。但在日常用法中,两者常常没有截然的分界线。此外,价值词在日常语言中往往较为松散(loose),我们可以探讨以人工的价值词来置换“日常的”(或自然的)价值词之可能性,和这种置换所能达到的程度。但无论如何,不管是在何种用法之中,也不论人工价值词能否完全履行日常语言中的价值词所能履行的功能,价值词和价值语言一样,都不是纯感情的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中,黑尔不单就价值语言和道德语言以及它们的使用“语境”(contexts),分析了道德语言、道德言谈或谈论所具有的描述性与评价性双重特征,而且还就历史文化和教育学等方面分析了这两种特征的相关变化。他认为,人类使用道德语言的用意,在于进行道德判断,而人类进行道德判断的基本前提是某种特定的标准或原则。这些标准或原则本身,也具有事实描述性和价值评价性双重品格。因为它们都是在人类世代更迭的过程中历史地形成和固定下来的。人们在依据它们进行判断、指导或自我修养时,往往因它们的“既定性”而将它们视为事实性或描述性的。而且,某一标准或原则保持越持久,越有连贯性和一致性,其所显示的描述力量就愈大,也就愈有权威性的评价力量;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因为人类历史地赋予它们以既定的事实性意味,仿佛它们确实无疑,因而也就使它们获得了某种表示事实的真理性。
但是,标准和原则的既定与“遗传”也会(且往往易于)产生另一种结果,即形成某种“僵化”、“刻板”和保守的教条。这就需要标准的更新和原则的突破,使之永远处于不断变化和完善的过程之中。人类不断地实践,总是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标准和新的原则。一方面,这种实践在不断地确认和巩固标准或原则的既定性、权威性;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修改它们,突破它们,重构它们;这即是“道德改革”的意义,也是人类道德得以发展的内在缘由所在。从道德语言这一视角来看,上述双重性发展状态主要是通过“教”与“学”这两种相互联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事实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教”与“学”实践,也就是描述性(传授知识、技术)和评价性(指导行为,使学习者接受、认同并按照确定原则或标准进行选择、并在特殊境况中作出自己的原则决定)双重意义上使用价值词的过程。
黑尔教授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远不止上述所示。总体看来,他是在力图清理元伦理学发展中的语言学分析误区的同时,矫正情感主义的偏颇。虽然本书篇幅不大,但视点独特,分析缜密,真可谓筚路蓝缕,爬罗剔抉;其观点和方法开辟了现代英美分析伦理学的新思路:即通过对道德的语言学分析,恢复伦理学的科学品格,使伦理语言所具有的描述(事实)与评价(价值)的双重特性得到系统而科学的确证,从而为他自诩的“规定主义伦理学”(prescriptivist ethics)提供坚实的逻辑基础。仅从这一角度来看,《道德语言》一书的学术价值便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尽管译者付出了艰苦的劳作,仍会有不少疏漏失雅之处,尚待细心的读者,特别是名家高手悉心指正。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但哲学家们又一再告诫我们,语言本身既传达着思想,又限制着思想的传达。人类思维及其表达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者甚多,况且翻译又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一次再转换,永远无法像“摄影”那样原版翻拍,故尔常有偏差文本(texts)的损蚀。这是不少严肃的译者共有的困惑。因之,我一方面在尽力而为的前提下恳求专家学者对拙译多多雅正,以便在有机会的时候亡羊补牢,逐步完善之;另一方面我也因译事不易和译力不逮的客观事实而深感惶惑乃至悲哀,也就因此而弃绝了那种至于完美的梦想。然而这种坦白并不意味着我想为自己译笔不力的缺陷开脱责任,更无意就此自我宽怀。追求本真依旧是我始终的学术承诺,著书立言、教学译介,概莫能外。
最后,我当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黑尔教授。在我请求翻译本书之际,他不仅给予我高度信任和鼓励,而且多次帮我解释一些疑难问题。今年五月,他来北京旅游时还专门来北京大学找我商询译事,可惜因我赴外地开会而未能一晤。不然,他的当面指点和建议一定会使本书的翻译更好一些。另外,因我多有延误,致使中译本未能尽快发稿,多有辜负黑尔先生的良好期望,亦使我惭疚不已。幸亏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不嫌余陋,悉心扶正。特别是本书责任编辑徐奕春同志,更是关心备至,他不仅对本书的翻译出版给予了始终如一的关怀、指导和帮助,而且为拙译作了许多超出职责范围的工作。他认真负责的工作使拙译减少了不少纰漏。没有他和上述这些同志热忱诚挚的扶携,我是很难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的。还有一些朋友也对此书的翻译出版给予了友好的关切和帮助,恕不一一作谢。
谨以本书中译本的圆功作为我献给作者的圣诞礼物!
万俊人
于北京大学园内
<FONT size=3><STRONG>再 版 序
</STRONG></FONT>
在本书第二版中,我作了一些轻微改动,而未对原文作大刀阔斧的改写。倘若我再有机会重写本书,我会把它写成一部面貌不同的新作,因为我现在对那些存有误解和使读者误解的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不过,尽管我的观点某些细节已有改变,但在我认为是基本的方面并无变化。我最衷心地感谢那些通过评论我的各种论点来帮助我廓清这些问题的人们。关于我现在的观点,我必须请读者参阅我的另一部新作,它是本书的继续,我希望这部新作能于近期问世。
R.M.黑尔
于波利奥尔学院,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