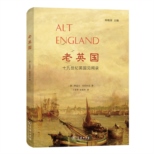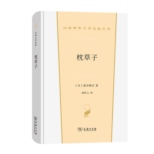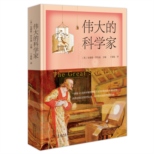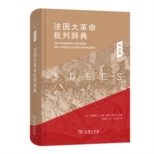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3><STRONG>译本序
陈 原
</STRONG></FONT>
校印这部译作,出于三重考虑。首先,由于本书是这个学术领域的权威著作,其材料之丰富,分析之精辟,迄今仍无出其右。其次,为了纪念两个真诚的学人,作者德雷仁和译者徐沫,他们都是悲剧时代的牺牲者。最后,为着实现胡愈之和叶籁士两位长者的愿望,他们生前曾力促这部译作能与中国读者见面。
先说书。
这部著作研究的对象是国际辅助语的思想发展历史,属于语际语言学的范畴。“语际语言学”这个术语,是三十年代初由举世闻名的丹麦语言学大师耶斯佩森(Otto Jespersen,1860—1943)在《国际通讯》(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杂志上发表的专门论文首次提出的,原文为Interlinguistics;他把这个术语定义为“研究一切语言的构造和基本观念,目的在创立一种跟各种语言并存的、能说能写的辅助语言”。
古往今来,或者说,自从巴贝尔通天塔的梦破灭以后,多少哲人怀着尊重、继承、沟通和交流人类文明成果的崇高愿望,年复一年地设计能被各族人民接受的共通语或辅助语;其中也包括耶斯佩森——他曾创制过一种叫做“诺维亚尔语”(意即“新国际辅助语”Novial)方案(1928)。事实上,多少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它牵涉到很多复杂因素,包括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国家的、文化传统的,等等;只有很少几种人工创造的辅助语方案曾在世界上一部分人中间流行过,而流通得最广的当推波兰柴门霍夫创始的“Esperanto”(我国通常译作“世界语”),在它问世后的一百多年间,拥有比较多的普通群众的爱戴,由是获得比较强大的生命力;战后又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和支持。德雷仁的这部专著,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检阅和分析各个时代、各个哲人、各种国际辅助语方案的观念、结构和得失,是人类创制国际语的历史总结。从来这类研究都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而德雷仁的书则不仅作语言学的探索,而且作社会学的探索,这是其他同类专著所不及的;它之所以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著作,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几十年来在不同的国家翻印了多次,其原因盖在于此。
本书作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那时马尔的语言理论正在走红,马尔本人也热衷于这个学科的研究,故他特地为本书俄文第一版写了序文。因此,本书在头一章中论述了并肯定了语言阶级性的论点,这些章节,译本仍保存着,相信读者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五十年代初,斯大林批判了马尔的这种错误观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从此马尔好像就一无是处了;其实马尔关于语言的人工性(即语言文字系统有可能加以人工调节)的论点,正是语际语言学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语言规划或文字改革的理论基础。正因为这一点,本书在信息时代重印,仍不失其学术意义。
第二,关于作者。
德雷仁(Ernest K.Drezen,1892—1937)是从红军军官转到科学研究领域来的,他是当代国际术语学的创始人之一,跟现在被称为术语学鼻祖的奥地利工程师欧根•维于斯脱(Eugene Wüster)一起,创立了国际标准化协会(ISA),即联合国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前身。他们两人都是热诚的世界语学者,并且都是从世界语运动走向术语标准化和术语国际化的研究工作的。维于斯脱同德雷仁过从甚密,包括频繁的通信和国际会议的商讨。德雷仁在三十年代上半期是当时苏联科学院术语标准化委员会的负责人,常常代表苏联术语学界出席国际会议。他又是全苏联世界语联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上的经历和工作,导致他在肃反扩大化中被诬为“人民公敌”,以“里通外国”罪名被捕(1937年4月17日),半年后即被处决(1937年10月27日),死时才45岁。二十年后才得平反(1957年5月11日)。
据我所知,国人见过德雷仁的只有胡愈之。在他写的《莫斯科印象记》中《D同志的家庭》和以下的几节所提到的“D同志”,就是这个德雷仁。那是1931年的事了,1935年至1936年我因热衷于研究工程术语的移译问题,读了德雷仁关于科学技术术语国际化的论文,曾写信向他请教,因此通过一两次信;但1937年我寄去的信件都被退回,加盖了“无此人”的图章,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实那时他已遇难,不过当年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点就是了。
第三,关于译者。
译者徐沫,原名何增禧(1916—1966),我跟他只见过几面,但印象却极深刻,是个质朴的严肃的学者。他的至友胡绳对他有过一段很确切的描述:
<FONT face=仿宋_GB2312>徐沫是个沉静寡言的人。在解放以前,他为了谋生而从事银行工作,钻研银行业务。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学马列主义。除世界语外,他还学好了英语,也学了日语、俄语。他一贯地、悄悄地为进步的世界语运动、为革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奉献。他直接间接地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对于他所能接触到的共产党员和党所领导的组织,他尽力给以支持帮助。他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在解放前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他从不在任何情况下炫耀自己做过什么工作,解放后他还是保持这种品质。他甘于默默无闻地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和工作。
</FONT>这部大书是他在三十年代初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出来的,其中个别章节曾在叶籁士主编的《世界》杂志附刊《言语科学》上发表过——这通通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稿子一直未能出版。解放后,徐沫专心做他的银行业务,到六十年代已成为熟悉国内和国际情况的外汇问题专家。然而那场荒唐的“革命”,连这样一个学者也不放过;他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位真诚的学者,经不住种种折磨,只得用原始的方法结束了自已短暂的一生;1966年8月24日走完了他五十年人生道路。
好容易熬过十年。绝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毕生致力于国际语的理论与实践的两位前辈,胡愈之和叶籁士,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同我讲过多次,让我设法促成这部译稿面世;叶籁士百病缠身,仍打算为中译本写一篇序言——直到他弥留时还记挂着此事。如今胡老叶老先后走了,我却已没有精力完成译稿的校订工作。随后我征得译者的遗孀康继琴同志的同意,由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领导硬逼着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组的杭军同志,挤出大半年的业余时间,将译稿校订一遍,最后由我在浏览全稿时解决了若干翻译上的疑难,算是定稿了。商务印书馆这家老店不怕捞不回成本,毅然将此书列入选题计划——这时,直到这时,我才如释重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部尘封了半个世纪的译稿,这部有世界声誉的专著,终于有机会同中国的读书界见面了;而我也终于能向几位可敬的师友偿还“债务”了;但愿我活着时能看到它的样书。
1994年4月29日
陈 原
</STRONG></FONT>
校印这部译作,出于三重考虑。首先,由于本书是这个学术领域的权威著作,其材料之丰富,分析之精辟,迄今仍无出其右。其次,为了纪念两个真诚的学人,作者德雷仁和译者徐沫,他们都是悲剧时代的牺牲者。最后,为着实现胡愈之和叶籁士两位长者的愿望,他们生前曾力促这部译作能与中国读者见面。
先说书。
这部著作研究的对象是国际辅助语的思想发展历史,属于语际语言学的范畴。“语际语言学”这个术语,是三十年代初由举世闻名的丹麦语言学大师耶斯佩森(Otto Jespersen,1860—1943)在《国际通讯》(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杂志上发表的专门论文首次提出的,原文为Interlinguistics;他把这个术语定义为“研究一切语言的构造和基本观念,目的在创立一种跟各种语言并存的、能说能写的辅助语言”。
古往今来,或者说,自从巴贝尔通天塔的梦破灭以后,多少哲人怀着尊重、继承、沟通和交流人类文明成果的崇高愿望,年复一年地设计能被各族人民接受的共通语或辅助语;其中也包括耶斯佩森——他曾创制过一种叫做“诺维亚尔语”(意即“新国际辅助语”Novial)方案(1928)。事实上,多少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它牵涉到很多复杂因素,包括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国家的、文化传统的,等等;只有很少几种人工创造的辅助语方案曾在世界上一部分人中间流行过,而流通得最广的当推波兰柴门霍夫创始的“Esperanto”(我国通常译作“世界语”),在它问世后的一百多年间,拥有比较多的普通群众的爱戴,由是获得比较强大的生命力;战后又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和支持。德雷仁的这部专著,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检阅和分析各个时代、各个哲人、各种国际辅助语方案的观念、结构和得失,是人类创制国际语的历史总结。从来这类研究都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而德雷仁的书则不仅作语言学的探索,而且作社会学的探索,这是其他同类专著所不及的;它之所以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著作,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几十年来在不同的国家翻印了多次,其原因盖在于此。
本书作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那时马尔的语言理论正在走红,马尔本人也热衷于这个学科的研究,故他特地为本书俄文第一版写了序文。因此,本书在头一章中论述了并肯定了语言阶级性的论点,这些章节,译本仍保存着,相信读者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五十年代初,斯大林批判了马尔的这种错误观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从此马尔好像就一无是处了;其实马尔关于语言的人工性(即语言文字系统有可能加以人工调节)的论点,正是语际语言学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语言规划或文字改革的理论基础。正因为这一点,本书在信息时代重印,仍不失其学术意义。
第二,关于作者。
德雷仁(Ernest K.Drezen,1892—1937)是从红军军官转到科学研究领域来的,他是当代国际术语学的创始人之一,跟现在被称为术语学鼻祖的奥地利工程师欧根•维于斯脱(Eugene Wüster)一起,创立了国际标准化协会(ISA),即联合国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前身。他们两人都是热诚的世界语学者,并且都是从世界语运动走向术语标准化和术语国际化的研究工作的。维于斯脱同德雷仁过从甚密,包括频繁的通信和国际会议的商讨。德雷仁在三十年代上半期是当时苏联科学院术语标准化委员会的负责人,常常代表苏联术语学界出席国际会议。他又是全苏联世界语联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上的经历和工作,导致他在肃反扩大化中被诬为“人民公敌”,以“里通外国”罪名被捕(1937年4月17日),半年后即被处决(1937年10月27日),死时才45岁。二十年后才得平反(1957年5月11日)。
据我所知,国人见过德雷仁的只有胡愈之。在他写的《莫斯科印象记》中《D同志的家庭》和以下的几节所提到的“D同志”,就是这个德雷仁。那是1931年的事了,1935年至1936年我因热衷于研究工程术语的移译问题,读了德雷仁关于科学技术术语国际化的论文,曾写信向他请教,因此通过一两次信;但1937年我寄去的信件都被退回,加盖了“无此人”的图章,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实那时他已遇难,不过当年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点就是了。
第三,关于译者。
译者徐沫,原名何增禧(1916—1966),我跟他只见过几面,但印象却极深刻,是个质朴的严肃的学者。他的至友胡绳对他有过一段很确切的描述:
<FONT face=仿宋_GB2312>徐沫是个沉静寡言的人。在解放以前,他为了谋生而从事银行工作,钻研银行业务。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学马列主义。除世界语外,他还学好了英语,也学了日语、俄语。他一贯地、悄悄地为进步的世界语运动、为革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奉献。他直接间接地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对于他所能接触到的共产党员和党所领导的组织,他尽力给以支持帮助。他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在解放前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他从不在任何情况下炫耀自己做过什么工作,解放后他还是保持这种品质。他甘于默默无闻地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和工作。
</FONT>这部大书是他在三十年代初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出来的,其中个别章节曾在叶籁士主编的《世界》杂志附刊《言语科学》上发表过——这通通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稿子一直未能出版。解放后,徐沫专心做他的银行业务,到六十年代已成为熟悉国内和国际情况的外汇问题专家。然而那场荒唐的“革命”,连这样一个学者也不放过;他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位真诚的学者,经不住种种折磨,只得用原始的方法结束了自已短暂的一生;1966年8月24日走完了他五十年人生道路。
好容易熬过十年。绝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毕生致力于国际语的理论与实践的两位前辈,胡愈之和叶籁士,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同我讲过多次,让我设法促成这部译稿面世;叶籁士百病缠身,仍打算为中译本写一篇序言——直到他弥留时还记挂着此事。如今胡老叶老先后走了,我却已没有精力完成译稿的校订工作。随后我征得译者的遗孀康继琴同志的同意,由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领导硬逼着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组的杭军同志,挤出大半年的业余时间,将译稿校订一遍,最后由我在浏览全稿时解决了若干翻译上的疑难,算是定稿了。商务印书馆这家老店不怕捞不回成本,毅然将此书列入选题计划——这时,直到这时,我才如释重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部尘封了半个世纪的译稿,这部有世界声誉的专著,终于有机会同中国的读书界见面了;而我也终于能向几位可敬的师友偿还“债务”了;但愿我活着时能看到它的样书。
1994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