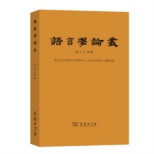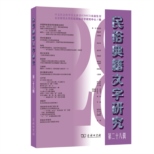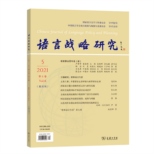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4> 自 序</FONT>
收入这本书里的多数文章原先是用英文在美国发表的,中国的读者也许不大容易直接看到。当石锋教授建议把文章的译文和中文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一本文集的时候,我就欣然同意了。李行德教授最近在《中国语言学报》里(JCL 28,116—162,2000)分析了中国和西方的语言学,他说这两个传统的距离,还是太远。我很赞同他的看法。如果这本文集能够为沟通中国和西方的语言学起一点促进作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十几篇文章的写作时间跨越了三十多年,其中有的是源自我早期在语音学方面的工作。有人曾把语音学称为语言学“不可缺少的基础”,这是颇有道理的。书中也有些文章是有关文字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对我们独特的文字系统产生浓厚的兴趣,其余的文章主要是讨论语言演变的本质的,特别是从方法论的观点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探讨。
这些论文涉及好几个学科的领域,这正好体现了我的这样一个信念: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真正理解语言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视野限制得太狭窄,就不能因已有的学科界限而墨守成规。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犹如画在沙滩上的线条,随着每一次先进知识的波涛到来,这边界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完全消失。人类的知识,特别是研究语言的知识,应该是彼此相连的,并且最终是相互贯通的。
尤其是研究语言变化,我们不得不借鉴生物学里发展出来的演化论。语言变化跟生物变化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这一点达尔文早就讨论过。他在1859年出版的书的第14章,提出过这样的假设:世界上人群的综合谱系也就是世界上语言的谱系。大家知道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基因是经常交换而混合成一体的,同时,这群人的语言也是经常相互影响而大致相同的,可是要是有一部分人离开主群很久,他们的基因跟他们的语言在新的环境里就会改变,时间越久,差异就越大:语言变得快,几百年后他们的话就可能跟主群的话互不通音了,基因变得比较慢,但是久而久之世界上所有的人群中的差异就逐渐积累出来了。
因此研究基因时所发明的一些方法及模型,例如计算距离以及画树形图,都可以用来研究语言。基因跟语言的共同之处是Cavalli Sforza教授几十年来继承达尔文的假设所探讨的焦点,他最近出版的书《基因、人群与语言》已有中译本,是很值得参考的。
可是,这两种变化也有一些很基本的差异,也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首先,“适者生存”这个演化论里选择的概念所指的对象是生物竞争,而语言只是寄生在人群里的一种文化系统。一个语言的利或弊当然可能间接地影响一群人的命运,可是人群的繁荣或灭亡肯定有很多更直接的因素跟语言并不发生关系,因此演化论的有些思想不能完全照搬地用在语言上。
另一点基本的差异是传达的方式。一个婴儿的基因是完全从父母得来的——父亲母亲各供给一半染色体,精子和卵子结合的那一刹那就全部规定,不可能再有别的来源,这跟语言的传达很不一样。婴儿的话是由他主动地观察他周围的语言环境,一步一步地归纳出来的。语言环境里的材料,很可能有父母的话,但是来源繁多,并且是经常变的。家里听到的话,街上的话,老师及同学的话,都会影响他的语言生长。一个人的语言主要部分是在青春期定型的,这十几年的语言环境里的语料,或多或少地都是他语言的来源。
总而言之,小孩学的语言,跟他接触的环境里的语言的差异,一代一代地积累起来,就是历史语言学所研究的语言变迁。要是我们追本穷源,再扩大我们的视野,一直问到数万年前最早的语言,也不过就是一些基本词汇,而目前世界上的如此复杂的语言,还就是经过数千代的小孩学语积累而逐步形成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几样东西的关系搞清楚,就是小孩学语,语言接触以及语言演化,才能了解到语言的真面目。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有很多很有意义的研究要作。我非常希望中国和西方的语言学家能够齐心协力地在新世纪里求出一些道理来。
这二三十年来由于有大量的计算机运用在建模仿真,我们对演化论的了解又迈进了一大步。霍兰(John H.Holland)1995年的书现在有中译本,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发行,书名里的三个词——隐秩序、适应、复杂——都是目前很多学科正在研究的课题。这些课题再加上混沌论里的一些基本概念,很可能是21世纪的一门重要的新科学。
“适者生存”这个想法在20世纪的演化论里扮了极重要的角色,作了很多贡献。可是单靠它来解释所有的演化似乎是不够的,尤其是一些非线形的复杂现象,包括屡次像冰化成水那样的相位改变。语言究竟是怎样在短短的十万年左右的时间内产生的:从无变到有,从个别的词变到无限多的句子,产生出这么多种奇妙的语法,这些语言学里最基本的问题希望也可以借助这门新科学来研究出些道理来。这也是语言学的一个新方向。工作量当然是很大,更希望国内的同行们也会对这些问题有兴趣,来参与这项工作。
书中有的文章是合作的成果,我在这里要感谢北京大学林焘教授,麻省大学沈钟伟教授,阳明大学曾志朗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柯津云女士,慷慨诚挚地与我分享他们的劳动和创见。编成这样一本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石锋教授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做完了这件事。校对的时候,又由汪锋先生及林千哲先生帮助,商务印书馆的金欣欣先生关照。无论这本书对于语言研究最终会有什么用处,我们都不会忘记这几位朋友曾经付出的努力。
原本,我来香港是为了能够看到她回归祖国的怀抱,身临其境地体验中国人的欣喜与骄傲,打算1997年之后就直接返回加州。但是我留下来了,在香港一年又一年,因为我实在不想离开这些志同道合的学生和同事,我们在一起分享着那么多求学的欢愉。所以,最后,我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以及这里的一些新朋友。
王 士 元
2001年6月
香港,马鞍山
收入这本书里的多数文章原先是用英文在美国发表的,中国的读者也许不大容易直接看到。当石锋教授建议把文章的译文和中文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一本文集的时候,我就欣然同意了。李行德教授最近在《中国语言学报》里(JCL 28,116—162,2000)分析了中国和西方的语言学,他说这两个传统的距离,还是太远。我很赞同他的看法。如果这本文集能够为沟通中国和西方的语言学起一点促进作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十几篇文章的写作时间跨越了三十多年,其中有的是源自我早期在语音学方面的工作。有人曾把语音学称为语言学“不可缺少的基础”,这是颇有道理的。书中也有些文章是有关文字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对我们独特的文字系统产生浓厚的兴趣,其余的文章主要是讨论语言演变的本质的,特别是从方法论的观点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探讨。
这些论文涉及好几个学科的领域,这正好体现了我的这样一个信念: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真正理解语言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视野限制得太狭窄,就不能因已有的学科界限而墨守成规。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犹如画在沙滩上的线条,随着每一次先进知识的波涛到来,这边界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完全消失。人类的知识,特别是研究语言的知识,应该是彼此相连的,并且最终是相互贯通的。
尤其是研究语言变化,我们不得不借鉴生物学里发展出来的演化论。语言变化跟生物变化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这一点达尔文早就讨论过。他在1859年出版的书的第14章,提出过这样的假设:世界上人群的综合谱系也就是世界上语言的谱系。大家知道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基因是经常交换而混合成一体的,同时,这群人的语言也是经常相互影响而大致相同的,可是要是有一部分人离开主群很久,他们的基因跟他们的语言在新的环境里就会改变,时间越久,差异就越大:语言变得快,几百年后他们的话就可能跟主群的话互不通音了,基因变得比较慢,但是久而久之世界上所有的人群中的差异就逐渐积累出来了。
因此研究基因时所发明的一些方法及模型,例如计算距离以及画树形图,都可以用来研究语言。基因跟语言的共同之处是Cavalli Sforza教授几十年来继承达尔文的假设所探讨的焦点,他最近出版的书《基因、人群与语言》已有中译本,是很值得参考的。
可是,这两种变化也有一些很基本的差异,也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首先,“适者生存”这个演化论里选择的概念所指的对象是生物竞争,而语言只是寄生在人群里的一种文化系统。一个语言的利或弊当然可能间接地影响一群人的命运,可是人群的繁荣或灭亡肯定有很多更直接的因素跟语言并不发生关系,因此演化论的有些思想不能完全照搬地用在语言上。
另一点基本的差异是传达的方式。一个婴儿的基因是完全从父母得来的——父亲母亲各供给一半染色体,精子和卵子结合的那一刹那就全部规定,不可能再有别的来源,这跟语言的传达很不一样。婴儿的话是由他主动地观察他周围的语言环境,一步一步地归纳出来的。语言环境里的材料,很可能有父母的话,但是来源繁多,并且是经常变的。家里听到的话,街上的话,老师及同学的话,都会影响他的语言生长。一个人的语言主要部分是在青春期定型的,这十几年的语言环境里的语料,或多或少地都是他语言的来源。
总而言之,小孩学的语言,跟他接触的环境里的语言的差异,一代一代地积累起来,就是历史语言学所研究的语言变迁。要是我们追本穷源,再扩大我们的视野,一直问到数万年前最早的语言,也不过就是一些基本词汇,而目前世界上的如此复杂的语言,还就是经过数千代的小孩学语积累而逐步形成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几样东西的关系搞清楚,就是小孩学语,语言接触以及语言演化,才能了解到语言的真面目。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有很多很有意义的研究要作。我非常希望中国和西方的语言学家能够齐心协力地在新世纪里求出一些道理来。
这二三十年来由于有大量的计算机运用在建模仿真,我们对演化论的了解又迈进了一大步。霍兰(John H.Holland)1995年的书现在有中译本,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发行,书名里的三个词——隐秩序、适应、复杂——都是目前很多学科正在研究的课题。这些课题再加上混沌论里的一些基本概念,很可能是21世纪的一门重要的新科学。
“适者生存”这个想法在20世纪的演化论里扮了极重要的角色,作了很多贡献。可是单靠它来解释所有的演化似乎是不够的,尤其是一些非线形的复杂现象,包括屡次像冰化成水那样的相位改变。语言究竟是怎样在短短的十万年左右的时间内产生的:从无变到有,从个别的词变到无限多的句子,产生出这么多种奇妙的语法,这些语言学里最基本的问题希望也可以借助这门新科学来研究出些道理来。这也是语言学的一个新方向。工作量当然是很大,更希望国内的同行们也会对这些问题有兴趣,来参与这项工作。
书中有的文章是合作的成果,我在这里要感谢北京大学林焘教授,麻省大学沈钟伟教授,阳明大学曾志朗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柯津云女士,慷慨诚挚地与我分享他们的劳动和创见。编成这样一本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石锋教授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做完了这件事。校对的时候,又由汪锋先生及林千哲先生帮助,商务印书馆的金欣欣先生关照。无论这本书对于语言研究最终会有什么用处,我们都不会忘记这几位朋友曾经付出的努力。
原本,我来香港是为了能够看到她回归祖国的怀抱,身临其境地体验中国人的欣喜与骄傲,打算1997年之后就直接返回加州。但是我留下来了,在香港一年又一年,因为我实在不想离开这些志同道合的学生和同事,我们在一起分享着那么多求学的欢愉。所以,最后,我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以及这里的一些新朋友。
王 士 元
2001年6月
香港,马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