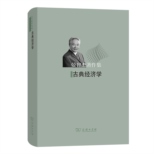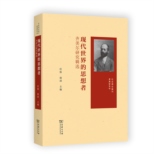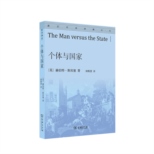显示全部序言
本书的目的,今天仍然与其1990年初版时一样,主要是向读者介绍社会科学中的一件极为重要并且耐人寻味的事情,那就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碰撞。这是两门社会科学在重大问题上互补不足的碰撞,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现实。
然而,今天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对话与1990年时一样,仍然是试探性的,两门学科之间也没有出现联盟。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都有一些好的观点,所有这些都值得人们倾听和尊敬。因本书而接受采访的17位人士都是杰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为这场对话的进行做了添砖加瓦的工作。
读者阅读本书将会发现,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相互分离、相互变得如此之隔膜,有一段长且复杂的历史。19世纪经济学在欧洲作为一门现代科学诞生的时候,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处得非常融洽。这一点可以用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为证。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它们却朝完全不同的方向走去。经济学的重心脱离了社会的其他方面而专一地集中在经济利益问题上,更一般地说,经济学的重心脱离了社会的结构。社会学则只处理留给它的一隅之地:用强调社会结构的方法,分析非经济的论题。双方的漠视甚为严重,借用熊彼特的一句挖苦话,经济学家现在正构建自己的粗浅的社会学,社会学家也在构建他们自己粗浅的经济学。
这种相互分离和漠视的状况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仍然存在,而这时,首先是经济学家,然后是社会学家,已经开始了对对方地盘的侵犯。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社会学,现在突然变得模糊起来。在此过程中,在经济学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是加里•贝克尔(第1章的受访人),他借助经济学分析工具,对一系列非经济学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其成果是在犯罪、教育、家庭和许多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划时代的洞见。本书出版几年后,加里•贝克尔因他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同样,在本书出版后,阿玛蒂亚•森(第14章的受访人)和乔治•阿克洛夫(第3章的受访人)也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本书在1990年面世的时候,人们立刻就明白了它的价值所在,即它让当时一批尝试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社会学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本书所采访的经济学家都是一些知名人士——他们同属一门显学——但社会学家却明显不同,他们属于一个相对来说不太受人重视的行业。而且多数社会学家完全不为世人所知,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创建一门全新的经济社会学,也完全不为世人所知。
创建一门全新的经济社会学的尝试首先出现在1981年。当时,哈里森•怀特(第4章的受访人)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理解市场问题的关键,必须在行为人之间所存在的社会关系中寻找。几年后,马克•格拉诺福特(第5章的受访人)发表了一篇经济社会学方面的通论性文章,该文被很多人视为是对经济社会学所从事范围的宣言。该文也因提出了“嵌入”(embeddedness)概念而著名(《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问题》,载《美国社会学杂志》,1985年)。
本书出版以后,我本人也主要致力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我一直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经济社会学的进展。在我最近的一本书《经济社会学原理》(2003)中,我注意到,自1980年代怀特和格拉诺福特开始的这一发展,今天在美国已成为方兴未艾的“新经济社会学”学派。其两大重要思想是:(1)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的;(2)所有的经济制度都要作为社会结构来理解。这两个主张意味着,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必须涉及到社会关系。像经济学家那样,只是简单地考虑经济利益以及这些经济利益如何驱动人类的行为,是不充分的。
自1980年代以来,主要出现在美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已经在几所知名大学里传播开来,比如说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康奈尔大学等。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研究成果,如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的《社会缺陷》(<EM>Social Holes</EM>)以及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的《为无价的孩子定价》(<EM>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EM>)等。新经济社会学主要利用了社会学中已有的三个范畴:网络分析法、组织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对新经济社会学现有状况的总结可以参见表一。
在我自已的研究中,我一直试图向人们表明,目前还存在另外一些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这些方法与人们认为属于新经济社会学的方法有所不同。一个例子是在法国。法国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自己的经济社会学方法,其代表人物是彼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布尔迪厄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年的阿尔及利亚》(<EM>Algeria 1960</EM>)、《区隔》(Distinction)和《经济的社会结构》(<EM>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Economy</EM>)。布尔迪厄将自己的理论视角切入经济问题,重点讨论这样一些概念:惯习、场和资本的不同形式(主要是社会、文化和金融资本)。布尔迪厄也写过一些关于社会和经济利益的作用的文章,并一直强调这些作用具有与社会结构同样的重要性。
我也认为,经济社会学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是找不到的,这只能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去寻找,尤其是在《经济与社会》中寻找。对那些对我的这一观点感兴趣的读者,我推荐我1998年出版的书《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我想只需这样说就足够了:韦伯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今天的经济社会学家,这不仅表现在他在经济史和法学等方面的博学,最重要的区别点还在于,韦伯坚持认为,人类行为由两个因素组成:利益和社会关系。下面引述的这段名言可以概括出韦伯通常立场:
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和合理的利益直接控制着人的行为。然而,由“思想”创造出的“现实形象”常常像扳道工那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轨道被利益推动向前。
在我的近著《经济社会学原理》一书中,我试图指出,今天的经济社会学不恰当地把实际发生在经济中的每一件事都视为社会关系的独一无二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赞同并追随韦伯的观点)认为,驱使经济行为的是与社会关系相关的利益。两者常常是纠结在一起的,不能分开。比如,制度就不能视为是规则的组成(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流行看法)。它们可以更好地概念化为靠社会关系锁定在不同形式中的利益。在《经济社会学原理》中,这种观点已被应用于一系列的问题,如公司、市场等等。
最后,我衷心地希望中国读者会喜欢这本书,读完这本书后脸上会浮现笑意。我一直坚信,智性的活动,包括社会科学,应该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事,这也是我选择将我自己的观点和其他人的观点用访谈的形式予以表达的原因。或许有一天,我还能读到来自中国的、译成了英文的同样的书吧?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
2002年11月27日于绮色佳
然而,今天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对话与1990年时一样,仍然是试探性的,两门学科之间也没有出现联盟。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都有一些好的观点,所有这些都值得人们倾听和尊敬。因本书而接受采访的17位人士都是杰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为这场对话的进行做了添砖加瓦的工作。
读者阅读本书将会发现,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相互分离、相互变得如此之隔膜,有一段长且复杂的历史。19世纪经济学在欧洲作为一门现代科学诞生的时候,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处得非常融洽。这一点可以用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为证。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它们却朝完全不同的方向走去。经济学的重心脱离了社会的其他方面而专一地集中在经济利益问题上,更一般地说,经济学的重心脱离了社会的结构。社会学则只处理留给它的一隅之地:用强调社会结构的方法,分析非经济的论题。双方的漠视甚为严重,借用熊彼特的一句挖苦话,经济学家现在正构建自己的粗浅的社会学,社会学家也在构建他们自己粗浅的经济学。
这种相互分离和漠视的状况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仍然存在,而这时,首先是经济学家,然后是社会学家,已经开始了对对方地盘的侵犯。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社会学,现在突然变得模糊起来。在此过程中,在经济学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是加里•贝克尔(第1章的受访人),他借助经济学分析工具,对一系列非经济学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其成果是在犯罪、教育、家庭和许多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划时代的洞见。本书出版几年后,加里•贝克尔因他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同样,在本书出版后,阿玛蒂亚•森(第14章的受访人)和乔治•阿克洛夫(第3章的受访人)也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本书在1990年面世的时候,人们立刻就明白了它的价值所在,即它让当时一批尝试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社会学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本书所采访的经济学家都是一些知名人士——他们同属一门显学——但社会学家却明显不同,他们属于一个相对来说不太受人重视的行业。而且多数社会学家完全不为世人所知,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创建一门全新的经济社会学,也完全不为世人所知。
创建一门全新的经济社会学的尝试首先出现在1981年。当时,哈里森•怀特(第4章的受访人)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理解市场问题的关键,必须在行为人之间所存在的社会关系中寻找。几年后,马克•格拉诺福特(第5章的受访人)发表了一篇经济社会学方面的通论性文章,该文被很多人视为是对经济社会学所从事范围的宣言。该文也因提出了“嵌入”(embeddedness)概念而著名(《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问题》,载《美国社会学杂志》,1985年)。
本书出版以后,我本人也主要致力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我一直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经济社会学的进展。在我最近的一本书《经济社会学原理》(2003)中,我注意到,自1980年代怀特和格拉诺福特开始的这一发展,今天在美国已成为方兴未艾的“新经济社会学”学派。其两大重要思想是:(1)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的;(2)所有的经济制度都要作为社会结构来理解。这两个主张意味着,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必须涉及到社会关系。像经济学家那样,只是简单地考虑经济利益以及这些经济利益如何驱动人类的行为,是不充分的。
自1980年代以来,主要出现在美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已经在几所知名大学里传播开来,比如说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康奈尔大学等。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研究成果,如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的《社会缺陷》(<EM>Social Holes</EM>)以及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的《为无价的孩子定价》(<EM>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EM>)等。新经济社会学主要利用了社会学中已有的三个范畴:网络分析法、组织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对新经济社会学现有状况的总结可以参见表一。
在我自已的研究中,我一直试图向人们表明,目前还存在另外一些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这些方法与人们认为属于新经济社会学的方法有所不同。一个例子是在法国。法国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自己的经济社会学方法,其代表人物是彼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布尔迪厄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年的阿尔及利亚》(<EM>Algeria 1960</EM>)、《区隔》(Distinction)和《经济的社会结构》(<EM>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Economy</EM>)。布尔迪厄将自己的理论视角切入经济问题,重点讨论这样一些概念:惯习、场和资本的不同形式(主要是社会、文化和金融资本)。布尔迪厄也写过一些关于社会和经济利益的作用的文章,并一直强调这些作用具有与社会结构同样的重要性。
我也认为,经济社会学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是找不到的,这只能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去寻找,尤其是在《经济与社会》中寻找。对那些对我的这一观点感兴趣的读者,我推荐我1998年出版的书《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我想只需这样说就足够了:韦伯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今天的经济社会学家,这不仅表现在他在经济史和法学等方面的博学,最重要的区别点还在于,韦伯坚持认为,人类行为由两个因素组成:利益和社会关系。下面引述的这段名言可以概括出韦伯通常立场:
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和合理的利益直接控制着人的行为。然而,由“思想”创造出的“现实形象”常常像扳道工那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轨道被利益推动向前。
在我的近著《经济社会学原理》一书中,我试图指出,今天的经济社会学不恰当地把实际发生在经济中的每一件事都视为社会关系的独一无二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赞同并追随韦伯的观点)认为,驱使经济行为的是与社会关系相关的利益。两者常常是纠结在一起的,不能分开。比如,制度就不能视为是规则的组成(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流行看法)。它们可以更好地概念化为靠社会关系锁定在不同形式中的利益。在《经济社会学原理》中,这种观点已被应用于一系列的问题,如公司、市场等等。
最后,我衷心地希望中国读者会喜欢这本书,读完这本书后脸上会浮现笑意。我一直坚信,智性的活动,包括社会科学,应该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事,这也是我选择将我自己的观点和其他人的观点用访谈的形式予以表达的原因。或许有一天,我还能读到来自中国的、译成了英文的同样的书吧?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
2002年11月27日于绮色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