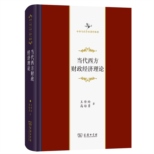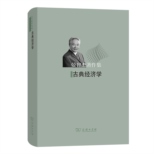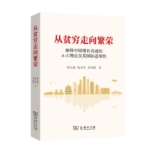显示全部后记
早在1987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之日起,我就开始在河西走廊这个浩荡千里的长廊里走来走去,转去转来,断断续续,走遍了河西7个城市,20个县(区),一半以上的乡镇。从祖国“镍都”走到西北“钢城”,从皑皑冰川走进茫茫沙漠,从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的源头走到尽头,从绿洲走进戈壁,上嘉峪关出玉门关,登长城上祁连山,进莫高窟出马蹄寺,携铜奔马举夜光杯,尝遍了河西走廊的美酒佳肴,从皇台、丝路春到昭武、“腾格里XO”,每每醉在廊里,乐在其中,思在心头,到今天已经走过了整整16个春秋。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的神秘,古“丝绸之路”的兴衰,金张掖银武威的驰名,中国第一口油井的开掘,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地酒泉“航天城”的神秘莫测,中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首飞成功的举世瞩目,国家商品粮基地的建设,茫茫戈壁大漠的喧啸,“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凄凉,甚至黑风暴的肆虐和古老城郭的废弃兴衰等等,一件件记载着河西走廊发展演变的历史事件,使这个绵延千里的天然走廊越发变得复杂模糊,不可捉摸驾驭。我对河西走廊的认识越发模糊不清。虽然迄今为止无法就河西走廊的今天和未来提出“革命性”的建设方案,但科学工作者面对模糊事件必要探其究竟的探知心理,驱动着我仍想“不顾一切”地将我“如饥似渴”研究河西走廊得出的初步结论“和盘托出”,以供有志于河西走廊研究与建设的同仁们分享和研讨。
出于对河西走廊的“偏爱”,在选做硕士论文时就有意识地选择了河西走廊黑河中游地区,这一选择对我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以“河西走廊绿洲空间结构分析”为题于1990年在《开发研究》上正式发表,手写稿变成铅字后的快感激发了我对科研工作的浓厚兴趣,奠定了学术生涯的良好开端。自此以后我把河西走廊作为自身从事科学研究的“主战场”,不少科研项目基本上围绕河西走廊去申请研究。获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使我有机会研究河西走廊水资源约束下的城市化过程和城市发展模式等问题;获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使我有机会研究河西走廊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战略、产业发展重点、示范园区建设等问题;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给了我研究河西走廊三大流域生态经济带及其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耦合系统规划的问题;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使我投入精力研究河西走廊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城市扩张趋向与城镇体系建设等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知识创新工程引进人才专项基金项目使我有机会关注河西走廊生态系统—生产系统—生活系统“三生”耙合系统与协调发展等问题。这些项目的开展为研究河西走廊奠定了扎实的学术积累和雄厚的资金基础。
由于工作的随机性和较强的实践性,对河西走廊的研究总是断断续续,一直苦于没有时间坐下来静静地思考,周密地分析河西走廊今天身处何处?未来迈向何方?前方的路该怎样走?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在一夜之间使所有的人放慢了节奏,停滞了脚步。我也毫不例外地“静”了下来,腾出本该是计划外的时间,“收回”了心,坐在家里开始整理、归纳、总结多年来关于河西走廊研究的点点滴滴的认识,沉溺在枯燥的数学模拟与数字计算的日子中,陶醉在河西走廊的每一处精彩的回忆里,迷失在平生第一次学着养花的氛围中。眼看着朵朵鲜花在我的亲自“催化”下争相吐艳,给我增添了无限的惬意和快慰。尽管窗外呼叫着的120急救车动辄打断我的思绪,但我还是不知不觉地忘却了来自户外的种种“非典”恐慌,把自己的思绪拉回到河西走廊。
经过三个多月的封闭式煎熬,终于完成了这本关于河西走廊研究的著作,经过反复考虑并听取相关专家建议,决定将本书起名为“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走廊”,以唤起更多的人从国家全局的角度,从树立科学发展观的角度,从西部大开发和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的角度,跳出从河西走廊审视河西走廊、研究河西走廊、建设河西走廊的狭隘视线,把河西走廊真正建设成为中国西部大地山川秀美的生态经济走廊。
《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走廊》书稿的付梓,是我近10年研究河西走廊迈出的第一步。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投入精力从不同角度和切入点走进河西走廊,去做无尽地探索,与河西走廊同呼吸!
方创琳
2003年6月6日于北京科学园
出于对河西走廊的“偏爱”,在选做硕士论文时就有意识地选择了河西走廊黑河中游地区,这一选择对我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以“河西走廊绿洲空间结构分析”为题于1990年在《开发研究》上正式发表,手写稿变成铅字后的快感激发了我对科研工作的浓厚兴趣,奠定了学术生涯的良好开端。自此以后我把河西走廊作为自身从事科学研究的“主战场”,不少科研项目基本上围绕河西走廊去申请研究。获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使我有机会研究河西走廊水资源约束下的城市化过程和城市发展模式等问题;获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使我有机会研究河西走廊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战略、产业发展重点、示范园区建设等问题;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给了我研究河西走廊三大流域生态经济带及其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耦合系统规划的问题;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使我投入精力研究河西走廊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城市扩张趋向与城镇体系建设等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知识创新工程引进人才专项基金项目使我有机会关注河西走廊生态系统—生产系统—生活系统“三生”耙合系统与协调发展等问题。这些项目的开展为研究河西走廊奠定了扎实的学术积累和雄厚的资金基础。
由于工作的随机性和较强的实践性,对河西走廊的研究总是断断续续,一直苦于没有时间坐下来静静地思考,周密地分析河西走廊今天身处何处?未来迈向何方?前方的路该怎样走?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在一夜之间使所有的人放慢了节奏,停滞了脚步。我也毫不例外地“静”了下来,腾出本该是计划外的时间,“收回”了心,坐在家里开始整理、归纳、总结多年来关于河西走廊研究的点点滴滴的认识,沉溺在枯燥的数学模拟与数字计算的日子中,陶醉在河西走廊的每一处精彩的回忆里,迷失在平生第一次学着养花的氛围中。眼看着朵朵鲜花在我的亲自“催化”下争相吐艳,给我增添了无限的惬意和快慰。尽管窗外呼叫着的120急救车动辄打断我的思绪,但我还是不知不觉地忘却了来自户外的种种“非典”恐慌,把自己的思绪拉回到河西走廊。
经过三个多月的封闭式煎熬,终于完成了这本关于河西走廊研究的著作,经过反复考虑并听取相关专家建议,决定将本书起名为“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走廊”,以唤起更多的人从国家全局的角度,从树立科学发展观的角度,从西部大开发和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的角度,跳出从河西走廊审视河西走廊、研究河西走廊、建设河西走廊的狭隘视线,把河西走廊真正建设成为中国西部大地山川秀美的生态经济走廊。
《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走廊》书稿的付梓,是我近10年研究河西走廊迈出的第一步。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投入精力从不同角度和切入点走进河西走廊,去做无尽地探索,与河西走廊同呼吸!
方创琳
2003年6月6日于北京科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