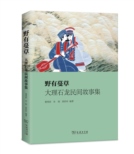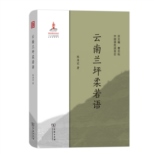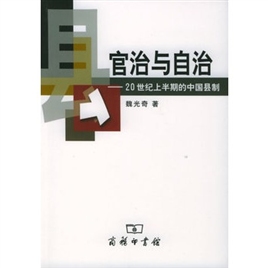显示全部序言
自 序
中国古代的地方初级政区,自秦汉至唐宋统称“县”;至元代,有些设于省、路、府之下的“州”没有属县,因此也属于地方初级政区。 明、清承元制,在少数地方设“州”和“直隶州”,与“县”同为地方初级政区,并称州县。至清代,除州、县外又在边远地区设“厅”和“直隶厅”,而极少数作为二级地方政区的“府”除管辖州、县外也有自己的直辖区境。于是,清代的地方初级政区就有府、厅、州、县等四种形式。入民国后,将有直辖区境的府、直隶厅、直隶州和其他散州、散厅一律改为“县”,地方初级政区再次统一为“县”。 国民政府时期,少数繁庶县份改为“市”,省以下的地方二级政区因此又有县、市两种。不过,中国的初级地方政区形式无论怎样变化,却始终是以“县”为主要形式。此外,清末以来改变古代在县以下不设治的传统而开始建立的各种区乡行政,也全都隶属于县(市)。鉴于这种情况,人们就完全有理由用“县制”一词来指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基层行政制度。如1940年代胡次威著《民国县制史》,其所述内容就同时包括主题时期的县行政制度和区乡制度。本书主题中所使用的“县制”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同于此。至于“官治”与“自治”,是20世纪上半期在“县制”问题领域中为人们所熟悉的话语,前者是指由国家自上而下任命官员运作的国家行政,后者是指由地方社会自下而上推选本地人士运作的地方自治。我认为,这两种基本模式的相互排斥与结合,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县制改革和演变的主轴。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我曾经在晋东南地区的一个山村插队,本本分分地做了四年的农民。这种经历,使得我对农民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对农村问题产生了很浓的兴趣。在这种非理性情感与兴趣的基础上,我在后来的专业学习中逐渐确立了一种十分理性的观点:以县乡一体的社会、行政系统为基础层面和基本单元,是中国社会结构不同于其他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特点即使在今后可以预见的现代化进程中,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因此,有社会责任心的学人应该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种角度对中国的县制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在填补有关学术领域空白的同时,为当代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和基层制度建设提供借鉴。基于这种认识,1980年代我在河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曾组织部分学生利用假期回各自原籍对县制问题进行社会调查,但因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取得成果。1990年代初,我开始了对中国近代县制问题的研究工作。当时,我读硕士研究生时期的导师山西大学乔志强先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命我就清末民初华北地区的地方自治推行情况进行研究,并撰写结题书稿中的有关章节。我性格本来拘谨,受命之后不敢怠慢,在图书馆苦苦蹲了近一年的时间,动手收集抄录了数十万字的资料,按时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同时也对近代县制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几年间,我继续进行有关的研究工作,并开始发表有关于清末民初直隶地方自治问题以及清代乡里制度问题的论文。1999年,我申报的科研课题“20世纪前期中国县乡行政制度研究”通过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在同事和学生们的帮助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2001年秋以50万字的书稿形式结题,并通过专家鉴定。不过,我自己深知结题书稿中尚存在各种层次的缺陷和问题,因此不敢即时谋求出版。此后又经过两年多的修改、补充和删节,终于以现在这种面貌付梓,而绝非自谦地说,我自己对这一稿仍是很不满意的。不过,由于以我浅陋的学识无力在短时间内进一步做全面、深入的修改,在各种现实因素的作用下,只好让“丑媳妇”先去“见公婆”,以冀问世后得到师友、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我看来,这部书作或许能够在几个方面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有所贡献,即:对近代县制范畴内各种制度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力求其“通”;在阐述各有关制度之初始设计的同时,力求探讨其实际实行情况;对清代至国民政府时期县制的财政层面进行了初步探讨(我认为,财政制度的落后至今是制约我国县乡制度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对蕴藏于县制演变背后的社会势力兴衰,做了初步探讨;以史为鉴,对今天的中国县制改革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建议。这部书作存在许多缺憾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我自己可以发见者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自己理论素养较低,且事先抱定以“述”为主、争取寓“论”于“述”的宗旨,所以理论分析较为薄弱;中国近代县制问题涉及面极广,不少本应探讨的问题未能进入自己的视野,例如,清末至国民政府时期各种县乡行政组织的施政活动乃是当时县制的动态表现,但由于精力有限,在这部书作中没有能够进行深入探讨;近代县制问题研究的相关资料十分丰富,自己虽然下了很大气力进行收集整理,但不仅谈不上穷尽,恐怕对于某些基本资料也难免有遗漏。此外,对于各种具体问题的阐述,更是存在不少片面和错误之处。所有这些,都诚恳希望专家、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魏 光 奇
2003年11月
中国古代的地方初级政区,自秦汉至唐宋统称“县”;至元代,有些设于省、路、府之下的“州”没有属县,因此也属于地方初级政区。 明、清承元制,在少数地方设“州”和“直隶州”,与“县”同为地方初级政区,并称州县。至清代,除州、县外又在边远地区设“厅”和“直隶厅”,而极少数作为二级地方政区的“府”除管辖州、县外也有自己的直辖区境。于是,清代的地方初级政区就有府、厅、州、县等四种形式。入民国后,将有直辖区境的府、直隶厅、直隶州和其他散州、散厅一律改为“县”,地方初级政区再次统一为“县”。 国民政府时期,少数繁庶县份改为“市”,省以下的地方二级政区因此又有县、市两种。不过,中国的初级地方政区形式无论怎样变化,却始终是以“县”为主要形式。此外,清末以来改变古代在县以下不设治的传统而开始建立的各种区乡行政,也全都隶属于县(市)。鉴于这种情况,人们就完全有理由用“县制”一词来指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基层行政制度。如1940年代胡次威著《民国县制史》,其所述内容就同时包括主题时期的县行政制度和区乡制度。本书主题中所使用的“县制”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同于此。至于“官治”与“自治”,是20世纪上半期在“县制”问题领域中为人们所熟悉的话语,前者是指由国家自上而下任命官员运作的国家行政,后者是指由地方社会自下而上推选本地人士运作的地方自治。我认为,这两种基本模式的相互排斥与结合,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县制改革和演变的主轴。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我曾经在晋东南地区的一个山村插队,本本分分地做了四年的农民。这种经历,使得我对农民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对农村问题产生了很浓的兴趣。在这种非理性情感与兴趣的基础上,我在后来的专业学习中逐渐确立了一种十分理性的观点:以县乡一体的社会、行政系统为基础层面和基本单元,是中国社会结构不同于其他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特点即使在今后可以预见的现代化进程中,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因此,有社会责任心的学人应该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种角度对中国的县制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在填补有关学术领域空白的同时,为当代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和基层制度建设提供借鉴。基于这种认识,1980年代我在河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曾组织部分学生利用假期回各自原籍对县制问题进行社会调查,但因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取得成果。1990年代初,我开始了对中国近代县制问题的研究工作。当时,我读硕士研究生时期的导师山西大学乔志强先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命我就清末民初华北地区的地方自治推行情况进行研究,并撰写结题书稿中的有关章节。我性格本来拘谨,受命之后不敢怠慢,在图书馆苦苦蹲了近一年的时间,动手收集抄录了数十万字的资料,按时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同时也对近代县制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几年间,我继续进行有关的研究工作,并开始发表有关于清末民初直隶地方自治问题以及清代乡里制度问题的论文。1999年,我申报的科研课题“20世纪前期中国县乡行政制度研究”通过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在同事和学生们的帮助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2001年秋以50万字的书稿形式结题,并通过专家鉴定。不过,我自己深知结题书稿中尚存在各种层次的缺陷和问题,因此不敢即时谋求出版。此后又经过两年多的修改、补充和删节,终于以现在这种面貌付梓,而绝非自谦地说,我自己对这一稿仍是很不满意的。不过,由于以我浅陋的学识无力在短时间内进一步做全面、深入的修改,在各种现实因素的作用下,只好让“丑媳妇”先去“见公婆”,以冀问世后得到师友、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我看来,这部书作或许能够在几个方面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有所贡献,即:对近代县制范畴内各种制度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力求其“通”;在阐述各有关制度之初始设计的同时,力求探讨其实际实行情况;对清代至国民政府时期县制的财政层面进行了初步探讨(我认为,财政制度的落后至今是制约我国县乡制度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对蕴藏于县制演变背后的社会势力兴衰,做了初步探讨;以史为鉴,对今天的中国县制改革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建议。这部书作存在许多缺憾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我自己可以发见者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自己理论素养较低,且事先抱定以“述”为主、争取寓“论”于“述”的宗旨,所以理论分析较为薄弱;中国近代县制问题涉及面极广,不少本应探讨的问题未能进入自己的视野,例如,清末至国民政府时期各种县乡行政组织的施政活动乃是当时县制的动态表现,但由于精力有限,在这部书作中没有能够进行深入探讨;近代县制问题研究的相关资料十分丰富,自己虽然下了很大气力进行收集整理,但不仅谈不上穷尽,恐怕对于某些基本资料也难免有遗漏。此外,对于各种具体问题的阐述,更是存在不少片面和错误之处。所有这些,都诚恳希望专家、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魏 光 奇
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