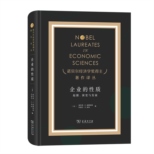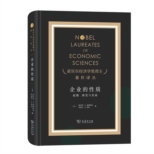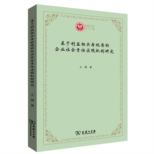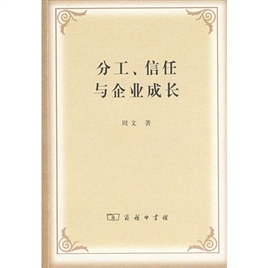显示全部序言
企业是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成长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因此,研究企业成长是理解经济成长的关键。但是正如彭罗斯所言:“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一位经济学家尝试过研究企业成长的系统理论。这让我觉得非常奇怪,所以我确信任何作这个尝试的人都应当谨慎地进行每一步研究。”
而之所以需要“谨慎”地进行每一步研究,是因为企业成长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企业制度变革、结构调整以及竞争力、战略和管理行为研究等诸多方面。也正因为如此,有关企业成长的问题既是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企业成长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斯密认为,分工是企业成长的主要诱因——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促进了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导致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过来,扩大的生产规模又深化了企业的分工协作。这种循环累进,带来了企业的规模经济,也就实现了企业成长。继斯密之后,约翰•穆勒和马歇尔重点探讨了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的关系,至此,始于分工视角的企业成长演变成了简单的规模经济理论。真正系统地从理论上研究企业成长的是彭罗斯,她第一次将企业成长作为分析对象,认为企业是一个资源的集合体,强调管理和协调对企业成长的作用,主张用成长经济来替代传统的规模经济。
但是主流经济学仅仅将企业看做是一个生产函数,形成了企业的“黑箱”理论,这严重制约了企业以及企业成长理论的推进。作为对这种“黑板经济学”的强烈反对的理论成果,科斯以交易成本的概念,重新开启了企业研究的大门。由此,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研究的蔚为大观的成果。然而,新制度经济学更多强调的是市场与企业的替代性,而忽视了企业产生和成长的历史和逻辑观。事实上,在市场出现之前,早已出现了为交换而生产的组织形式。因此,分工无论是从历史和逻辑上都是企业产生的起点。这一起点毫无疑问意味着对企业、企业成长研究的古典回归。
分工意味着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交换没有信任是无法完成的。交换无法完成,分工就不可能继续深化和扩展,企业也就难以实现成长,由此,信任与企业成长也紧密地联系起来。基于这样的思路,本文作者构建了一个分工、信任与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企业被定义为以人为主体、人与人关系为中心的一系列关系的组合体,企业的治理结构主要是围绕企业成长来不断地动态调整不同主体利益的协调机制;企业成长的实质是企业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契约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从信任的视角来看,企业成长必须经历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演化。因此,企业成长,一方面是源于分工的演进;另一方面得益于信任半径的扩展。本书更多地把信任视为影响企业成长的一种社会资本,嵌入企业成长的路径中。因此,能否拥有和扩展信任,是企业成长的关键。
作为一种回归古典的尝试,以及将“经济人”嵌入社会关系中,从而将信任纳入企业成长分析框架,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企业定义为以信任为黏合剂的分工协作性的要素集合体,分工协作中依靠亲缘、血缘信任向依靠制度信任的转变,是企业实现成长的关键;而从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的演进,同时也是分工深化的过程,分工深化不仅有助于企业成长,而且促成了产业集群的发展;根据成长的不同阶段,提出了动态的企业家概念:在企业创立时期,企业家应具有“冒险”和“洞察力”,在企业成长阶段,因为分工和专业化的趋势,企业家应具有创新和协调力;相应地,还提出了从制度化角度去理解市场的观点,把市场看成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这样,交易的扩大与信任的扩展是相互推动和相互促进的。最后,作者从历史视角、运用本书的理论框架考察了企业成长问题,为作者提出的分工、信任与企业成长理论框架作出了经验意义上的诠释。
当然,本书作为一项尝试性的研究,难免存在有待商榷和进一步探讨的地方,需要作者继续探索,不懈努力。同时,作为对探索性研究的鼓励,我恳切地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够点燃企业理论古典回归的“星星之火”,引起更多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并最终形成我国学界企业理论研究的“燎原”之势!
丁任重
2008年9月1日
而之所以需要“谨慎”地进行每一步研究,是因为企业成长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企业制度变革、结构调整以及竞争力、战略和管理行为研究等诸多方面。也正因为如此,有关企业成长的问题既是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企业成长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斯密认为,分工是企业成长的主要诱因——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促进了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导致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过来,扩大的生产规模又深化了企业的分工协作。这种循环累进,带来了企业的规模经济,也就实现了企业成长。继斯密之后,约翰•穆勒和马歇尔重点探讨了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的关系,至此,始于分工视角的企业成长演变成了简单的规模经济理论。真正系统地从理论上研究企业成长的是彭罗斯,她第一次将企业成长作为分析对象,认为企业是一个资源的集合体,强调管理和协调对企业成长的作用,主张用成长经济来替代传统的规模经济。
但是主流经济学仅仅将企业看做是一个生产函数,形成了企业的“黑箱”理论,这严重制约了企业以及企业成长理论的推进。作为对这种“黑板经济学”的强烈反对的理论成果,科斯以交易成本的概念,重新开启了企业研究的大门。由此,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研究的蔚为大观的成果。然而,新制度经济学更多强调的是市场与企业的替代性,而忽视了企业产生和成长的历史和逻辑观。事实上,在市场出现之前,早已出现了为交换而生产的组织形式。因此,分工无论是从历史和逻辑上都是企业产生的起点。这一起点毫无疑问意味着对企业、企业成长研究的古典回归。
分工意味着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交换没有信任是无法完成的。交换无法完成,分工就不可能继续深化和扩展,企业也就难以实现成长,由此,信任与企业成长也紧密地联系起来。基于这样的思路,本文作者构建了一个分工、信任与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企业被定义为以人为主体、人与人关系为中心的一系列关系的组合体,企业的治理结构主要是围绕企业成长来不断地动态调整不同主体利益的协调机制;企业成长的实质是企业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契约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从信任的视角来看,企业成长必须经历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演化。因此,企业成长,一方面是源于分工的演进;另一方面得益于信任半径的扩展。本书更多地把信任视为影响企业成长的一种社会资本,嵌入企业成长的路径中。因此,能否拥有和扩展信任,是企业成长的关键。
作为一种回归古典的尝试,以及将“经济人”嵌入社会关系中,从而将信任纳入企业成长分析框架,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企业定义为以信任为黏合剂的分工协作性的要素集合体,分工协作中依靠亲缘、血缘信任向依靠制度信任的转变,是企业实现成长的关键;而从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的演进,同时也是分工深化的过程,分工深化不仅有助于企业成长,而且促成了产业集群的发展;根据成长的不同阶段,提出了动态的企业家概念:在企业创立时期,企业家应具有“冒险”和“洞察力”,在企业成长阶段,因为分工和专业化的趋势,企业家应具有创新和协调力;相应地,还提出了从制度化角度去理解市场的观点,把市场看成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这样,交易的扩大与信任的扩展是相互推动和相互促进的。最后,作者从历史视角、运用本书的理论框架考察了企业成长问题,为作者提出的分工、信任与企业成长理论框架作出了经验意义上的诠释。
当然,本书作为一项尝试性的研究,难免存在有待商榷和进一步探讨的地方,需要作者继续探索,不懈努力。同时,作为对探索性研究的鼓励,我恳切地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够点燃企业理论古典回归的“星星之火”,引起更多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并最终形成我国学界企业理论研究的“燎原”之势!
丁任重
2008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