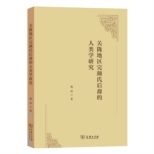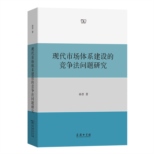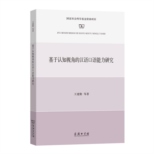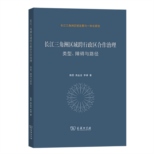第一章 中国碳排放与碳转移问题及测算(节选)
第一节 碳排放、碳转移与碳达峰问题概述
本节主要通过阐述碳排放、碳转移与碳达峰的关系,为后文中国碳达峰问题的研究奠定基础。其中,碳排放是碳达峰问题出现的根本缘由,是碳转移的前提;碳转移影响碳排放责任核算,进而影响碳达峰政策。
一、碳排放、碳转移与碳达峰
(一)碳排放与碳达峰
全球变暖是21世纪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并逐渐成为世界聚焦的全球性气候问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曾在报告中言明,全球变暖主要归咎于温室气体,而由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温室气体的主要组成部分,由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燃烧带来的能源消费碳排放是人类活动产生碳排放的主要形式。在全球范围内,碳排放始终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递增,对生态系统造成威胁。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中提到,2019年的碳排放规模相较于2010年多12%,相较于 1990年多54%,2021年的碳排放规模相较于2019年更甚。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的能源消费大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hina Emission Accounts and Datasets,CEADs)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中国的碳排放规模已达110亿吨,大约占全球碳排放总规模的28.87%。并且,碳排放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约占全国碳排放总规模的77%。1990—2019年间,中国碳排放量增长了近80%,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显著增加,已经是全球碳排放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碳减排行动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面对如此严峻的气候变暖形势,低碳减排逐渐成为全球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及其修正案、《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全球减排方案不断涌现。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的能源消费大国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都是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提出相较于2005年,2030年的碳排放强度实现60%—65%的下降目标,并努力实现碳达峰。在2020年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双碳”目标,计划中国碳排放于2030年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正处于能源转型关键时刻,减排压力不容小觑。而“双碳”目标的提出,正高度展现了中国的减排决心与担当。
(二)碳排放与碳转移
地区间碳排放可经由诸多途径发生转移,包括空气流通、光合作用、自然物质流转、经济活动等。从广义角度而言,碳转移包括经济系统中的碳排放转移和生态系统中的碳生物转移;从狭义角度而言,碳转移是指通过经济活动发生的全部隐含碳的排放转移。本书所指的碳转移即为狭义角度的隐含碳转移。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隐含碳是产品从获得原料、生产加工、运输到消费这段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包括直接与间接碳排放。随着地区间的经济流动,隐含碳隐藏在商品和货物贸易背后,形成隐含碳排放转移,即碳转移(郭正权,2021)。
在国内循环中,各地区为了优化资源配置,满足生产和消费需求,发挥其生产优势,省际的生产资料交换、生产价值分配和跨省域消费等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经济内循环的构建,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中国的省际经济流动规模日渐庞大。在
2017—2022年间,中国省际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2.8%。在全国贸易总额中,省际贸易额占比从38.2%提升至39.8%,并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在体量巨大的省际贸易背后,隐含碳转移问题不容小觑。
碳转移于消费地而言,是通过调入商品和货物所避免的直接碳排放;于生产地而言,是调出的商品和货物所产生的碳排放。例如,制造业大省会向其他地区输出工业产品,而以轻工业为主的地区会输入高碳产品以满足生活、生产需求,在此过程中,相伴而生的是隐含碳转移。隐含碳转移会致使生产所产生的碳排放与消费分离,进而导致一系列相关问题,如“碳泄漏”等,极大地不利于生产地的生态环境,会加剧其生态负担。因此,研究中国的碳转移问题在中国碳减排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由于经济流动需要综合地理环境、经济要素、资源禀赋和效率等做出最优选择,中国省际碳转移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驱动影响。研究碳转移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优化省际碳转移网络,促进各地区协作减排。
(三)碳排放责任核算与碳达峰
在地区间商品和货物贸易的过程中,隐含在其背后的碳排放发生转移,形成碳转移。生产地生产的商品和货物被其他地区消费,但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却由生产地承担,导致其承担了过多的碳排放责任。在此情形下,对各地区的碳排放责任进行核算,准确反映碳排放责任归属,需要将碳转移考虑其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落实“双碳”目标,需要推进“双碳工作”的基础制度建设,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省域作为政策落地的主要单位,其碳排放责任核算的准确性、公平性,是国家整体减碳目标实现的关键。
目前,碳排放责任界定的主流方法为生产者责任原则,在该原则下,消费地可通过地区间贸易将隐含碳排放转移至生产地,以此来规避碳排放责任,而生产地则需要承担非本地区消费的那部分碳排放责任。考虑到生产者责任原则的不公平性,随后提出了消费者责任原则,即“谁消费,谁承担”。但该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生产地减排意愿的降低,不利于中国减排进程的推进。出于公平性和减排目的双重考虑,生产者与消费者需要共同承担碳排放责任,即责任共担原则。该原则逐渐得到学者们的推崇。责任共担分配因子的确定成为主要难点,虽然近来涌现了不少相关研究,但目前并无统一定论。找到公平合理的责任共担分配因子,准确划分各地区应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有利于国家减排进程的推进和减排政策的实施。
二、碳排放测算问题
关于碳排放测算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能源排放系数为依托的能源使用测算法;二是以生产过程为线索的生命周期评价法;三是以投入产出表为工具的投入产出分析法。
(一)能源使用测算法
能源使用测算法是以能源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各单位的能源消耗数据与碳排放系数测算碳排放的一种方法,一般以直接碳排放为结果导向。该方法较为权威的应用为IPCC碳排放核算指南,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展开碳排放研究。武红(2015)借鉴IPCC碳排放核算指南,根据化石能源消费测算中国各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并结合空间自相关理论方法发现中国不同地区间具有差异化的减排特征和潜力。汪辉平和张准(Wang & Zhang,2022)也根据IPCC方法计算了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碳排放,同时构建空间灰色模型预测了2020—2025年各地区的碳排放量。何小钢和张耀辉(2012)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类一次能源为基准估算化石燃料燃烧的碳排放,得到中国工业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与劳动产出间的走势联系。除原始碳排放系数以外,也有学者对碳排放系数进行创新。例如,田成诗和陈雨(2021)构建了差异化碳排放系数,利用各碳源使用量测算2006—2016年中国各地区的农业碳排放规模,发现中国农业碳排放呈先降后升的态势,并基于此构建农业低碳化水平评价体系,得到农业低碳化水平整体有所欠缺的结论。
能源使用测算法的关键在于确定能源消耗规模和碳排放系数,可针对不同研究对象灵活选择能源数据,且简明易懂。但该方法的测算较为笼统,不确定性较大。而且,能源使用测算法是从生产角度计算碳排放,其结果仅限直接碳排放。
(二)生命周期评价法
生命周期评价法(LAC法)是根据生产活动过程,以生产、加工、销售、使用、废料回收等环节为分类单位,通过获取活动、过程、产品或服务在整个生产周期内投入的原料、能源和输出的产品、废弃物,核算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该方法遵循一种“自上而下”的核算逻辑,主要适用于针对单个产品或服务的碳排放核算。王云等(2011)利用生命周期评价法对循环燃烧技术系统进行了囊括“建设、运行、解体”三大过程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并结合全生命周期成本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助力低碳技术发展。王兆君等(2017)、埃兰基和兰迪斯(Eranki & Landis,2019)也采用生命周期评估法对轮胎产业进行了低碳评估。前者以子午线轮胎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传统轮胎,发现碳排放集中在使用阶段和生产阶段;后者以银胶菊轮胎为研究对象,并将传统轮胎作为对比,评估其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刘强等(2008)利用生命周期评价法对中国46类出口重点产品进行载能量和碳排放量核算,发现中国对外贸易所负载的能耗与碳排放规模较为庞大。
生命周期评价法的关键在于确定研究对象在全生命周期中的输入、输出清单,适合微观层面的计算,且计算过程详细清晰。但生命周期各环节边界的划分与确定较为复杂,环节中的排放数据难以获取,系统的完整性往往有所欠缺(耿涌等,2010;王俊博等,2023)。
(三)投入产出分析法
投入产出分析法是根据投入产出表的平衡关系,通过其中的初始、中间投入,中间、最终使用等数据反映生产活动中各经济主体的依存关系,并基于此对碳排放进行核算。该方法遵循一种“自下而上”的核算逻辑,以投入产出表为依据计算直接碳排放与间接碳排放,其优势在于可以对隐含碳排放进行测算(刘宇,2015),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碳排放测算研究中。投入产出分析又可以划分为单区域投入产出(SRIO)分析和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分析。
单区域投入产出(SRIO)分析用于测算单个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洪娜眉等(2022)基于2017年广东省投入产出表以及相关能源数据,测算了广东省11个产业部门的直接与间接碳排放规模,并分析其中的产业关联。蔡浩等(Cai et al.,2020)构建了中国2009—2016 年的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出口碳足迹的变化趋势。但由于单区域投入产出表的限制,SRIO模型假定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生产技术条件相同,由此造成较大误差;而且,这一路径无法反映各地区间的生产活动联系,具有一定局限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分析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中。MRIO模型是将多个地区、多个生产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考虑其中,弥补了SRIO模型的缺陷,使得测算结果更为精确,也能观测到隐含碳排放在地区和产业间的流动情况。肖雁飞等(2014)基于2002年和2007年的MRIO模型测算了中国八大区域间由产业转移而带来的“碳排放转移”效应。梁巧梅等(Liang et al.,2007)建立了中国能源需求以及碳排放的MRIO模型,发现中部地区的能源需求及碳排放占比最大,有必要注重提升中西部地区的能源使用效率。张永姣和王耀辉(2023)利用MRIO模型测算了黄河流域九个省区市间的隐含碳排放,并进一步测算碳转移情况和生态补偿额度。陈晖等(2020)根据MRIO模型方法,编制了2012年中国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并基于此测算了省际碳转移,分析碳公平性问题。
针对碳排放转移的测度,能源使用测算法缺乏经济主体间的联系,仅局限于直接碳排放,无法反映隐含碳排放的转移关系。生命周期评价法在应用上较为烦琐,且对数据的完整性要求较高,不适用于宏观层面的碳排放测算。投入产出分析法则可以反映地区和部门间的生产联系,测算地区间的隐含碳排放转移,同时对数据要求较简单,易于操作。因此,投入产出分析法是目前研究碳转移问题的主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