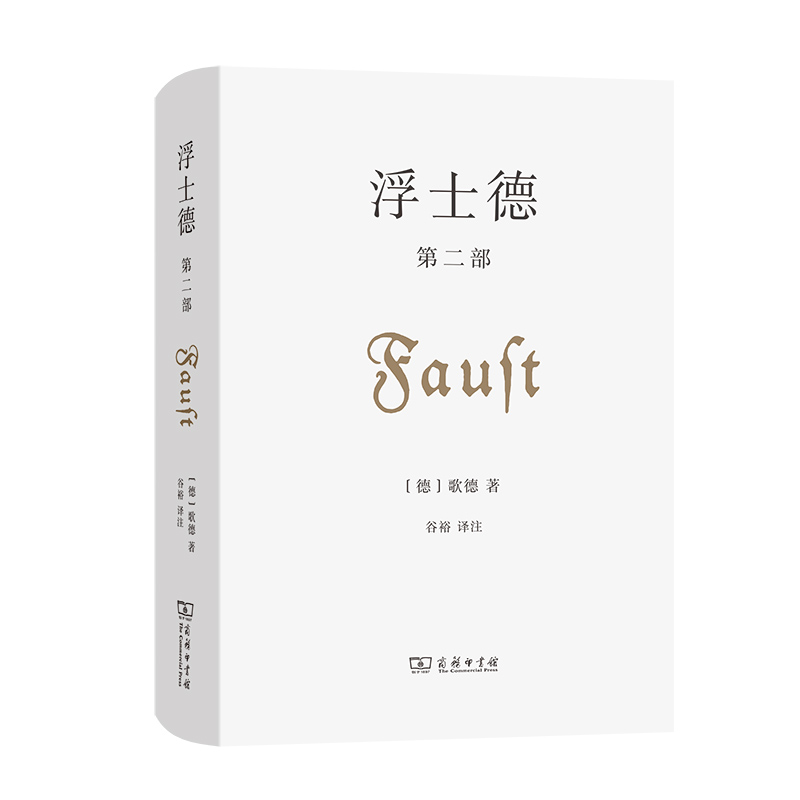关联图书
-
浮士德 第二部¥120.00
《浮士德》注释版,第八版序言节选
《浮士德 第二部》(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有朝一日,若所有的文学都从世上消失,人们或可以这部戏剧重建之。
(1804年1月28日,歌德致席勒)
歌德曾如此评论卡尔德隆的剧作《坚贞不屈的亲王》然而,但凡可以充分理由如此评价世界文学中某部作品的话,那恰恰非歌德自己的《浮士德》莫属。
早在童年时代,歌德就曾观看以浮士德博士为题材的木偶剧;在去世前几周,他对自己《浮士德》剧的终场进行了最后修订,这期间相隔近75年。歌德的《浮士德》满载丰富的文学形式,唯有禀赋卓著之人以其漫长的一生,方可赋予它如此卓越的语言力量、文学塑造力,以及近乎独一无二的变化的能量。在该多声部作品中,汇聚了不同声音的言说和歌唱,有莱比锡的大学生,有斯特拉斯堡和法兰克福的狂飙突进诗人,有魏玛的古典作家,有居住在圣母广场边的老人。歌德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创作时期,学习和掌握了丰富的文学手段,并将之尽数用于《浮士德》创作,使之成为展示作者创作才能的集大成之作。

吸收前人和外来的文学财富
所有艺术都建立在艺术积累的基础上,没有任何一部艺术作品仅归功于某一个人的天赋。在1824年12月17日致冯•米勒总理大臣的信中,歌德写道:“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成就”按理是属于作家的,“只有吸取他人财富化为己有,才会产生伟大作品。我不是也在(天堂序剧一场天主与梅菲斯特对话中)塑造梅非斯特时吸收了约伯的形象,且(在夜晚和格雷琴门前的街道两场中)吸取了莎士比亚的小调吗?”
《浮士德》吸取了从古代至歌德时代不计其数、多种语言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的作品,《约伯记》和《哈姆雷特》仅是其中两例。歌德并非采用一目了然、一一对应的方式吸收外来财富,而是通过引用、改写、影射、用典等方式,对之游戏式地进行了改造。因此说《浮士德》可以“重建”文学,意思还在于,它的文学形式是文学家们的集体财富,作品丰富的意涵正得益于从集体财富这一宝库中汲取的大量营养,包括辞书引用、句式、修辞,包括母题、比喻、象征、寓意,包括典型形象、场景模式、行为方式、舞台艺术。对此将在以下注释中以大量例子加以展示。
本序言无意对整部《浮士德》做一个概述,而只是提纲挈领指出几点特殊之处,为以下的注疏给出基调。故而就“吸取外来财富”一项,在此仅以诗歌格律和文体为例加以说明。前者是一切语言规则的基础,对于后者会稍作展开。
在喜剧中,诗歌的格律通常可以比较自由地转换,而在“严肃”剧中,格律通常是统一的(使用每个时代特有的形式)。比如就演员台词来讲,古希腊悲剧规定连贯使用双三音步抑扬格,16世纪的狂欢节剧使用双行押韵体,法国文艺复兴戏剧和德国巴洛克悲剧使用亚历山大体,莎土比亚的主要戏剧和德国古典时期戏剧使用五音步无韵体,在近现代,狂飙突进剧作家开始使用散文体,到19世纪已经全面普及。
然而在一部《浮士德》剧中,不仅使用了所有上述形式,而且还有更多格律和不同形式的诗节(有学者将之分为37组,并按出现频率绘制出图表)。此外,《浮士德•早期稿》中有个别部分使用了散文体,《浮士德•一》中至少阴郁的日子一场保留了这种散文体。当然在多样性方面可与之媲美的,尚有西班牙剧作家德•维加和卡尔德隆的作品,后有浪漫派的戏剧。
戏剧形式
《浮士德》吸收了丰富的诗歌形式,同时也吸收了丰富的戏剧形式。
歌德把自己创作的多部戏剧称为悲苦剧,单单把《浮士德》称为悲剧。还在1797年歌德重拾《浮士德》创作之际,他就表达过自己的疑虑,他担心“写一部真正的悲剧”,“这一尝试或许会毁了”他自己(1797年12月9日,致席勒)。继而在《浮士德》即将杀青时,他再次进一步表示:“我天生不是悲剧作家,因我天性随和;纯悲剧事件不会让我感兴趣,因它本质上必是不能和解的,而在这样一个平庸至极的世界,我觉得不和解简直是荒唐的。”(1831年10月31日致采尔特)
歌德称整部作品为一部“悲剧”,这其中包括天堂序剧和山涧一场。然而单是这一形而上的框架,无论人们如何理解,它都消除了剧作的“不可和解性”。若论在框架中发生的一切,虽然进取-迷茫的浮士德一次次失败,他在尘世游历的每一个驿站都导致灾难,但因此框架它们便绝非“纯-悲剧-事件”。人们习惯于把《浮士德》分解为诸如“学者悲剧”“格雷琴悲剧”“海伦悲剧”,或者如汉堡版将之分为“思想者悲剧、爱情悲剧、艺术家悲剧和统治者悲剧”,要知“真正的悲剧”并非如此由“个别悲剧”组成。
无论如何,对于歌德来讲,浮士德所遭遇的一切,他所造成的一切,或他在大世界经历的一切,已经具有足够的悲剧性,尽管他并未让戏剧结束于无可救药的毁灭,或让主人公陷入毫无希望的自我毁灭,而是把一切“提升”至山涧之上那个不可描述者的无限开放的天界。
歌德的《浮士德》全称《浮士德:一部悲剧》,副标题给出的文体形式成为某种预设的标签,从一开始就阻止了对框架内事件,在历史乐观主义-目的论意义上的理解。因此,断不可因循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解释传统来理解这部剧作,比如把它说成是有关个体或以浮士德为代表的人“类”日臻完善的教谕诗,或认为它是对——包括科学认知领域,技术-工业领域,令自然屈从人类或人类经济、社会、政治关系方面(无论人们怎样把这一过程说成是“辩证的”,无论人们认为这种预言具有怎样“乌托邦”特征)——有着明确目标的“客观”进步的赞美。
因这样的理解,显然忽视了作品中很多足以驳倒上述观点的反面表征,比如作品中有很多信号显示出不确定性,有很多指征表现出深度怀疑,此外还有大量对灾难的报告,对灭亡的预测,以及随处可见的有关末世将至的弦外之音——由此简直可以把《浮士德》称为一部末世之作。同时,这样的理解,也全然将悲剧概念的主要特征和必要保留条件置之不顾。《浮士德》接受史已充分证明,如此理解与某种入世的、追求完善的意识形态以及进步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然而虽称之为悲剧,剧作并未排除“有许多按经典分类规则当算作喜剧的场景”,或可算作悲喜剧的场景。剧中不少地方表现为严肃与搞笑、令人震惊又令人惬意的混合风格,不仅如此,可以说《浮士德》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学中多种文体、准文体、文学式样、塑造方式、戏剧传统的集合。它留有木偶剧和流动剧团演出的痕迹,在天堂序剧中借鉴了大型宗教剧模式,在夜一场加入中世纪复活节剧,在格雷琴剧中展示了当时代市民悲剧的特征,在“海伦”一幕中模拟了古希腊悲剧,重拾了酒神节的羊人剧,此外还有与巫魔滑稽剧、粗野闹剧、宗教剧、道德剧,与歌舞剧、假面联欢、假面游行、宫廷或酒神节庆典相对应的“文本形式”。
朗读文化
然而事实上,早在首演甚至出版前,《浮士德》剧就已广为流传:通过歌德自己公开朗读手稿的形式。对于剧本的传播这种形式如今已不多见。然而几十年之久,它都是《浮士德》传播的唯一方式(即便在作品出版和被搬上舞台后,歌德也终生保持了这一方式)。在大约在1797年创作的献词中,歌德写道:他们再听不到我将作的歌呤,/虽则开篇曾是唱给这些灵魂;/欢聚的友人早已是四散飘零,/可叹最初的应和已无影无踪!/ 我的歌将要面对陌生的观众……(行17及以下)
在小的朋友圈子中传播和接受文学作品,直到18世纪还相当流行,作家可口头-直接传播,听众是一个熟悉的圈子,可直接对作品进行“应答”。这样的形式逐渐被在无名读者中的文字传播、面对陌生观众的公演所取代。献词中哀怨的诗句无疑是对这一深刻作用于作品的、充满危机的过渡阶段的反思。
早在移居魏玛之前,歌德就开始朗读作品,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去世前不久。他曾在1813年这样说过:“莎士比亚要通过活的语言表现出来,朗读是最好的流传方式,这与表演不同,听众不会因表演的好坏分散注意力。最美妙和最纯粹的享受,是闭上眼睛,听人用自然的声音朗读而非朗诵莎士比亚的戏剧。”这样“我们会不知不觉获得生活中的真理”。
当然对于《浮士德》的作者,朗读还不仅仅只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同时可以检验行文是否合适,它可以要求、促进、塑造纸上文字所不能给予的“活的语言”。
歌德日记显示,在1832年1月2日至29日间,老年歌德最后一次全文朗读了他禁止在生前出版的《浮士德•二》,听众只有他自己的儿媳奥蒂莉。日记同时记录了本次朗读对修改音律所起的作用,如1月17日日记中写道“帮助修订了《浮士德》中的几处”,1月18日日记中称“改写了几处”。虽然歌德生前做的最后这番修订是由“内容”决定的,但毕竟内容自带形式,形式永不脱离内容。
歌德生前讲话一定是声情并茂,他的所有文字也便带有这样的特征,也就是说,在写下的文字中,一定包含活的语言(更何况有很多文字是他口授给书记员的)。因此可以说,在《浮士德》诗行表现出的不刻板的韵脚中,在富有魔力的音韵和生动的旋律中,朗读者歌德的声音依稀可辨。
阅读剧
《浮士德》是舞合剧,是朗读剧,但同时也是一部阅读剧。这并非说要把《浮士德》当作阅读剧来接受,而是指它同时具有阅读剧的特殊品质,或曰只有通过这种传达形式和接受方式,才能感知到其深意。比如在高山一场中,紧随梅菲斯特关于地壳运动、高山形成的故事之后,是一处重要的对圣经的影射,给出了火成说所包含的政治-革命寓意,这便是戏剧表演所无法传达的。
因此说剧中有很多地方,只有通过阅读才能理解到其深意。再比如所有舞台技术都无法呈现终场中,炽天使神父如何把有福童子接纳到自身之中,好让这些不谙世事的童子,用他的眼睛观看山涧;或者对于浮士德的不朽、裹缚他的丝絮被解开、从苍穹的霓裳中,/ 走出最初的青春力量等等,人们都只能通过想象去感知。
当然并非诸如此类不能在舞台上呈现的个别场景,决定了《浮士德》同时是一部阅读剧,而是更重要的是,整部戏剧需要人们启动思考,“用心”去领会。按照作者自己所讲明的意图,读者需要自己去补充完整,去“衔接前后关联”;为理解整部作品,人们必须认识到前后的呼应,把作品当作一部“前后相互映照的整体”来读;同时还要加入读者自己的处世和人生经验,甚至需要读者“敢于超越自己”。
也就是说,《浮士德》剧要求“接受者自身要有所贡献”。不间断的舞台演出、朗读时快速的语流,都无法给人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只有缓慢阅读、不断驻足、前后翻阅、深入思考的读者,才可能发现作品更多的内涵。如果说舞台演出和朗读(作为对演出台词的一种实践性解释)需要选择性地,也就是局限性地对某些角色和场景,针对个别词句乃至整部作品,给出固定的意义取向,那么阅读则可增进对这部丰富而自由的作品的多意性的认识,因为终究是这种多意性赋予了作品以张力、广度和深度。
本版本的《浮士德》只能提供一个阅读本,注释也只能把它当作一个读本来对待,这样就难免会偏离完整的、完全的文本实践,不得不又是用文字来解释文字。如有某些地方会对舞台演出有所启发,那么则希望这些地方会对导演、演员、舞台设计师或技术员有所帮助。但注释首先要唤醒的是读者自己对舞台的想象力。它们当启发读者,走出书本上的文字,开启想象力,去想象那个奇妙的自由的舞台。因为虽说《浮士德》是一部舞台剧、朗读剧、阅读剧,但它终究是为此一完全“不可想象”的舞台[读者想象力中的舞台]创作的。
“集体”创作
歌德自己曾说,“只有学习和借鉴外来财富才能产生伟大作品”,这并不局限于我们至此所探讨的艺术领域;如果人们认为,“若有朝一日文学从世上消失”,人们可以《浮士德》“重建”之,那么人们必须看到,这部文学大全并非只是产生于文学的文学。这种时髦的艺术领域的近亲繁殖并非歌德所求。以下表述说明了这一点:
我做了什么呢?我不过是对我所见所闻的种种进行收集和加工罢了。我的作品是由成千上万不同的个体所哺育的,他们之中贤愚不齐,老少兼备。所有人都纷纷来到我面前,向我吐露他们的思想,展示他们的才干,呈现他们的存在方式,我所做的仅是常常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我的作品本是一种集体创作,不过是冠以歌德之名罢了。
(歌德致弗里德里克•索莱,1832年2月17日)
这段谈话发生在歌德去世前不久,他刚刚在几周前完成了对《浮士德•二》的最后修订,并且把誉抄稿封存起来。为照顾客人,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在歌德毕生作品中,没有哪部比《浮士德》更符合这段表述。当时大家在圣母广场边歌德的家中谈论米拉波伯爵。就是那位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重要推动者,说他不过是天才地观察、收集和借鉴了他人的想法和理念,利用了已有的思想和思考并对之进行了大力宣传。时已82岁高龄的歌德发问道,米拉波自己又做了什么呢?他的工作归功于成百上千他人的生活方式、经验、观点和能力。他常常仅仅是收获了他人播下的种子。然后便是这句语出惊人的:“我的作品本是一种集体创作,不过是冠以歌德的名字罢了。”
为歌德之创作做出贡献的,大多是一些无名英雄,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行为方式、讲话方式反映到歌德这位伟大的人类观察者、形象塑造者的作品中。希腊人和犹太人参与了创作——希腊神话和犹太圣经奠定了《浮士德》的基础;除世界各地和各个时代的文学家外,还有无数其他人(在狭义或广义上)“共同撰写”了这部集体创作,他们有神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有政治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军事理论家,有工程师、技术员,有历史学家、语文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有建筑师、雕塑家;还有画家特别是素描画家,歌德或收藏有他们的原作或复制品,或通过他人描述得知他们的作品。很多作品都给予了他很大启发,为《浮士德》的语言和戏剧人物、动作、场景等提供了模式。
既然歌德认为这样的“集体”是作品的真正作者,那么本版则将在注释中,清楚注明作品中包含的大量此类细节,其目的是为让读者更好理解剧作,而非罗列各种证明。因就《浮士德》对外来财富的学习借鉴来讲,很多地方并非拿来就用或淡化出处,也并非因化用而使出处显得无关紧要,而是保留了可以辨认其出处的形式。
《浮士德》的创作,其孵化期和成文史贯穿了歌德漫长的一生,其主人公因此吸纳了各个时期广泛的经验(以致年迈的浮士德称:世事于我已足够熟悉),读者于是也跟随主人公经历广阔的时空。近代文学中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为读者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当然作品给读者开启的维度,要远多于它赋予剧中人物的。如在天堂序剧中,在众多后台人物中,首先登场的是不可见的约伯;在“尾声”一场中,浮士德的不朽是沿着教父奥涅金给出的复归说之路,向更广阔的空间和时代走去。因此可以说,戏在开场前就已上演,在歌德标上“剧终”后仍未结束。



- 《红色气质》序言2022-03-02
- 《浮士德•第二部》译者序2022-03-22
- 吕斯布鲁克及其《精神的婚恋》中的“迎接”的含义(节选)2013-01-04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