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图书
-
什么是科学(第二版)¥58.00
范瑞平评《什么是科学》︱为着求知本身的目的
2023-02-22作者:范瑞平刊发媒体:澎湃新闻浏览人数: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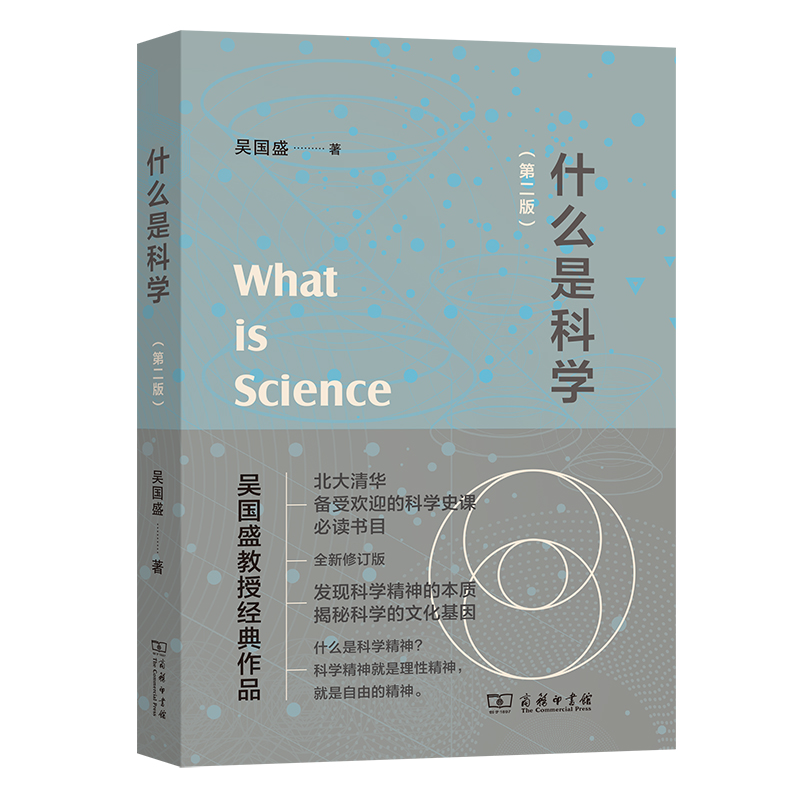
《什么是科学(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23年出版)
吴国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学》近期发行了第二版(以下简称吴著),第二版除了文字表达上做了小幅修订外,还增加了两个附录,一是对各种批评的回应,一是对本书主旨在科学哲学上的支持,值得读者留意。
本书主旨之一,是指出科学的真正鼻祖不是东方的实用技术,而是希腊的演绎科学(几何与哲学)。这一主旨让那些沉浸在李约瑟汇编的中国古代科技辉煌之中的人,实在感觉不爽。但不爽归不爽,事实终究无法否认。吴著以真正的文化自信和深入浅出的笔法,描绘出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的不同。好比说前者建了一所精致的房子,后者栽了一棵漂亮的树,它们各自精彩动人,很难说谁比谁更真实、更好,但确实大为不同。当后者长出甜美的水果时,你不能以为前者本来也能长出那样的水果。吴著就是告诉我们,那是一个误解,而且是一个于事无补的误解。
我们当然也想吃到甜美的水果,那就需要我们去认真看看那棵树,特别是它的底部。吴著表明,希腊的科学是演绎科学,它纯粹为“自身”而存在,没有功利目的、实用目的,这一特征同中华古典文明的旨趣适成对照(39页)。作者小心地表示这是希腊科学作为其学科存在的特征,意谓这种特征不必完全契合每位科学家的动机和行为。当然,科学的特征无法全然不受科学家的动机和行为的影响,而后者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形成和展现的。就古希腊城邦而言,那是自由成年男性的“公共”场合,女性无权参与这个场合,另有大批奴隶供养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因而,他们是贵族式的学者,既有闲暇保证又有兴趣来支撑着他们思考宇宙的奥秘、推断事物的原理,追求纯粹为“自身”而存在的“无用之学”。提及这一点,意在提示“无用之学”与“有用之学”之间具有复杂关系,但绝不能否认吴著所揭示的希腊价值观对产生这种科学的关键作用:纯粹的科学必须是为着求知本身的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目的而存在(40页)。这种知识目的论不能全部还原为经验心理学:希腊人区分知识与意见,后者因为带有个人心理成分未能经受演绎的洗礼而难以成就确定性或必然性。然而,价值论也无法完全脱离心理学而存在,因为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有兴趣的人。联系到兴趣,希腊科学的一大特征也可以粗略表述为:你是为发现和理解真理(而不是为名为利或为家人的福祉)这样的兴趣去做科学研究的。
古代中国的价值观大概是《尚书·洪范》所总结的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知识不在其中,我们不好硬塞进去。但无法否认,知识必定是追求五福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假设我们先不考虑五福之间的可能冲突)。这里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谁之五福?何种知识?举例来说,当今香港的优秀学生大体只选三个学科:医学、法律、商学。看着高考状元们在镜头前大讲“因为医生对社会有重要贡献”所以他们选择学医云云,我不免想到也许生理学、病理学以及有机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会对社会有更重要的长远贡献,为什么不选呢?其实,较之于整个社会的五福,状元们的主要动机首先是自己及其亲人的五福,这是人性所在,没有什么不好(因为首先考虑自己及其亲人的五福并不有损于其他人的五福),也没有什么不对(儒教文明本来就认可“差等之爱”)。但就何种知识而言,我实在怀疑,医学是否真是他们每个人的兴趣所在。医学在香港是一个高薪专业(内地医生无法不羡慕),“富”不成问题。但它也是一个天天要面对病人的高强度、超复杂、极艰苦的工作。如果你其实喜欢的是安静的实验室研究,那么天天为病人看病就难以给你带来相同的“康宁”,以至于会给你的“好德”“长寿”带来负面影响,即使对你的“善终”没有影响。同时,你的不快乐当然会影响到你的亲人。平衡下来,哪种选择更能增进五福呢?也许,如果你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基础学科的实验室研究工作,你还可能做出了不起的科学发现,增进你自己、你的亲人以及所有人的五福呢!
1992年我在从北京到休斯顿留学的班机上,遇到一位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的同学。他兴致勃勃地讲述自己不喜欢物理学,但为了容易拿到资助并且容易其后转向电脑专业,所以决定先报考物理学,等在美一年后再转电脑专业。问他喜欢电脑专业吗?他说不喜欢,但为了好找工作能赚钱一定要学。听说我学哲学,他立即关切地说:“你以后很难找到工作!” 本人那时年轻气盛,立马怼回去:“我要是从哲学转了去学电脑,你岂不是多了一个找工作的竞争对手?”的确,当年学人文的不少转行去搞了电脑、会计,也不知现在混得如何。而那些凭兴趣继续学习哲学的,现在全是大学教授。国人做学问很讲“有用性”、看前途。家长们总爱询问哪个专业最有发展前景、最多机会,其实这问题无人能答,因为它受很多因素包括未来科学发现的影响,而科学发现本身是无法预测的。过去我们太穷,一不留神就要忍饥挨饿,陷父母于“不义”,讲“实用”可以理解。但现代社会的人们大体已衣食无忧,基本福利能让人人吃上饱饭。我看吴著的启发是,要想搞好科学研究,我们实在需要转向希腊人“为着求知本身的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目的”去搞科学。只有按自己的兴趣选择学科来做研究,才有可能取得科学成就,并有可能增进“五福”。
这一问题还关乎自由。吴著表明,希腊人看重的真知识是关于事物的本性(nature)、本质(essence)、具有“永恒”要素的知识;只有认识这种知识,你才能达到自由——即顺应和实现自己的本性、本质或永恒的东西(也即所谓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希腊人认为只有严格的演绎推理才能保证这种知识,所以必须把演绎逻辑贯彻到你的研究之中,吴著将此称为“理性自由”(126页)。事实上,这种自由就是现代社会所讲的进取性自由或理想自由。中华古人并非没有理想自由,而是具有一种不同于古希腊的理想自由。如果把希腊理想自由称作追求演绎推理的理性自由,那么中华理想自由可以称作追求类比推理的和谐自由,前者重视物体的运动、因果关系,以及时间上的历时性(diachronicity)特征,而后者则关注人物的心态、相互感应,以及时间上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特征。
中华古人当然不会否认一般的因果观念,也不会拒斥时间的流逝性(“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前辈在我先,晚辈在我后),但他们的着意之处不在这些方面。当亚里士多德通过运动与记数来理解时间以及苦思冥想他的四因说之时,孔子的追随者们探索的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易经·系辞传》)的一套共时感应原理,而且成为儒道两家的共同兴致:“同类相应”“同气相动”“天人感应”(《淮南子》)。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 G .Jung, 1875-1961)把这套原理称作共时性原理(以别于科学的因果性、历时性原理):有同样或类似意义的两件事情同时出现,但它们之间没有因果联系,也不只是碰巧同时出现。在他看来,这正是“道”这个概念的底蕴:没有因果关系的有意义的巧合能够同时出现,是因为它们具有内在的“道”之联系。他还认为《易经》的奥秘可能就是利用这一原理来揭示事物之间以及与人的心灵之间的这种非因果性的深层联系结构。显然,这一原理所涉及的逻辑不是演绎推理,而是类比推理。我们在《易经》(包括《易传》)以及中医经典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类比论述。
当然,不是所有学者都会赞同对中华文化的这种理想自由的表达。我认为,这种理想自由的追求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它不把人看作因果决定序列中的一环,而是看作自发动作、相互感应、和谐自然的存在;这里的人不是被操控、被决定的物体,而是自在自由的精神。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理想自由的观念,并未取得进一步研究的实际成果。与此相关的汉代谶纬之学,胡编滥造,异想天开,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相反,正如吴著表明,希腊的演绎推理与现代实验研究相结合,已经获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上天入地,求精显微,几乎全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事实一再表明,按照后一原理去做认真诚实的科学研究,很大可能是会有成就的,区别不过是成就大小而已。但按照前一原理去探索,就很难说了。因此,社会把公共资源用在前者而不是后者,是有理由的。
但这里还涉及一个不同的自由概念。吴著认为,现代科学受到基督教意志自由观念的影响,开始追求“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129页)。求力意志使得西方人不服从原来的理性观念,摆脱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自然哲学,重建一个以动力因为主要因果模式的自然知识体系(136页),从而利用实验科学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从理性自由走向意志自由(138页)。作为一部科学史、科学哲学的专著,作者非常小心地不去碰任何政治哲学的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无可否认的是,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对两种自由做了最清楚的概念区分:一种是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即上文所称的理想自由,它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应该用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和行动的理想、理性、真正自我或高级本性?”这种自由是对理想的追求。另一个自由概念是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也可称为底线自由,它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允许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涉个人?”这种自由是对个人不受政府强制的底线要求。伯林认为,如果允许政府推行一种理想自由来限制个人的底线自由的话,那将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社会,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政府就能以追求你的“真正”自我的名义来无视你的实际愿望,以维护真理或追求人的“真正”目标——无论是幸福、安全、义务、智慧还是正义——的名义来恐吓、压迫、拷问你,因为那才是你没有认识到的、你的“真正”自由所在。历史已经表明,这种社会是可怕的、灾难性的。在社会生活(包括科学研究)中势必需要个人的底线自由: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理想自由观念(如古希腊的演绎自由、古中华的感应自由),无论它们是被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持有,它们都应该得到宽容,不应该受到镇压,只要其理想自由追求不损害别人的自由追求即可。
1992年当我赴休斯顿留学时,非常惊奇地发现,这个紧邻航天发射中心、现代科技十分发达的城市中,竟然还有人相信大地是平的,他们还有个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Flat Earth Research Society,至今存在),自筹经费进行相关的实验研究,召开学术会议,发行自己的宣传品、音乐、批判“错误的”地圆说。认真考虑一下,如果政府出资支持这种研究,那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我们确实已有强大的理由和证据表明地平说是错误的,不应该把纳税人的钱花在这上面。另一方面,从底线自由出发,如果政府强迫取缔这个学会,禁止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来进行研究,那也是错误的。没准儿他们的研究歪打正着,也能做出什么有趣的发现呢。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具有追求自己的理想自由的自由——尽管他们的理想自由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愚蠢的,即社会应该允许他们享有人人都需要的底线自由。我想,这或许也是吴著既呼吁“改造我们的文化土壤,让科学能够在中华文化中生根发芽”,又强调我们的传统中有发达的“博物学(自然志)”传统,值得科技史重视的深意所在(273页)。
原载于《澎湃新闻》2023年2月22日
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教授范瑞平
关键词阅读
- 科学“树”与科学“河”2023-02-15
- 李宏图评《创造现代世界》:从“启蒙理性”到“人的科学”2022-07-12
- 笺注的首要目的是回到作者本意——评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2022-05-21
- 朱玉麒:刘衍淮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2021-09-10
- 吕海春:《中华科学技术大词典》——推动两岸“科技术语共同体”建设2020-08-03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