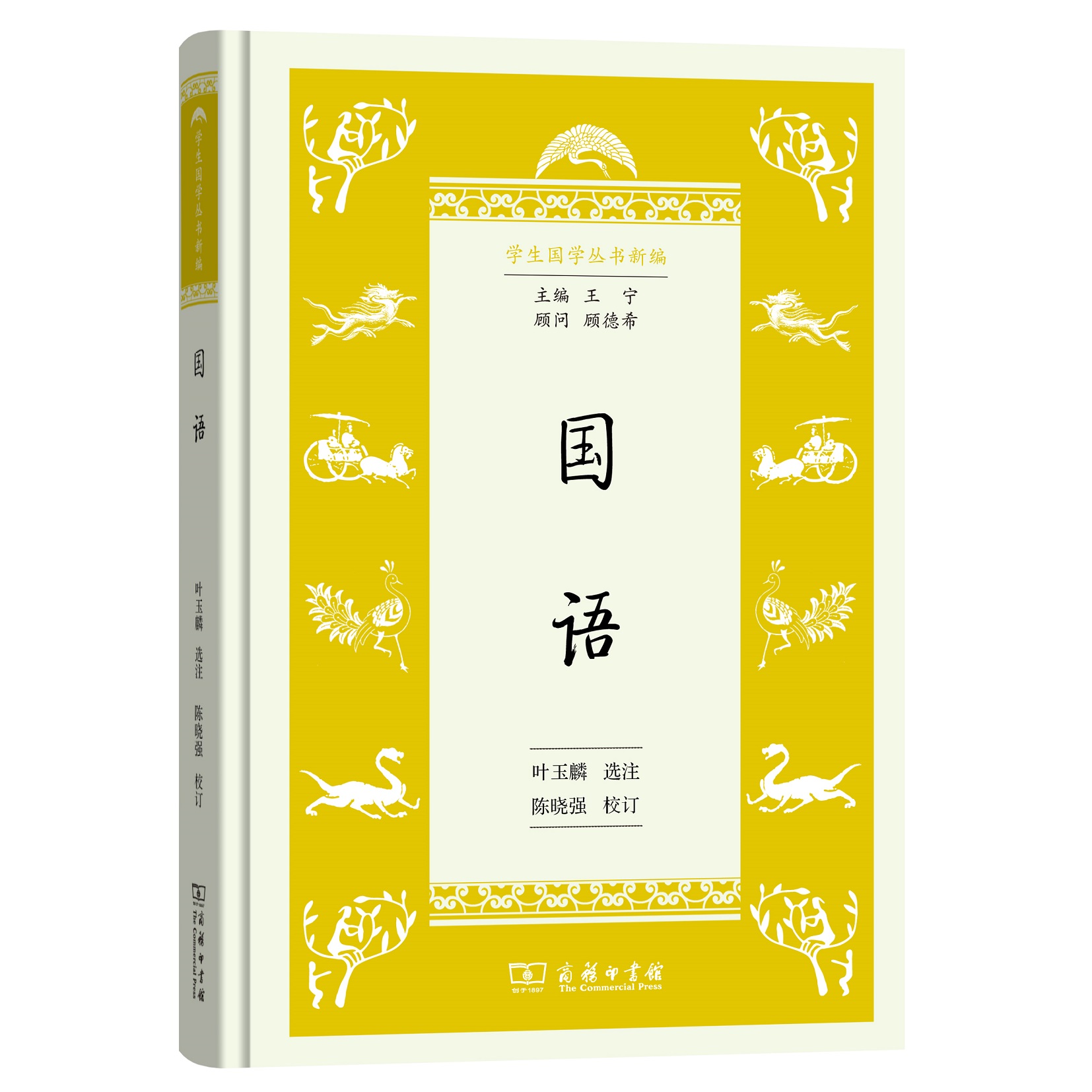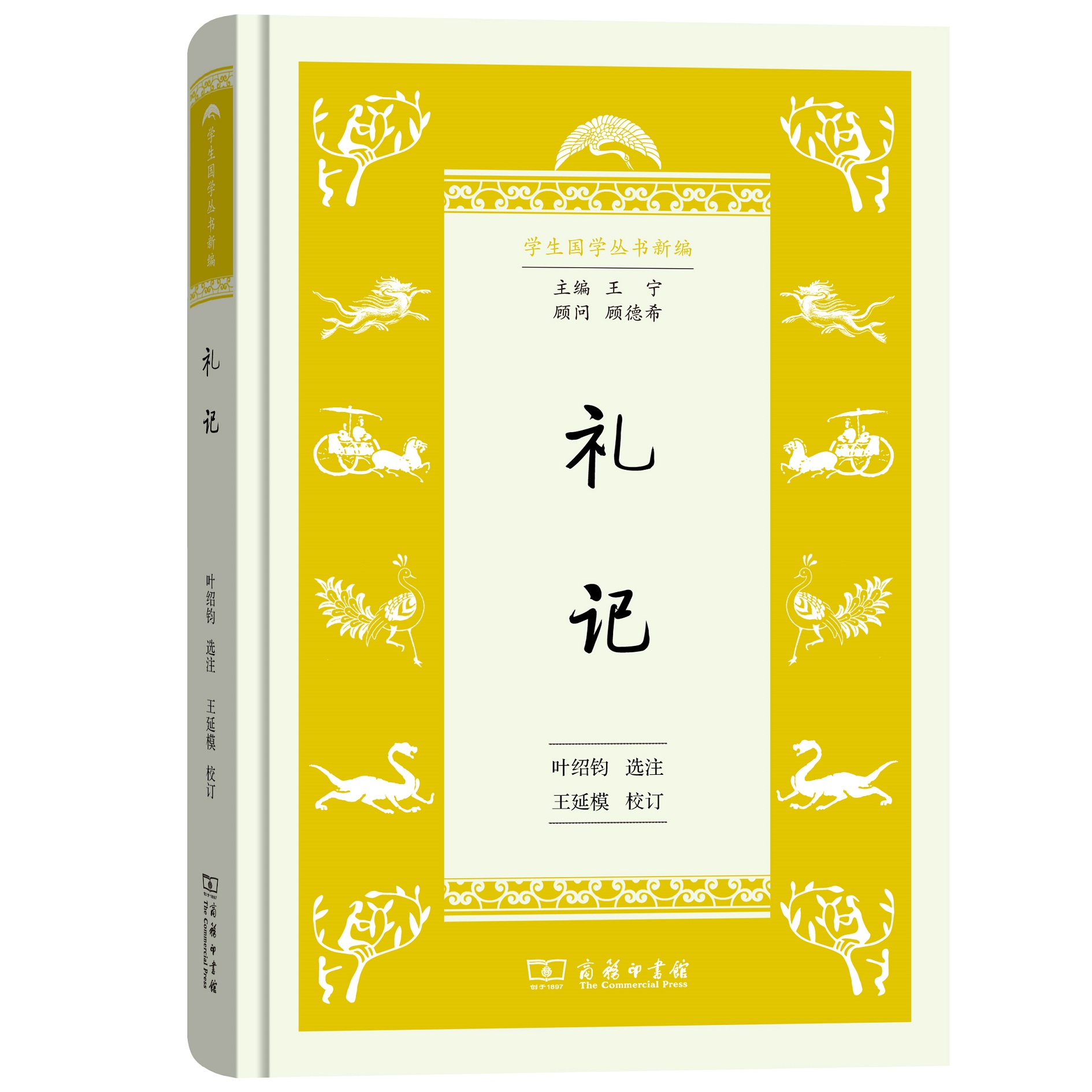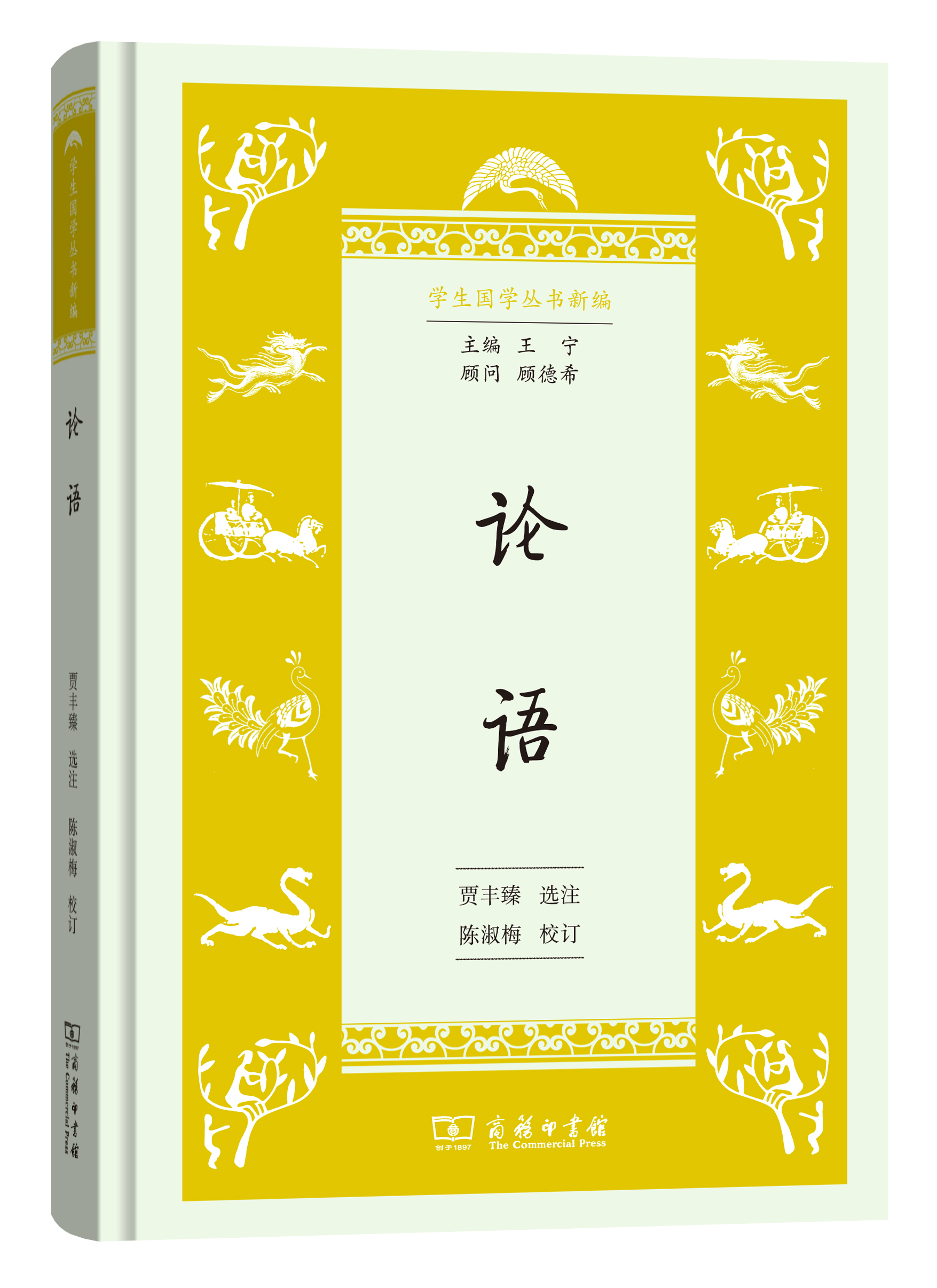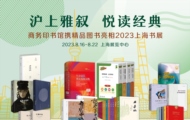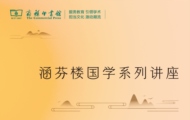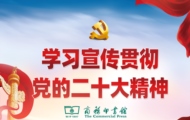(换照片)“礼让的力量”讲座现场
9月2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国学系列讲座第23讲“礼让的力量”在涵芬楼书店·商务印书馆历史陈列馆举行。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永定分校初中语文教研组长周伟川做主题讲座分享,近百位读者现场参加活动。

(换照片)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永定分校初中语文教研组长周伟川
《国语》虽称“国别史”,其实特色不在记史,也不在国别,而在“语”。这本书的特征,是以事为辅、以语为本,重点记载了王侯卿士大夫对治国理政问题的见解、议论。《国语·楚语》记载了大夫申叔时谈及教育的话:“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这说明“语”是楚国王公贵族子弟需要学习的文献典籍之一,其地位与“春秋”“诗”等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性。楚国有“语”,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也有各自的“语”,于是就有“周语”“鲁语”“齐语”等。战国时期,熟悉各国史料的史官,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遂成《国语》。
关于《国语》的性质,汉代学者普遍认为它是“《春秋》外传”。所谓“外传”,是相对于“内传”(即《左传》)而言的。《国语》所记载的历史范围,最早为周穆王伐犬戎,最晚为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国语》记载的历史时期与《左传》大致相同,所载历史事件又与《左传》密切相关。《左传》以解经为主,故称“《春秋》内传”;而《国语》则“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韦昭《国语解叙》)。这说明,《国语》与《左传》区别很大。《国语》的内容主要是一些政治人物分散的言论,其所涉及的历史事件,相互间缺乏历史演进的线性关联,这与《春秋》的编年记事完全不同。经历代学者的辩驳,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儒家经学的尊崇地位被破除,今人已不再相信所谓“内传”“外传”的说法,《国语》已经被看作一部独立的重要历史文献。
《国语》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个部分。八“语”所占比例不一,侧重点也不同。《晋语》九卷,较完整地记载了武公并晋、骊姬之乱、文公称霸一直到“三家分晋”的政治史。《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敬王时的部分大事。《鲁语》二卷,主要记鲁国上层社会一些人物的言行。《楚语》二卷,主要记灵王、昭王时的事件。《越语》二卷,记勾践灭吴。《齐语》一卷,记管仲辅桓公称霸。《吴语》一卷,记夫差伐越和吴国灭亡。《郑语》一卷,记事最少,仅记周太史论西周末年天下大势。
由于史料来源不同,《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周语》《鲁语》近儒家;《齐语》记管仲霸术,近法家;《越语》记范蠡顺应天道、地道、人道,近道家;《晋语》部分言论讲机变权谋,近纵横家。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学派的思想差不多都可从《国语》中找到痕迹。但从《国语》编者对史料的取舍和事件的评判看,民本思想是其主要倾向。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出现及推广,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引发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大动荡,形成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社会剧变的严酷现实,使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民”的力量关乎天下兴亡,这导致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由“天道”向“人道”的转变。在《国语》中,尽管还可看到“天”“神”的存在,但这里的“天意”因民意而定,民本思想才是其实质内容。《国语》的民本思想倾向,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基本思想的反映。
《国语》是一部有独立思想价值的史学名著。三国时代的韦昭在《国语解叙》中,称誉《国语》作者“明识高远”,采辑“邦国成败、嘉言善语”以为《国语》,点明了《国语》的精华所在。例如《周语》,记穆王不修德政、炫耀兵力,结果失去周边少数民族的归附;记厉王监谤,结果被人民流放:这些是失败的教训。而《齐语》记齐桓公重用贤才,征伐强暴,扶助弱小,一匡天下,则是成功的经验。《国语》充分发挥了史书“以史为鉴”的功能,其中的“嘉言善语”,堪称珍贵的历史智慧,在今天仍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国语》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它将记言与记事紧密结合,丰富了先秦散文的叙事方式。对过程曲折、头绪纷繁的事件,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叙述。例如《晋语》讲“骊姬之乱”,时间跨度长、涉及人物多,但作者游刃有余地组织材料,将这一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具体、清晰地展现出来,读之使人惊心动魄。《国语》的文风虽然并不统一,但亦可称多姿多彩。朱彝尊的《经义考》中引陶望龄的说法:“《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鲁》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这说明《国语》异彩纷呈的文笔,对后世散文确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人怎样读《国语》?这是初学者很关心的问题。
叶玉麟先生在这个选本“绪言”中有八个字说得好。他指出,初读者要“究观终始,抉择幽眇”,即初读者要大体弄清每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并注意提取其中精深微妙的内涵。
例如《鲁语》“季文子相宣成”,是个典型的小故事,说的是季文子在鲁宣公、鲁成公两朝为“相”,可是他“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这让一位“官二代”种孙它看不下去了,就劝说季文子,这遭到季文子的严肃反驳和批评。种孙它不服,回家把经过告诉父亲。他父亲却立即把他拘起来,关了七天。种孙它深刻自省,从此也“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了。季文子认为种孙它“过而能改”,就举荐他当“上大夫”。
这个故事值得提取的“幽眇”就很不少。季文子反驳种孙它的那些话就颇耐深思,如“人之父兄食粗衣恶,而我美妾与马,无乃非相人乎”,如“吾闻以德荣为国华,不闻以妾与马”,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实在值得今天很多人反复寻味。又如,“官二代”种孙它的“家风”可谓极严。他父亲认为他错误严重,就关他七天禁闭,令其反思。看来鲁国“精英”阶层确乎有严格家教。再是季文子两朝为相,受特殊信任,那么他对鲁国的忠心表现在哪儿?除“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的勤俭之外,在观察人、任用人方面,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也颇不少啊。
又例如上文的姊妹篇“莒太子仆弑纪公”,记述鲁太史里革冒杀头之罪,更改了国君的诏书,坚决惩处弑父的莒太子,为的是不使国君蒙上恶名。里革这种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的精神,真可谓坚守道义的典范。鲁国是小国,而且国君的毛病不少,例如因贪图宝玉而下达优待莒太子的诏书,但鲁国在春秋之际能受到尊重,不能说与其“精英”阶层尊贤尚义无关。
再例如《郑语》中“桓公为司徒”一篇,这是《国语》中少见的长文。故事很简单,全文记述的只是史伯回答郑伯友“何所可以逃死”的追问,而其“幽眇”恰在史伯对这个问题的议论中。史伯对当时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及民风,如数家珍,在那文献资料匮乏的时代,史伯具有何等惊人的眼界啊!而更精彩的是,他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和”是指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同”是指无差别性的单一事物,如果此事物不与彼事物相“和”,就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来。史伯认为,西周所以行将灭亡,原因是周王“去和而取同”,即排斥直言进谏者而宠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史伯大概是第一个区别“和”与“同”概念的人。他认为不同的事物互相结合才能产生百物,如果同上加同,不仅不能产生新事物,而且世间的一切也就变得平淡无味,没有生气了。史伯是西周末年人,他的话无疑是见诸文献最早的朴素的辩证观点。经过这番“抉择幽眇”,我们不是认识了一位比老子、孔子还早二百多年的杰出思想家吗!
类似这样值得“抉择幽眇”的精彩故事和议论还有很多。如“穆王将征犬戎”“厉王虐国人谤王”“桓公欲从事于诸侯”“范文子暮退于朝”“司马侯举羊舌肸”“叔向贺贫”“梗阳人有狱”“屈建去芰”“夫差许越伐齐”“勾践用文种”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国语》中的深刻人文内涵,凝聚在许多名言警句中,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忧德不忧贫”等,言简意丰,应用至今;稍长一点的名句如“君子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子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焉”“人之有学也,犹木之有枝叶也。木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之学乎”“哀无人,不哀无贿;哀无德,不哀无宠;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天之所弃,必骤近其小喜,而远其大忧”等,这样的名言警句几乎在在皆是,都值得反复玩味。
读《国语》,如能静下心来,借助注释“究观终始”,然后反复诵读,深加品味,那么“抉择幽眇”的乐趣便会油然而生。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