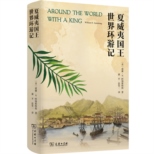关联图书
-
夏威夷国王世界环游记¥68.00
透视WASP的世界观——读《夏威夷国王世界环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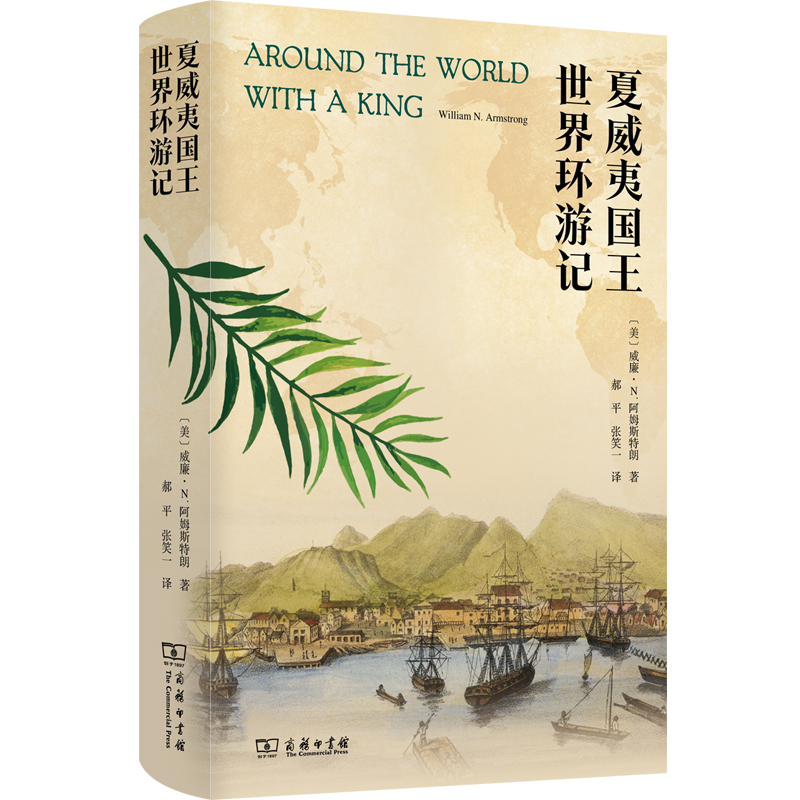
《夏威夷国王世界环游记》(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公元1881年,清光绪七年,当时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爱新觉罗·载湉刚满10岁,正在毓庆宫里读书,学习魏源等人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而在遥远的夏威夷檀香山,另一位15岁的中国少年正在当地的伊奥拉尼书院接受西式教育,学习英语、数学和西方历史等课程。这位少年便是孙中山,30年后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当蝴蝶的翅膀在太平洋上开始挥动之际,那里有一位历史人物与这两位中国少年都产生了微弱的连接。他就是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Kalakaua,1836—1891年)。卡拉卡瓦在这一年到访中国,希望到北京会见光绪皇帝而未能成功。但从光绪帝批复总理衙门的奏折上可以看到,他有可能了解卡拉卡瓦的访问。到了第二年7月,卡拉卡瓦在檀香山的圣安德鲁大教堂为伊奥拉尼书院毕业生孙中山颁发了英文语法奖。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当时都没有想到,在他们眼中的“番鬼”国王治下,将会培养出推翻他们统治的人物。而卡拉卡瓦的想象力和行动力不止于在夏威夷岛上支持西式教育。他在这一年做出了惊人的壮举——从他的夏威夷王国乘坐汽船出发,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环游世界的君主。
1904年,曾任夏威夷王国司法部长的美国人威廉·N.阿姆斯特朗(William N. Armstrong)出版了他陪同卡拉卡瓦国王进行此次环球旅行的回忆录。2022年,此书经郝平教授和张笑一教授翻译成准确而流畅的中文,并由安乐哲教授撰写了精彩的序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25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英文原著,这一英文版附上了郝平教授和张笑一教授精心编写的众多注释,令中文读者更能理解此书所具有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笔者看完全书后,感到这本记录140余年前夏威夷国王环球旅行的著作仍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对于理解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局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不揣冒昧,在此记上几笔。
作为历史叙事主体的阿姆斯特朗
首先需要提醒中文读者注意的是,此书的英文原名并非《夏威夷 国王世界环游记》,而是“Around the World with a King”(直译“与一位国王环游世界”)。当然,中文译者的处理简洁明了,突出了书的主题,完全值得肯定。不过,中文书名容易使读者认为,本书是以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的视角写作的。其实,卡拉卡瓦并不是历史叙事的主体。据夏威夷历史学者格伦·格兰特(Glen Grant)为此书撰写的导言介绍,卡拉卡瓦自己对周游世界的记述是他的信件《皇家游客——卡拉卡瓦在东京到伦敦段旅途的家书》。“with a king”意味着卡拉卡瓦国王只是相伴而行之人(虽然他是环游的主导者),而记述者威廉·N.阿姆斯特朗才是这一历史叙事的主体。而且,在卡拉卡瓦一行人访问完葡萄牙之后,他和其余随从去了西班牙,之后前往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最后从利物浦前往纽约。阿姆斯特朗被留下来处理夏威夷与葡萄牙的双边协议,没有随行,最后自己去纽约与卡拉卡瓦等人会合。因此,卡拉卡瓦这一段在西班牙等地的行程在书中没有得到反映,足见阿姆斯特朗是根据自己的旅行经历和观察来进行写作的。这一点对于理解此书的视角和主旨至关重要。
威廉·N.阿姆斯特朗于1835年出生在夏威夷茂宜岛拉海纳。父母都是美国新教传教士,1831年来到夏威夷岛传教。1849年,他进入酋长子女学校学习,同学中有后来的国王卡拉卡瓦和国王的管家查尔斯·H.贾德上校。1859年,阿姆斯特朗从耶鲁毕业,在纽约当过律师,后来又去了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直到1880年受卡拉卡瓦国王邀请入职夏威夷王国内阁出任司法部长。1881年1月,卡拉卡瓦国王任命他为国务大臣和移民部门皇室长官,陪同自己一起周游世界:
夏威夷国王在之后的十个月 内完成了环游世界的使命,成为众多国家王室或官员的座上宾,包括日本天皇,中国大臣李鸿章,英属香港总督,暹罗国国王,英属新加坡、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与缅甸的长官或专员,印度总督府,埃及总督,意大利国王,罗马教皇,英国女王,比利时国王,德意志帝国威廉皇帝王室,奥匈帝国官员(皇帝缺席),法兰西共和国官员,西班牙王室官员(摄政王缺席),葡萄牙国王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受到以上国家国礼相待。
由于环游世界肯定会耗费巨大,所以,卡拉卡瓦国王只带了阿姆斯特朗、查尔斯·H.贾德和曾有德国男爵头衔的男仆罗伯特三个人。据阿姆斯特朗介绍,卡拉卡瓦环游世界的目的有三个:(1)躲避当时正在流行的天花疫情。此前,由于欧洲人的到来而使麻疹、天花、伤寒、梅毒和麻风病在夏威夷流行,夏威夷土著人口锐减。(2)为了扭转夏威夷当时人口日渐减少的局面,想引入外国移民填补人口空缺,并通过外国移民来修复本土人的体魄。(3)满足了解世界的好奇心,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来造福夏威夷民众。尽管卡拉卡瓦自己在旅行中也留下日记和书信,但阿姆斯特朗撰写的这部著作是惟一一部关于此次环球之旅的翔实记录。格伦·格兰特与安乐哲都认为,阿姆斯特朗在此书中的叙事并不公正和中立,而是充满了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政治偏见。而笔者感兴趣的恰恰是这一环球旅行的记述者阿姆斯特朗。他的历史叙事为19世纪后期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时代记录。
一个19世纪WASP眼中的世界
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缩写为“WASP”)这一术语起源于20世纪前期。1964年,社会学家迪比·巴泽尔(E. Digby Baltzell)所著《新教当权者:美国的贵族和社会等级》(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Aristocracy & Caste in America)一书使其广泛流行。它描述的是殖民时代来自英国和西北欧的白人新教徒后裔,后来逐渐占据美国的上流社会,成为精英阶层,并长期代表美国社会的主流观念。这一术语虽然在20世纪中期才开始流行,但这一群体的形成和鼎盛时期却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阿姆斯特朗笔下时常出现的“盎格鲁—撒克逊式政府”“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制度”“国王治下最有力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占据统治地位的白人”“基督教世界”“美国的新教徒”“传教士”“高级文明”等词汇无不显示出他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WASP观念。他对此也毫不讳言:“我生为夏威夷子民,但却是传承美国传统的美国人。”
首先,对于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和夏威夷土著居民,阿姆斯特朗从头至尾都表露出一种鄙夷和轻视的态度。尽管阿姆斯特朗出生在夏威夷,少年时代是卡拉卡瓦的同学和能够一起玩潜水取硬币游戏的伙伴,当时还被卡拉卡瓦任命为司法部长,并受到卡拉卡瓦的充分信任而一同进行环球旅行,但他对夏威夷王国的君民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他认为,夏威夷王国在世界上“无足轻重”,国王和他的子民还是“未经启蒙的异教徒”,“离文明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他讥讽卡拉卡瓦“那波利尼西亚式的、有些迷信的大脑”,还托前任国王之口,指责夏威夷土著居民“没有出息、生性懒惰、缺乏能力”。这些都基于他的白人优越主义和种族歧视观念。因此,他会这样描述卡拉卡瓦抵达旧金山时的情景:
国王在国内时,是个慷慨大方的主人,曾经邀请许多旧金山居民,在摆放着赏心悦目的热带藤蔓、鲜花和植物的地方共进早餐和晚餐,因此他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 他是个“黑人”,肤色比一般波利尼西亚人要深,一些面部特征也显现出些许黑人血统,但是这些(旧金山)市民,无论男女都很“善良”,即使心怀厌恶也都忍着,能够应付这种场面,热情友好地把黑的说成是白的。
而夏威夷能够在文明发展上取得进步,全赖美国传教士和当地白人的推动作用:
国王已经在他自己的朝廷建立起文明的礼节。他的国家的文明程度已经得到了所有国家的认可,而他自己也可说是世界上王族中合格的一员了。而这是和美国传教士以及其盟友的努力分不开的,是他们创造了政府机构的框架,也是他们将法制的重任交到智慧诚实的白人手上……
其次,对于亚洲和非洲地区,他主要以学习西方文明的程度来对他们进行评判。“大洋洲”号从旧金山驶往日本,途中正逢乔治·华盛顿的诞辰纪念日(2月22日),船上的各国人都纪念华盛顿。阿姆斯特朗借此评论说:
当华盛顿在美洲丛林视察未来美国各州的所在地时,日本已然拥有了悠久的文明;而日本人重建本国古老的政治体系,却需要阅读教授美国治国原则的书籍,从中寻找金玉良言,只见每页书上都写满了华盛顿的名字。
他对日本近代政治家的肯定是基于他们学习西方的议会制:
基督教世界把这些(日本)人视为异教徒,但是根据世俗的标准,他们完全称得上政治家。……这几位日本政治家,西乡隆盛、伊藤博文、井上馨、大久保利通、胜海舟,却是在天皇的支持下,把议会制这样的现代政府结构,搭建在独裁封建制度那个狭隘而古老的基础上。
当时的中国人很难理解美国的联邦制度。在李鸿章为卡拉卡瓦举办的晚宴上,李鸿章的儿子向阿姆斯特朗直言,美国的联邦制度既混乱又危险。而阿姆斯特朗也对杀人如麻的李鸿章心生厌恶。总体而言,阿姆斯特朗认为,当时的日本和中国都正在开展国家重建(明治维新、洋务运动),向欧美学习,未来会具有相当的工业实力和经济水平。日本欧化的速度明显快于中国。与此同时,香港和新加坡不仅仅是亚洲交通枢纽和大型贸易港,还是“将西方文明之光播撒到远东”“展现法制和秩序优越性”的“传教站”。
在阿姆斯特朗眼中,与日本和中国相比,暹罗、缅甸、印度、西亚和埃及等地的民众更加沉溺于各自的传统宗教,显得更为落后。虽然暹罗国王和埃及总督的西方化程度都很高,但那里的民众不是“不知节俭,懒懒散散”,就是“过着如梦如醉、不可思议的生活”。例如,他这样记述在曼谷的见闻:
我们看到佛教寺庙密密麻麻,总共超过500座,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民众不求上进,在那里对佛陀顶礼膜拜,那是当地的主业。他们一边咀嚼槟榔,一边毫无变化、永无休止地重复“佛陀”一词,这种祷告方式,十分适合这帮懒人,根据这种信仰,只要无休止地重复“佛陀”,他们就能从罪恶之海中探出头来!
同时,各种宗教信徒之间不能互相理解,甚至彼此仇视。在缅甸到加尔各答的蒸汽船上,他看到一位穆斯林在做祷告,动作“优雅得体,从容不迫”,但其余那些中国人、印度教徒和马来人全部“无动于衷”。而对于英国女王的诞辰纪念日,“整个亚洲都知道”。这给了欧洲殖民者(尤其是英国殖民者)对广大亚非地区分而治之的机会。这一点得到了英国驻孟加拉邦部长麦考利的证实。阿姆斯特朗询问麦考利,五万名英国士兵如何能管理两亿五千万印度民众。麦考利回答他说:“因为他们内部意见不合;如果他们能够达成共识,我们的统治就会立刻成为历史。”
再次,在欧洲访问时,阿姆斯特朗充分观摩了欧洲列强各自的优势和它们之间的明争暗斗。此时的欧洲,除了法国是共和国外,其余大部分国家和亚非地区一样都是君主体制,但经过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后,社会面貌却和东方社会大不一样。他们亲身领略了伦敦和温莎的奢华场所,德国高水平的战争训练和克虏伯军工厂,维也纳的皇家歌剧表演,法国在外交礼节上的讲究与傲慢,葡萄牙的往日荣耀和如今的虚张声势,意大利酒店的漫天要价,罗马教皇刻有精美壁画的房间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显赫的宅邸。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殖民掠夺、贫富悬殊和列强之间此起彼伏的战争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阿姆斯特朗在参观英国议会时对当时的大英帝国做出了这样的评论:
虚弱或强壮,光荣或耻辱,大英帝国表现出人类所有的美德与罪恶。它侵占自己无权管辖的土地,推翻实力不够强大的政府,炮轰毫无防御之力的城市,残害妇女与儿童,轻视并背弃许多群体的权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在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法律与秩序,以及代表正义的明智的政府,它还在世界上与所有国家开通了安全的贸易……
伦敦既是当时西方世界的文明中心,又是罪恶之都。书中数次提到英国社会深受“金钱至上论”的“毒害”,大量赤贫阶层的人们生活凄惨,绝望无助。同时,皇室、贵族和资产阶级在每日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也深感精神上的空虚。在英国皇室成员举办的聚会场合,谈话的内容多半是些“愉快的流言蜚语”。阿姆斯特朗一行人在伦敦待了十六天,却从头到尾没有听到英国那些高贵人物发表什么高尚的思想。陪同阿姆斯特朗的英国贵族女子告诉他当时英国人内心的想法:“生活是无聊的(life was a great bore),无论对贵族还是平民都一样,不过是追逐浮华和影子而已。”
卡拉卡瓦到比利时后,兴致勃勃地前往滑铁卢战场旧址参观。他问阿姆斯特朗,为什么伟大的国家要打仗,而不是用调停解决问题。阿姆斯特朗当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在从美国返回夏威夷的海上,阿姆斯特朗梳理旅行所得,他进一步的观感是:
英国人鄙视其他所有国家,其中包括法国和德国。法国人又鄙夷英国、德国、美国。每个国家的文献中都充满了对其他国家不真实的记述和不公正的评价。所有的基督教国家又认为中国人、日本人和东印度群岛人是异教徒,没有高尚的品质,而且根据基督教的教义,这些人在道德上和智力上都无法取得进步,尽管他们占到世界上人口的三分之二。
最后,阿姆斯特朗几乎完全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看待世界和考虑问题。可以说,他自觉充当了美国政府在夏威夷王国的代理人。他高度认同美国的教育、文化和民主政治。他在维也纳见到耶鲁大学的两位外交官同学时会“一下子变成老伊莱(Old Eli,耶鲁大学的捐助人叫伊莱胡·耶鲁)的男孩儿”,一起在酒店房间内高唱《我们在耶鲁的生活》。相比之下,他觉得“夏威夷人才刚刚脱离野蛮状态”,“没有书面语言,没有各种艺术,只不过这个民族异常驯服,欣然接受那些诚实、智慧的人施加影响力”。在陪同卡拉卡瓦环游期间,他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和战略企图,极力阻挠卡拉卡瓦为夏威夷王国寻求其他国家(日本、欧洲列强)保护的数次尝试。作为夏威夷王国的国务大臣,他竟然认为美国吞并夏威夷是正当的、明智的,而卡拉卡瓦国王反对外国干涉夏威夷的事务倒是“愚蠢的”: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感觉到美利坚帝国国旗的新星,很快就会照耀在夏威夷上空,其他国家都不太可能会节外生枝,让这颗新星偏离原有的轨道。
笔者认为,阿姆斯特朗的叙事逻辑只有放到19世纪WASP的世界观之中才能理解。他和卡拉卡瓦的分歧也在于他们的世界观不同。
阿姆斯特朗与卡拉卡瓦:两种世界观的冲突
在返回夏威夷的海上旅途中,阿姆斯特朗与卡拉卡瓦有一场关键性对话,既是对此次环游的总结,也是双方立场上的摊牌。阿姆斯特朗问卡拉卡瓦能给夏威夷人民带来什么。卡拉卡瓦回答说,据他观察,他的夏威夷子民已经比他访问的许多国家的人民好很多了。他们吃穿不愁,从不负债,家里的小农庄就能解决一家人的生计,享受音乐和户外生活,没有饥饿,也没有消化不良,没有人打家劫舍,是他见过的最开心的人民。而阿姆斯特朗对卡拉卡瓦的回答直接否定:
您的人民正在走向灭绝。
阿姆斯特朗此言暗含逼迫卡拉卡瓦下台、让美国统治夏威夷的潜台词——任由卡拉卡瓦和夏威夷土著居民继续过这样“不思进取”的生活,只能走向灭亡,这种局面必须要由美国来改变。面对阿姆斯特朗的挑衅,卡拉卡瓦也毫不让步,表明自己的态度:
您觉得欧洲人和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 库克船长和随之而来的新英格兰人,他们给我的人民带来了麻风病,又让我们强行接受朗姆酒。有一个传教士做了一点好事,就有五百个他的同胞让我们的妇女腐化堕落,传染给她们各种各样的疾病。
双方表态后,卡拉卡瓦回到夏威夷就决定举行加冕仪式,并加强自身的君权。阿姆斯特朗对此深表不满,从夏威夷内阁辞职。美国传教士和白人移民发动武装叛乱,逼迫卡拉卡瓦妥协。在卡拉卡瓦逝世后,他的妹妹利留卡拉尼女王又被白人发动武装叛乱推翻。1894年,在美国的操纵下,夏威夷成立了共和国。1898年,美国政府又正式吞并夏威夷,将其作为“夏威夷领地”。阿姆斯特朗欢欣鼓舞地说:“夏威夷已经成为美国文明在太平洋先进的前哨线了。”对此,格伦·格兰特的看法一针见血:
作者对夏威夷人充满否定,而当时世界各国却承认卡拉卡瓦是一个独立的统治者,接受夏威夷王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夏威夷得以与几十个国家分别缔结合法条约。盎格鲁—撒克逊法律赋予美国什么权利吞并夏威夷,把它先变成领土殖民地再变成州?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土著人所建立的夏威夷王国的主权,又有什么法律、道德上的依据?
笔者认为,卡拉卡瓦与阿姆斯特朗除了在政治上有根本利益的分歧外,还有世界观上的冲突。对于历史和人类文明,卡拉卡瓦抱有古老民族的信仰。他说:“伟大的民族消亡了,新的民族取而代之,如果真是这样,我的民族与他们别无二致。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让我们顺其自然吧。”这种周而复始、听天由命的历史循环观是阿姆斯特朗想重点“改造”的观念。
阿姆斯特朗承认,他屡次对卡拉卡瓦进行说教,想“向国王灌输一些道理”。他认为,卡拉卡瓦在环球旅行中,看到的只有赤裸裸的事实,却无法看到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是“进化规律”。纵观全书,阿姆斯特朗所谓的这种“进化规律”混杂着白人优越主义、基督教的线性史观、近代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通过贬低卡拉卡瓦和夏威夷原住民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以抬高WASP的优越性,目的是对美国吞并夏威夷的行动进行合理化解释。
在阿姆斯特朗看来,当时的世界分为五个等级:(1)最低的一级是夏威夷、塔希提等海岛上的土著居民,他们属于原始部落,不会读书和写字,只有原始崇拜。他们能够有所发展,全靠白人的“悉心照料”。(2)信仰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广大亚非地区,道德感和组织性比原始部落要高一级,但仍然懒散,沉溺于传统宗教崇拜,没有进取心。即使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仍然采取各种方式抵制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3)以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地区,已经开始觉醒,决定向西方学习,但毕竟还是异教徒,不可能被基督教文明完全同化。(4)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主导了当时的世界发展。但大部分欧洲列强都还是君主制,仍需要使用“陛下”(Your Majesty)这种象征衰落文明的词汇。(5)美国不仅在本国建成了伟大的合众国,而且还肩负传教士式的使命,要向海外推广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制度,将“保护人权”“司法独立”和“政治自由”的口号传播到遥远的海岛上。因此,美国是“明日之国”,美国文明将是最高级的文明。美利坚帝国将成为基督教世界新的中心。根据这一文明等级论,美国吞并夏威夷不仅符合“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而且符合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的“历史规律”,甚至符合虔诚、优秀的基督徒改造迷信、慵懒的异教徒的“道德规律”和“宗教规律”。这是19世纪WASP给出的法律和道德上的依据。它试图使美国吞并一个太平洋地区的主权国家成为合法又合理的事情。
1898年,美国完成了吞并夏威夷的计划。同一年,美国还进行了美西战争,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等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少年时代读书之地夏威夷的命运或许也给孙中山先生带来了启示。时至今日,身处百年大变局之中的我们,随着对世界历史和局势的理解加深,更应当看懂、看透美国WASP的世界观。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现代化模式也在不断演变,但其骨子里的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没有任何改变,其弊端愈益明显。”温故而知新,多了解一点世界历史,就能多了解一点现在的世界。而想了解WASP世界观的朋友们,最好读一读这本书。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 》2025年06月04日18版),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在地图演变中看见世界的发展——读龚缨晏《世界地图的故事》2025-04-07
- 在路上,感受自己的精神世界2024-05-26
- 为读者打开自然博物的纸上世界2024-01-17
- 梳理世界艺术史是伟大之事2024-01-15
- “人们并不仅仅靠面包生活”:《十三世纪英格兰村民》中的情感世界2023-11-01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