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系统阐释和勾画影响中国学术思想二百余年的乾嘉学派的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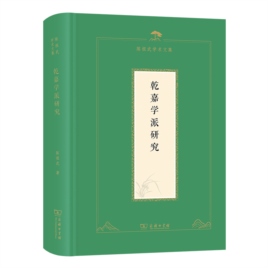
定价:¥198.00
系统阐释和勾画影响中国学术思想二百余年的乾嘉学派的全貌
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经史考证,朴学大兴,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学术史上称之为乾嘉学派。为什么会出现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历史现象?20世纪初叶以来,我们中国的几代学人,都在不间断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20世纪80年代末,陈祖武先生究心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承前哲时贤数十年积累。复以一己不间寒暑之文献爬梳,多历年所,千虑一得,逐渐悟到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百年之久,实非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彼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为宋明以降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所制约、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论究乾嘉学派,不宜孤立地以某一方面的原因把问题简单化,而应当放开视野,多方联系,力求准确地把握历史合力的交汇点,揭示出历史的本质。
晚清七十年之学术大势
道光中叶的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以之为肇始,迄于清朝覆亡,七十年间的中国学术界,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中国社会走出困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以下,拟就此一历史时期的学术演进谈几点极不成熟的认识,一孔之见,难得要领,敬请读者批评。
一、经世思潮的崛起
乾隆中叶以后,正当清高宗宣扬文治、侈谈武功之时,吏治败坏,官逼民反,清王朝业已盛极而衰。嘉庆一朝,其衰颓不振集中表现为此伏彼起的南北民变。就中尤以湘黔苗民起义、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东南沿海武装反清和畿辅天理教起义,予清廷的打击最为沉重。道光前期,王朝的危机则突出地反映为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前者是内忧,后者则是外患,内外夹攻,交相打击,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以空前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为根据,自康熙中叶以后沉寂多年的经世思潮再度崛起,在鸦片战争前后趋于高涨,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序幕。
(一)龚自珍的经世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末,以举人官内阁中书。道光九年(1829)成进士,因书法不中规矩而仍归中书原班。后擢宗人府主事,官至礼部主客司主事,兼祠祭司行走。道光十九年(1839),迫于仕宦艰险,托名避其叔父出任礼部尚书之嫌,拔足南旋。返乡后,置别业于江苏昆山徐元文故园,应聘主持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兼职江苏丹阳县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在丹阳暴病而卒。
龚自珍出身于浙江望族,父祖簪缨文史,世代为官,其外祖段玉裁更是著称一时的文字学家。他自幼随父宦居京城,在家学濡染之下,为学之始即受乾嘉朴学影响。然而置身日趋加剧的社会危机之中,家庭影响毕竟是不能与社会力量相抗衡的。嘉庆十八年(1813)四月,自珍入京应顺天乡试。九月,天理教义军攻击紫禁城,朝野为之震惊。至此,所谓太平盛世已成历史陈迹,一代王朝衰象毕露。“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江河日下的国运,志不得伸的际遇,终于驱使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走上一条特立独行的学以救世的道路。
嘉庆十八年,龚自珍撰成著名的《明良论》四篇,喊出了“更法”的时代呼声。他说:“待其蔽且变,而急思所以救之,恐异日之破坏条例,将有甚焉者也。”自珍敏锐地感受到一场历史大动荡行将来临,于是在随后写成的《尊隐》一文中,他再度敲响惊世之钟:“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二十一年(1816)前后,自珍再成《乙丙之际著议》二十五篇。文中,他深刻地描绘出一幅“将萎之华,惨于槁木”的“衰世”景象:“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对于这样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欲使一世之人皆麻木不仁的衰世,龚自珍痛心疾首,他惊呼:“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因此,龚自珍对现存秩序的合理性大胆提出质疑,他说:“居廊庙而不讲揖让,不如卧穹庐;衣文绣而不闻德音,不如服櫜鞬;居民上、正颜色而患不尊严,不如闭宫庭;有清庐闲馆而不进元儒,不如辟牧薮。”一如《明良论》之倡言“更法”,在《乙丙之际著议》中,龚自珍再次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他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二)魏源“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
道光时代的思想界,魏源与龚自珍同以“绝世奇才”而齐名。他们不仅以各自学以救世的倡导,成为一时经世思潮的领袖,而且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皆是晚清学术的开风气者。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汉士,湖南邵阳金潭(今属隆回县)人。他早年随父宦居京城,相继从胡承珙问汉儒经学,从刘逢禄问《春秋》公羊学,从姚学塽问宋儒理学。道光二年(1822),举顺天乡试,以博学多识,名噪京城,时谚有“记不清,问默深;记不全,问魏源”之语。后屡经会试不第,为地方督抚藩臬聘,作幕四方,于江淮盐务、河工、漕运诸大政,多所赞画。道光二十五年(1845)成进士,累官至高邮知州。咸丰初,太平军下扬州,以“贻误文报”被劾去职。晚年侨居兴化,潜心佛学,法名承贯。咸丰六年(1856),南游西湖。翌年三月,病逝于杭州僧舍。
魏源之学,始自王阳明心学入。及至北上京城,侨寓江南,广交一时耆儒硕彦,视野大开,故于乾嘉汉宋诸学,皆深知其病痛所在。立足动荡的社会现实,他终由《春秋》公羊学而转手,走向了“通经致用”的道路。与汉宋学营垒中人异趣,魏源主张“以经术为治术”,倡导“通经致用”。他说:
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
同将经术与治术、通经与致用合为一体相一致,魏源立足现实,厚今薄古,主张把古今、“三代以上之心”与“三代以下之情势”相结合,进而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社会改革论。他就此阐述道:
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世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
在魏源的现存经学著作中,《诗古微》和《书古微》自成体系,是最能体现他“以经术为治术”思想的著述。尽管二书逞臆武断,牵强立说,多为后世学者讥弹,但是学以经世的精神,在道咸时代的大动荡中,则又是可宝贵的财富。如果说《诗古微》《书古微》是魏源在假经术以谈治术,因而还不得不披上神圣的经学外衣的话,那么他的《皇朝经世文编》以及稍后结撰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则是呼唤经世思潮的旗帜鲜明的呐喊。自《皇朝经世文编》出,同光诸朝,代有续辑,讫于民国,影响历久不衰。
(三)经世思想的高涨
嘉道之际崛起的经世思潮,自管同的《永命篇》倡言改革,经包世臣著《说储》主张废八股、开言路、汰冗言,具体拟议改制方案,到龚自珍社会批判思想的形成,南北呼应,不谋而合,都是一时学术界针对日趋深化的社会危机而发出的拯颓救弊呐喊。由于西方殖民者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愈益加剧的军事威胁,赋予这一思潮以新的时代内容。在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时局使之迅速发生重心的转化,由拯颓救弊转向呼吁挽救民族危亡,成为近代反帝爱国斗争的先导。
在这里,首先应当表彰的是林则徐。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号少穆,晚号俟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以翰林院编修官至湖广总督。道光十八年(1838)末,以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旋任两广总督。讫于二十年九月被诬革职,两年间,林则徐雷厉风行,禁绝鸦片,加强战备,抗敌御侮。同时,又组织译员,从事外国书报的翻译,以知己知彼,抗御外侮。据陈胜粦教授研究,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外国书报,可大致归为五类:一是《澳门新闻纸》六册,并据以选辑《澳门月报》五辑;二是摘译《华事夷言》和《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三是据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为《四洲志》;四是摘译滑达尔著《各国律例》(又译 《万国公法》);五是翻译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应用书籍。其中《四洲志》及相关中外文献,后来皆转交魏源,辑入《海国图志》之中。
经历鸦片战争失败的打击,尤其是《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民族屈辱,魏源率先而起,探讨抗敌御侮的对策。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在江苏镇江晤林则徐,接过《四洲志》等资料,遵林氏嘱,纂辑《海国图志》。翌年,五十卷书成,旋即刊行。后续经增补,于咸丰二年(1852)以一百卷重刊。全书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诸方面情况,开宗明义即揭出撰述宗旨,乃在:“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自此,“师夷长技以制夷”遂成一时进步知识界的共识。
在介绍西方富国强兵之道的同时,魏源又着手总结清代前期的用兵经验,撰为《圣武记》十四卷。该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初成,后叠经增订,于二十四年(1844)重刊。二十六年(1846)再刊。全书与《海国图志》两位一体,激励民族奋发,成为一时探讨抗御外侮途径的重要著述。同林则徐一样,在鸦片战争前后,魏源也是倡导开眼看世界的杰出先驱。
鸦片战争后,清廷的妥协退让,导致投降声浪一度甚嚣尘上。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的经世主张,因之而多遭朝廷士大夫非议。然而当此逆境,与林、魏同调共鸣者,亦不乏其人。其中,尤以姚莹、徐继畬二人影响为大。
姚莹(1785—1853),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和,晚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鸦片战争期间,以台湾兵备道率一方军民抗击英国侵略军,英勇卓杰,名垂史册。《南京条约》签订后,竟因之获咎,贬谪川藏。在颠沛流离之中,他既据亲身经历所得,又“就藏人访西事”,撰成著名的《康纪行》一书。全书十六卷,接武林则徐《四洲志》和魏源《海国图志》,对世界各地的历史地理作了较之林、魏更为详尽的介绍。著者主张通过深入了解各国的情况,以从中寻求抗敌御侮的正确途径。他说:“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书中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英国侵略者对我西藏的觊觎,进而敦促清廷加强边防守备,尤具远见卓识。
徐继畬(1795—1873),字健男,号牧田,一号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自十六年(1836)起,历官广西浔州知府、福建延建邵道、汀漳龙道、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广西巡抚。二十六年(1846),调任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为对外交涉之前沿,徐氏多年供职两广、福建,于各国风土人情多所了解。其间,入觐京城,宣宗曾以各国风土形势为问,徐氏奏对甚悉,后即奉命采辑成书。道光二十八年(1848),《瀛寰志略》十卷竣稿刊行。全书据中外多种图书编纂而成,所涉凡八十余国之风土人情、史地沿革和社会变迁等,尤以东南亚各国资料最称详备。由于该书编纂严谨,构图精审,足以与魏源辑《海国图志》并肩比美,成为鸦片战争后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重要著述。因而不惟在国内风行,而且同《海国图志》一并传入日本,影响甚巨。
二、从“中体西用”到“三民主义”
咸丰间,太平天国民变如火如荼,资本主义列强剑拔弩张,清廷内外交困,国家积弱不振。于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潮应运而起。同治、光绪间,此一思潮凭借时局的短暂稳定而席卷朝野。甲午中日战争清廷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三十余年的“自强新政”,被日本侵略者的炮舰击得粉碎。帝国主义列强凶相毕露,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风潮骤然加剧,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于是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酝酿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潮,遂以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迅速发展成强劲的变法维新思潮。晚清的最后十余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汹涌澎湃的时期。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旗帜,这一思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猛烈地冲击腐朽的君主专制政治,从而推动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埋葬了清王朝。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文化观。它以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先导,中经曾国藩、李鸿章等清廷重臣的首肯而张扬,直到由洋务派殿军张之洞撰《劝学篇》而加以总结,在洋务运动中形成和定型,风行于晚清论坛数十年。
“中体西用”文化观在晚清思想界的风行,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情,它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从文化演进的角度而言,此一文化观的萌生,乃是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的有力挑战,朝野士大夫和知识界的积极回应。其主要目的则在于为接受西学,使之为我所用而进行呼吁。
道光中叶的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文化,以“船坚炮利”向中国文化发出了有力的挑战。如何对待这样一个挑战?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正视现实,倡言“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为了抗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必须向他们在军事上的长处学习。在当时弥漫朝野的保守氛围中,尽管这一主张未能迅速传播,但是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再败之后,慑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奕、曾国藩、李鸿章等内外重臣被迫接受了严酷的现实。咸丰十年(1860),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他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 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的这一主张,同奕、李鸿章等此呼彼应,无异向朝野发出信号,即可以有选择地向西方学习,具体地说,就是向列强学习“船坚炮利”之术。
清廷重臣的思想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则来源于进步知识界的促进。在这方面,最先发出呐喊的便是冯桂芬。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又号邓尉山人,江苏吴县人。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右中允。后因病居乡不出,讲学著书,岿然为东南耆宿。他学有根柢,经史、小学,多所究心,于天文、历法、数学,尤多用力。面对列强侵略,他接武林则徐、魏源,于时务多有议论,且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更深入一层。咸丰十一年(1861),他的《校邠庐抗议》编成。全书二卷,凡五十篇。书中冯桂芬倡言“采西学”“制洋器”,敢于承认中国“四不如夷”,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而主张在不违背“三代圣人之法”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他甚至说:“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一言以蔽之,冯桂芬所提出的文化观,就叫作:“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为“中体西用”文化观确立了基本格局。此后之阐发“中体西用”说者,无论是洋务派中人,还是批评洋务派的早期改良主义者,乃至倡变法以图强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皆未能从总体上逾越其藩篱。同治、光绪间的思想界,一如梁启超所论,“中体西用”之说,确乎大有“举国以为至言”之势。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张之洞推出《劝学篇》,对之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总结。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卒谥文襄,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官湖北、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湖广总督,晚年以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病逝。作为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张之洞以兴办洋务的诸多业绩,而对晚清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之相辅而行,身为名重朝野的儒臣,他学养深厚,政教并举,亦对晚清学术留下了深刻影响。何以要结撰《劝学篇》?张之洞于此有如下说明: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如何评价“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赞成冯天瑜教授的意见。冯先生认为,洋务运动初起,统治阶级中人提出这样一种“折中”的文化选择,自有其进步意义。然而在酝酿维新变法的关键时刻,依然坚持这样的文化观,力图以“中体”去抗拒变法,当然是不可取的。戊戌变法失败,政治革命已经提上日程,仍旧鼓吹“中体西用”, 就更是对抗革命舆论,妨碍思想解放,阻挠社会进步。
(二)梁启超的变法活动及学术贡献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自幼即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科第,才气横溢。光绪十六年(1890)春,入京会试,颓然受挫。南归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眼界为之一开。初秋返粤,得以结识学海堂高材生陈千秋。时值康有为以布衣上书受逐,寓居广州。千秋服膺康氏学术,梁启超遂于是年八月通过千秋以弟子礼前往拜谒。这次历史性的拜谒,成为梁启超一生学术和事业的里程碑。从此,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揭开了康、梁并称的一页。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廷腐败无能,丧师败绩。国家民族的危难,把正在万木草堂求学的梁启超召唤到荆棘丛生的政治舞台。翌年春,他北上京城。三月,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和约的消息传来,启超与其师康有为挺身而起,组织在京会试的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反对割地赔款,力主拒和、迁都、变法。此后数年,启超奔走南北,投身变法救亡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为发生在当年的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他写下了自己青年时代极为悲壮的一页。
这年正月,梁启超抱病北上,二月抵京。面对西方列强的瓜分风潮,他不顾病体孱弱,冒险犯难,愤然奔走呼号。四月二十三日,以光绪皇帝颁发的定国是诏谕为标志,梁启超、康有为等志士多年来为之奋斗的变法维新,一度演成事实。八月初六日,梁启超正在谭嗣同寓所商议国事,忽然接到宫廷政变发生,光绪皇帝被软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报告,而且还得悉康有为住宅已被查抄。谭嗣同决意一死报国,敦促梁启超潜往日本驻华使馆求助。后幸为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庇护,始得取道天津,投日轮东渡。从此,讫于清亡,他一直客居日本。
百日维新后的十余年间,同在政治舞台上的连年受挫相反,梁启超的学问则大为增进。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锐意求治,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还是学术文化诸方面,都一跃而成为亚洲一流强国。梁启超置身于这样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度,使他得以广泛接触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深入探讨日本强盛的经验。这不仅给了他以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而且也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使之摆脱康有为的改制、保教说,接受了西方的资产阶级进化论。梁启超抱定“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的为学宗旨,以“思想界的陈涉”自任,在这十余年间,写下了大量的、影响深远的政论文章,成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先行者之一。
作为进化论的笃信者,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他将此一理论引入史学领域,转而致力于中国历史学的建设,发愿编著《中国通史》。为此,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其中尤以刊布于光绪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影响最巨。
在中国史学史上,梁启超第一次引进了“历史哲学”的概念。他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尤为可贵者,他正是以之为依据,朦胧地触及了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轨迹,提出了历史进程“非为一直线”的思想。他指出:“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梁启超就是这样以他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史界革命”,最早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引入中国,而且也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把“史界革命”的主张诉诸实践,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全文原拟作十六章,惜仅写至前六章即搁笔。后来,他又于光绪三十年(1904)续作八、九章,以《近世学术》为题刊行。梁启超的这篇学术论著,虽然对章炳麟所著《訄书》多有借鉴,但是他却以较之章氏略胜一筹的高屋建瓴之势,对中国古代学术演进的历史做了鸟瞰式的勾勒。他不仅把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视为一个有公理公例可循的历史进程,而且就历史编纂学而言,则在旧有的学案体史籍基础上,酝酿了一个飞跃,开启了一条广阔而坚实的研究途径。
(三)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提出
孙中山先生(1866—1925),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华民国的伟大缔造者。在晚清的最后十余年间,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日趋成熟,以“三民主义”学说的提出为标志,有力地推动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涨,成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山先生于当年十月抵达檀香山。在他的倡导下,革命组织兴中会成立。兴中会的《盟书》《章程》,皆为中山先生草拟。在《盟书》中,中山先生为这一团体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斗争目标。而中山先生草拟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则明确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翌年正月,中山先生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并着手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后因事机不密受挫,中山先生被迫流亡欧美。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获悉中山先生伦敦踪迹,遂由驻英使馆将先生诱捕。幸得英国友人相助,逃出使馆。从此,中山先生以中国革命家而驰名于世。他的革命思想,亦通过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向四方传播。
光绪三十年(1904),中山先生的著名论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在美国发表。文中,中山先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理想。他说:“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中山先生号召,建立“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即“把过时的……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中山先生就此指出:“这样一来,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就能解除其他国家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的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有许多极有教养的能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起组织新政府的任务。”孙中山先生满怀信心地瞻望前程,明确向全世界昭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
为了实现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以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为中心,联合其他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从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趋向高涨。同年十月,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中山先生为该刊撰发刊词,文中,先生第一次完整地揭示了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中山先生说: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施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一年之后,为庆祝《民报》创刊一周年,中山先生在日本发表重要演说,对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做了全面阐发。中山先生指出:“兄弟想《民报》发刊以来已经一年,所讲的是三大主义:第一是民族主义,第二是民权主义,第三是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中山先生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所谓民族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山先生稍后所说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倾覆满洲政府”。关于民权主义,中山先生说:“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因此归结到一句话,中山先生讲的“民权主义”,就叫作“建立民国”。关于民生主义,中山先生说:“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中山先生认为,对于社会问题应当未雨绸缪,“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平均地权”。
中山先生的结论是:“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为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思想指导,故而使之在思想上战胜了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并为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会通汉宋学术以求新
晚清七十年间的学术,有一潮流行之最久,亦最可注意,这便是会通汉宋,推陈出新。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论清代学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王先生所说的“新”,既指当时方兴未艾的西学,同时亦应包括中国传统学术在会通汉宋中的自我更新。
(一)曾国藩与晚清理学
晚清理学,枯槁狭隘,已非宋明时代之可同日而语。惟得一曾国藩,以其事功学业相济,几呈中兴之势。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以翰林院检讨累官至大学士兼直隶、两江总督。他一生既以功业显,为洋务派重要领袖,亦以学业著,实为晚清学术界一承前启后之关键人物。
曾国藩之学术,既承桐城姚鼐遗绪,又得乡先辈唐鉴熏陶。曾国藩为学,虽承唐鉴之教,但又不拘门户。多方采获,遂终能由博返约,自成一家。乾嘉以还,汉学脱离社会实际的积弊,到曾国藩的时代已经看得很清楚。所以,在为《国朝学案小识》作跋时,曾国藩对汉学病痛进行针砭,指出: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
这就是说,乾嘉学派中人引为学的之“实事求是”,在曾国藩看来,同朱子主张的“即物穷理”并无二致。
然而于汉学中人所擅长的“博核考辨”,曾国藩则并不一概抹煞。他表示:“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又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对于一时朝野每以太平天国民变归咎汉学,曾国藩则持异议,他说:
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酿晚明之祸,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
他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
由此出发,曾国藩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己任,极意表彰礼学,主张以之去经世济民。他说: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焚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
对于曾国藩在晚清学术史上的地位,已故钱宾四先生早年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过专题讨论。宾四先生指出:“涤生论学,……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大师定评,实是不刊。
(二)黄式三的实事求是之学
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晚号知非子,浙江定海人。式三早年为岁贡生,屡应乡试不售,遂绝弃举业,专意治经。他毕生为学,“以治经为天职”,主张会通汉宋,实事求是。他说:“经无汉宋,曷为学分汉宋也乎!自明季儒者疏于治经,急于讲学,喜标宗旨,始有汉学、宋学之分。”又说:“学者分汉宋为二,誉矛忘盾,誉盾忘矛,读沈征君《果堂集》而知其非矣。……惠征君定宇,治汉学者之所宗也,志君之墓则曰:‘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昌;经术之士,汩于利而行不笃。君能去两短,集两长。’然则士苟志学,何不取汉宋之所长者兼法之也邪!”因之式三倡言:“天下学术之正,莫重于实事求是,而天下之大患,在于蔑古而自以为是。”
黄式三早年,即本“实事求是”为学的,撰为《汉郑君粹言》一书,以推尊郑玄学说。书中有云:
世推北海郑君康成为经学之祖,辄复以短于理义而小之。郑君果短于理义乎哉?……夫理义者,经学之本原;考据训诂者,经学之枝叶、之流委也。削其枝叶而干将枯,滞其流委而原将绝。人苦不自知,而诩诩焉以其将枯绝者,矜为有本有原,鄙意所不信。而谓好学如郑君,无本而能有枝叶,无原而能有流委,尤不敢信之矣。
而对于一时学术界中人宗汉宗宋,分门别户,黄式三深不以为然,他说:“自治经者判汉宋为两戒,各守专家,而信其所安,必并信其所未安。自欺欺人,终至欺圣欺天而不悟,是式三所甚悯也。”因此,黄式三既肯定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可以救忘本失源之弊”,同时又指出:“江氏宗郑而遂黜朱,抑又偏矣。”他的结论是:“江氏宗师惠、余,揽阎、江诸公为汉学,必分宋学而二之,适以增后人之惑也。”
式三晚年,尤好礼学,认为:“礼者理也。古之所谓穷理者,即治礼之学也。尽性在此,定命在此。”式三治礼,谨守郑学,不废朱子,于封建、井田、兵赋、郊禘、宗庙、学校、明堂、宗法诸大节目,凡有疑义,多所厘正。所撰《复礼说》《崇礼说》《约礼说》三篇,荟萃一生治礼心得,提纲挈领,最得礼意。《复礼说》集中讨论礼之渊源流变,一以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为依归,他说:
礼也者,制之圣人,而秩之自天。当民之初生,礼仪未备,而本于性之所自然,发于情之不容已,礼遂行于其间。……孔圣言克己复礼为仁。复礼者,为仁之实功也,尽性之实功也。
《崇礼说》论证“礼即为德性”,进而主张以“崇礼”为根本,融尊德性与道问学于一体。文中指出:
君子崇礼以凝道者也,知礼之为德性也而尊之,知礼之宜问学也而道之,道问学所以尊德性也。……后世君子,外礼而内德性,所尊或入于虚无;去礼而滥问学,所道或流于支离。此未知崇礼之为要也。不崇礼即非至德,何以能凝至道!
《约礼说》则阐发《论语》博文约礼旨趣,并据以驳难“以心之臆见为理”“以本心之天理言礼”的诬枉。式三说:
《论语》言博文约礼,圣训章矣。礼即先王之《礼经》也。王阳明《博约说》,博其显而可见之礼曰文,约以微而难见之理曰礼。岂圣人之教,必待王氏斡补而后明乎?礼一也,分显微而二之。文与礼二也,以礼之显者为文而一之。其所谓理,谁能明之乎?……以心之臆见为理,而理已诬;以本心之天理言礼,而礼又诬。
(三)黄以周会通汉宋学术的努力
黄以周(1828—1899),字元同,号儆季,晚号哉生,浙江定海人。定海黄氏,世代力农。至以周祖兴梧,有志经学,以治《易》《诗》著名庠序。以周父式三继起,潜心经学,遍治群经,晚专以治经名家。以周幼承庭训,为学伊始,即在式三课督之下奠定经学藩篱。他六岁入塾识字,七岁便开始读《小戴记》,初知礼学。后依次读《尚书》《诗经》《周易》,打下坚实经学根柢。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军蹂躏定海,以周随父避兵镇海之海晏乡。迄于式三病逝,二十余年间,一门朴学,治经传家。式三晚年,笃志礼学。以周亦步亦趋,专意读礼。他先是读秦蕙田《五礼通考》,病秦氏书言吉礼之好难郑玄说,军礼又太阿康成意,于是每一卷毕,皆有札记。自咸丰十年(1860)起,开始全面整理和总结历代礼学,结撰《礼书通故》,从此走上会通汉宋、表彰礼学的为学道路。时年三十三岁。
以周治礼,一秉其父之教,扫除门户,实事求是。他说:“六经之外无所谓道,六书之外无所谓学。故欲谭道者先通经,欲通经者先识字。”又说:“离故训以谈经而经晦,离经以谈道而道晦。”因此,以周主张:“去汉学之琐碎而取其大,绝宋学之空虚而核诸实。”他读《汉书·艺文志》,就《孝经》《尔雅》共编一家,成札记一篇,有云:“凡解经之书,自古分二例,一宗故训,一论大义。宗故训者,其说必精,而拘者为之,则凝滞章句,破碎大道;论大义者,其趣必博,而荡者为之,则离经空谈,违失本真。博其趣如《孝经》,精其说如《尔雅》,解经乃无流弊。《汉志》合而编之,乃所以示汉世读经之法。惜今之讲汉学、讲宋学者,分道扬镳,皆未喻斯意。”以如是之见而论《汉志》,可谓读书得间,别具只眼。
同治元年(1862),黄式三病逝,以周居丧守制,读礼不辍。至光绪四年(1878),历时十九年,《礼书通故》撰成,以周已然年逾半百。全书一百卷,自礼书、宫室、衣服、卜筮,至六书、乐律、车制、名物诸通故,附以仪节、名物二图及叙目,凡作五十目。以周所撰该书叙,梳理礼学源流,阐发著述大旨,最可见其礼学思想。他说:
夫礼唐修其五,虞典以三,夏造殷因,周礼犹醵。东迁以后,旧章云亡,孔子赞修,犹苦无征,言、曾讨论,又复错出。礼学难言,由来久矣。战国去籍,暴秦焚书,先王典章,尽为湮没。抱残守阙,汉博士之功也。分门别户,又汉博士之陋也。宣帝忧之,遂开石渠,以为不讲家法,无以明其宗旨,专守家法,又恐戾乎群经。于是令其法之异者,各陈师说,博观其义,临决称制,以定一尊。小戴次君,爰作奏议,执两用中,有合古道。白虎之论,聿追前徽,班氏孟坚,又纂通义,乃专取一己所好,尽扫群贤之议,大义虽存,师法莫考。许君叔重,裒集异议,拾戴议之遗,砭班论之锢,殽陈众见,条加案语。郑君康成,又驳其非而存其是,古礼以明。
夫西京之初,经分数家,东京以来,家分数说。一严其守,愈守愈精;一求其通,愈通愈密。诸博士,其守之精者也;戴、许二书,其通者也;郑所注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其密者也。唐宋以来,礼学日微,好深思者或逞臆说,好述古者又少心得。究其通弊,不出两轨。以周不揣谫陋,缀入异闻,不敢立异,亦不敢苟同,为之反复群书,日夜覃思。贤者识大,不贤识小,道苟在人,何分扃途。上自汉唐,下迄当世,经注史说,诸子杂家,谊有旁涉,随事辑录。昔者高密笺《诗》而屡易毛传,注《礼》而屡异先郑,识已精通乎六艺,学不专守于一家。是书之作,窃取兹意,以为按文究例,经生之功,实事求是,通儒之学。或者反以不分师说为我诟病,甘作先儒之佞臣,卒为古圣之乱贼,惴惴自惧,窃有不敢。
《礼书通故》成,一时经学大师俞樾欣然撰序,备加称道。俞先生说:
国朝经术昌明,大儒辈出,于是议礼之家日以精密。……而荟萃成书,集礼家之大成者,则莫如秦味经氏之《五礼通考》。曾文正公尝与余言,此书体大物博,历代典章具在于此,三通之外,得此而四,为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余读之诚然。惟秦氏之书,按而不断,无所折衷,可谓礼学之渊薮,而未足为治礼者之艺极。求其博学详说,去非求是,得以窥见先王制作之潭奥者,其在定海黄氏之书乎!……君为此书,不墨守一家之学,综贯群经,博采众论,实事求是,惟善是从。……洵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视秦氏《五礼通考》,博或不及,精则过之。
晚近著名经史学家胡玉缙先生为其师《礼书通故》撰写提要,亦给了该书以“体大思精”的至高评价。
《礼书通故》刊行,已是光绪十九年(1893),以周年届六十六岁。晚年的黄以周,表彰先秦诸子,沟通孔孟学说,依然专意兴复礼学。对于颜子,他表彰道:“颜子之所乐者天,而乐天之学由好礼始。……颜子所见之大,虽无容轻拟,要不越《中庸》所谓‘优优’之礼矣。……颜子有王佐才,要亦不出乎礼。”由表彰颜渊而及赵宋诸儒,以周又说:“朱子论程门高第弟子,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皆入禅学,惟吕与叔不入禅。吕氏初学于张子横渠,湛深礼学者也。朱子之门,群推黄子勉斋为冠,黄子亦深于礼。”以周认为:“古人论学,详言礼而略言理,礼即天理之秩然者也。”因此,他的结论是:“考礼之学,即穷理之学。”本此认识,黄氏论曾子有云:“曾子之穷理,本末兼彻,经权并明,故卒能得孔孟一贯之传,又何间焉!”
对于子游、子夏,黄以周亦有专文表彰,他说:
《仪礼》之记,先儒多以为子夏作。子游之言,亦多散见于《戴记》中。二子之学,实于礼为尤长。……学士之习礼者,专尚繁文缛节,务外而遗内,不知礼意所在。子游欲挽末流之失,独作探本之论。……子夏谨守礼文而不夺其伦,子游深知礼意而不滞于迹,一沉潜,一高明,学各得其性之所近。
一谨守礼文,一深知礼义,一沉潜,一高明,黄以周之表彰子夏、子游学说,其着眼点亦在礼学。
黄以周晚年最为精意者,则是表彰子思子。为此,他以六十九岁之年,辑为《子思子辑解》七卷。以周考证:“子思困于宋作《中庸》,归于鲁作《表记》。”不惟若此,黄氏还推阐先儒旧说,以论证今本《礼记》之《坊记》《缁衣》诸篇,皆出子思手。他说:
《旧唐书》载沈约之言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诸子思子。王伯厚《艺文考证》,径引沈言。夫子思子作《中庸》,史有明文。《文选注》引子思子“民以君为心”二句及《诗》云“昔有先正”四句,今皆见《缁衣》篇。则《缁衣》出于子思子,可信。且小戴辑记,以《坊记》厕《中庸》前,《表记》《缁衣》厕《中庸》后,与大戴类取《曾子》十篇正同。《坊记》《表记》《缁衣》,皆以“子言之”发端,其文法尤相类,则休文之言益信。
近者湖北郭店楚简出,时贤多有表彰子思学说者,黄儆季先生之说,考信不诬。黄先生九泉有知,当可安息矣。
四、结语
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一时朝野俊彦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中国社会之走出困境,为中国学术之谋求发展,殊途同归,百家争鸣。晚近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论清代学术,以一“新”字而言晚清,得其大体,实是不刊。七十年间,先是今文经学复兴同经世思潮崛起合流,从而揭开晚清学术史之序幕。继之洋务思潮起,新旧体用之争,一度呈席卷朝野之势。而与之同时,会通汉宋,假《公羊》以议政之风亦愈演愈烈,终成戊戌维新之思想狂飙。晚清的最后一二十年间,“以礼代理”之说蔚成风气,遂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出而集其大成。先秦诸子学之复兴,后海先河,穷源竟委,更成一时思想解放之关键。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挺生其间,以之为旗帜,思想解放与武装抗争相辅相成,遂孕育武昌首义而埋葬清王朝。
有清一代学术,由清初顾炎武倡“经学即理学”开启先路,至晚清曾国藩、陈澧和黄式三、以周父子会通汉宋,兴复礼学,揭出“礼学即理学”而得一总结。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历时三百年,亦随世运变迁而向会通汉宋以求新的方向演进。腐朽的清王朝虽然无可挽回地覆亡了,然而立足当世,总结既往,会通汉宋以求新的学术潮流,与融域外先进学术为我所有的民族气魄相汇合,中国学术依然在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曲折地前进。跟在别人的后面跑,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这不就是晚清七十年的学术给我们所昭示的真理吗!
述往思来,鉴古训今。认真总结晚清七十年的学术史,对于今日及尔后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是会有益处的。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