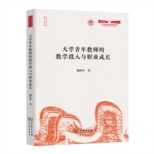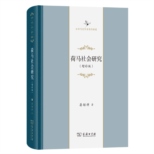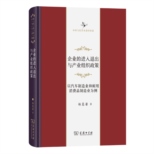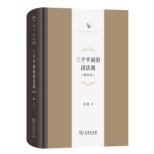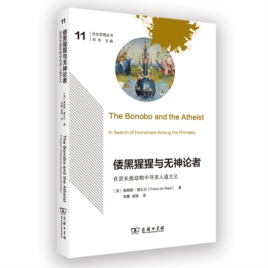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热爱和平、性趣盎然的倭黑猩猩,究竟是演化史上的孱弱异类,还是伊甸园中理想人类的化身?且听弗朗斯·德瓦尔细述由动物书写的历史,解读镶嵌在灵长类基因中的道德哲学密码
★以人文之光观照生物学谜思,描摹温情脉脉的“另类”动物世界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我们似乎习惯了从互相杀戮的食物链视角看待野生动物,就连需要共同生活、集体行动的群居动物内部,也逃不脱群内争霸、胜者为王的刻板印象,仿佛唯有征战不休,才是生存之道。
而在心理学家兼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那里,若摘下被“兽性”概念镀上杂色的望远镜,带上包容谦逊、平等真诚的人文主义情怀,在田野中认真观察、仔细体会,残酷血腥的动物世界其实是另一幅模样:如“党鞭”一般统领雌性、影响雄性政治的黑猩猩女王,已年老力衰但仍要热情拉架的“和事佬”,爱耍小聪明、瞒着头领小心翼翼偷欢的雄猕猴,举起自己的孩子、与同为人母的科学家两两相望的雌猩,为濒死同伴提供临终关怀、陪他走完最后一程的猩群……有竞争,也有团结;有流血殴斗,也有握手言和;有偷奸耍滑,也有无私奉献。透过德瓦尔平实而生动的文字,透过贯穿全书的精彩又温暖的小故事,我们将见识到过去未曾涉足的动物世界的另一面,并重新思考那个困扰历代学人的经典问题:究竟是什么让大自然中的芸芸众生走得更远?
★以灵长类之眼透视人类社会,剑指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当我们渴求以动物界规则为锁钥,为人类社会议题找到答案时,可能会落入怎样的理论误区?当我们以人类本位为前提,为“以爱止战”的倭黑猩猩和“武德充沛”的黑猩猩论战不休时,我们究竟在争辩什么?细读本书,读者将发现,德瓦尔的书写正是对这种思路的“反叛”:将人类世界的种种概念一厢情愿、简单粗暴地套用到这些灵长类近亲身上,想象发展出宗教的猩猩对神祇祈祷“愿您的国降临”,实属大可不必;而回溯道德在生物演化史上的起点,人类和其他动物在某种意义上并无多少高下之分。
本书以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的笔法,回顾了数世纪来历代学者的探究成果,带领我们沿着演化树的枝桠向上攀援。由此,我们将重新审视人类与类人猿在心灵上的距离,解构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印象,并意识到那些本以为是我们所独有的禁忌和律令实则早已镌刻在动物的社会性中,甚至在它们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诠释。
电影《流浪地球2》中,周喆直的联合国演讲以一根断裂后愈合的股骨作引,诠释了人类文明何以通过互助团结繁衍至今;而在我们的灵长类近亲那里,我们也将找到属于它们的愈合的股骨,找到超越人猿之分的“人”道主义之光。
★在现代社会重新理解演化论的道德意义
由达尔文等学者创立并不断发展的生物演化论如今已得到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可正如本书所呈现的学界百态,即便掌握了丰富的实物证据,不断填充“人猿相揖别”后人类漫长的“小儿时节”的空白,仍有反演化论者依托宗教阵地顽固抵抗,一如初次听闻“从猿到人”之说的模样;而另一方面,强调优胜劣汰、强者权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打着科学的旗号,以人类社会为法庭,不断对“违背自然规律”的伦理道德进行严苛的审判,尽管达尔文自己都肯定了人类为善的能力与动物情感的价值。
时至今日,演化论衍生出的正反两面仍在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对社会生活具体现象的认知,譬如是否应该扶助老弱病残,情感有无意义,不同生命的价值几何。面对一场场激烈论战、一个个经典辩题,我们心中或已有答案,或悬而未决;此书必将为各位读者提供一种视角和知识上的参考,让我们从热火朝天的辩论桌前后退几步,反思演化与道德本应如何相互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