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一位汉学家用哲学的眼光去审视中国儒家原典所蕴含的思想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19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的《中国圣书》,至今仍在世界各地不断印刷出版,其翻译不仅使中国典籍的生命在另一个时空得以延续,更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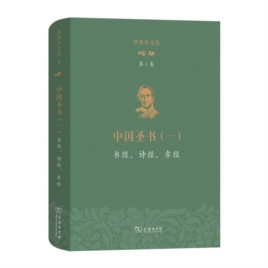
定价:¥120.00
一位汉学家用哲学的眼光去审视中国儒家原典所蕴含的思想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19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的《中国圣书》,至今仍在世界各地不断印刷出版,其翻译不仅使中国典籍的生命在另一个时空得以延续,更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理雅各文集》第1卷辑录了由理雅各译注的《中国圣书(一)》,包括《书经》《诗经》《孝经》,并将序言、导论译成中文,辅以费乐仁(Lauren F.Pfister)所撰导读。
作为19世纪西方汉学的大师,理雅各通过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诠释,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中西文明的交流搭建了一座“文化之桥”。
《中国圣书》第一卷是理雅各为《东方圣书》贡献的第一卷书。《东方圣书》是理雅各著名的同事麦克斯·缪勒主编的一套丛书,总计50卷,理雅各为之贡献了6卷。理雅各1876年在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开始了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的生涯,在他任职仅仅三年后便有了这卷书的出版。此前,理雅各在香港从事传教事业,于1867年从伦敦会退休,结束了他长达20多年的传教士生涯,后来又于1870—1873年在香港佑宁堂(Union Church)担任全职牧师。尽管如此,传教期间的理雅各在很大意义上仍然堪称一位汉学家。与英国国内许多普通基督徒一样,理雅各是支持各个活跃在大清帝国的差会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特别关注理雅各如何把他对中国“圣书”的讨论导向基督徒读者。
作为教授,理雅各不仅要教授学院的课程,还要为整个牛津大学开设讲座。一般一年要开设两次大学讲座,这些讲座大部分都被认真地记录了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在1879年这卷书出版之前,理雅各没有讲过其中的任何一部儒经。只是在数年后的 1883 和 1884 年,理雅各才讲了“中国年表”(Chinese Chronology)和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朝代,这就会提到《尚书》(理雅各喜欢称之为《书经》)里的事件。后来他有一场“中国诗歌”的讲座,应该会提到《诗经》。理雅各没有开设过关于《孝经》性质或《孝经》注疏史的讲座。
另外,在1879年理雅各教授就在他的正常课程中讲授“中国历史”,而且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继续与学生一起学习不同的史书,尤其是《史记》。从1886年开始他才为部分课程讲授了部分《诗经》,但《孝经》本身从未成为任何课程的指定读物。
理雅各贡献的这一卷《中国圣书》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它包含
了理雅各曾在《中国经典》系列翻译过的两部儒经,包括《书经》(《中国经典》第三卷,1865年)和部分《诗经》(《中国经典》第四卷,1871年)。后几卷《中国圣书》都没有包含之前出版过的经书。那么,问题就来了,理雅各是否只是重印了之前他已经翻译和阐释过的《书经》和《诗经》?这样的问题显然有些意外。理雅各作为专注于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的译者和阐释者,这样的问题将揭示他学术生涯的许多面相,将表明他是如何认真地重新思考那些翻译的。我们将看到改译的地方并不多,但这些改变揭示了理雅各在智识上长期浸淫于中国古典文本,这不仅是他在牛津大学的学术模式,更是在他到牛津大学之前就养成了。另外,它也表明理雅各的翻译和阐释并非“完美”,也不是没有错误,但这些翻译和阐释是他在学术上孜孜不倦追求的结果。这其中的许多细节都可在本导读所附的两份表格中看出。
如表所示,1879年前理雅各不仅出版了《书经》的完整译本,而且还有两个完整的《诗经》译本(一个为散文体,一个为英文韵律体)。但他之前从未出版过《孝经》的译本。他为《东方圣书》准备的所有这些译本与《中国经典》最大的不同是,它们仅以英文呈现,而《中国经典》则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呈现。鉴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经典》针对的不仅是英文读者,也包括中文读者,而且在翻译《中国经典》时理雅各还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帮助;但《中国圣书》针对的仅仅是英文读者,是理雅各独立完成的。
我们还应论及本卷书产生的背景,即理雅各其他方面的经历和活动,但读者可在《中国圣书》总论中发现有这些方面的详细论述。其中包括理雅各对中国经书理解的加深,1873年他最后一次离开香港之后到华北旅行的人生经历,及至1876年他担任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的教授。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