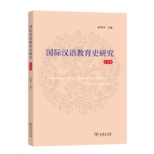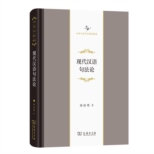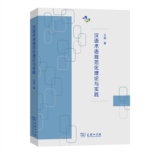显示全部序言
序
徐 枢
王艾录、司富珍两先生的《汉语的语词理据》一书已经完稿了。我有幸在付印前看了一遍,觉得很受教益,想借此机会谈点个人的感想。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词汇研究和语法研究均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我有一个感觉,即大多数研究成果还是侧重于事实的描写和叙述。至于事实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里面有无一定的缘由,却很少有人作深层次的思考与探讨。即使有所涉及,也大都限于少数问题或个别论文。仅以词汇而言,系统而全面地考察词语形成动因的专著,《汉语的语词理据》还是我国第一部。这部著作应该说是填补了这个领域的一项空白。
词汇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如果我们既能对词语的含义和用法准确地加以说明,又能对它们采取这一说法的原因加以解释,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已达到或接近了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境界。当然,这样的工作是相当艰巨的。因为除了要解决许多理论性质的问题以外,还要参阅大量古代、近代、现代的语料,要研究各种有关的人文资料,有时还需要考察语音、句法等现象。可以想见,撰写这部著作是花费了大量心血与劳动的。
书中渗透着的两个重要观点(这两个观点在他们的另外一本书稿中有较详细的论述)值得重视。这两个观点不但饶有新意,而且是书中实例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个观点是,理据并不等同于内部形式。作者认为,过去有些语言学论著常常把它们混淆起来,因而造成了分析上的偏误。事实上,理据虽与内部形式有密切联系,但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要区别二者的界限,首先应该确认单纯符号与合成符号的不同。为了有助于理解作者的观点,书中还附有理据与内部形式关系的示意图。
另一个观点是任意性和理据性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势如水火的。我们知道,索绪尔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论点: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这一论点在国内外语言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比如,目前国内“语言学概论”一类的著作大多持有如下看法:“音义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没有道理可言的。”而一些反对任意性的人又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任意性是一个“虚构的原则”。本书作者经过严密论证和对语言事实的深入分析,认为理据性和任意性是同样重要的原则,二者并非不可调和,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我们赞赏作者的看法,因为它不但覆盖面宽,可以解释大量的语言现象,而且也因为真理往往就在截然对立的两个极端的中间。
从全书的格局看,大体而言,前半部侧重方法方面的研讨,后半部侧重本体方面的研讨,此外书中还有大量的、有关汉语词语理据的实例。这些实例知识性强,而且大都十分富于情趣。比如“原来”本写作“元来”,因明代朱元璋推翻元朝以后,再说“元来”就有让元朝复辟、卷土重来之嫌,所以改“元”为“原”。“两个小时”中的“小时”何以称为“小”?书中告诉我们:我国古代用“日晷”、“铜壶滴漏”计时,将一昼夜分作十二个时辰。钟表传入我国后,逐步使用了新的计时制度。因为新制一个钟头相当于古代一个时辰的二分之一,于是把新制的一个钟头叫“小时”,而把旧制的一个时辰叫“大时”。再如,“桥牌”中的“桥”,我们都知道这是英语bridge的意译,但这种牌到底与“桥”有何关联,书中也十分生动地叙述了它的得名由来。
当然,探讨词语的理据有时相当困难,也可能引起一些争议。比如“熊猫”一词。许多人把这个词理解为“如熊之猫”。王艾录先生在《汉语理据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中指出这个词的理据是“体形若猫似熊”。本书里作者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50年代初期,重庆北碚博物馆首次展出这种动物时,标牌上横写着“猫熊”两个大字。参观者按照当时习惯,从右到左误读成“熊猫”。从此以讹传讹,“猫熊”就逐渐为“熊猫”所代替了。这个例子说明,探讨理据同不断深入挖掘语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一些理据不明或无法找到理据的词语,更需花费很多时间去搜索材料,进行分析或论证。
理据研究十分重要。除了我们开头部分提到的以外,它对语言规范化、对词典编纂、对确定某些词语的书写形式、甚至对研究文化与民俗,都很有助益。这在本书已有不少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有关两位作者的话。王艾录先生我过去并不认识,只是经常读到他的文章,觉得他视野开阔,勇于探索,所论颇多新意。我在给研究生授课时,也常常提到王艾录先生的观点,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司富珍是王先生的研究生,她的主攻方向是借鉴自组织理论研究汉语理据,并和她的导师一起撰写了这部专著。能在就读研究生期间作出这样的成绩,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果今后条件许可,我希望他们能进一步深化汉语理据问题的研究,继续撰写汉语句法理据的论著,以推动这方面研究的开展。
是为序。
1998年8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徐 枢
王艾录、司富珍两先生的《汉语的语词理据》一书已经完稿了。我有幸在付印前看了一遍,觉得很受教益,想借此机会谈点个人的感想。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词汇研究和语法研究均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我有一个感觉,即大多数研究成果还是侧重于事实的描写和叙述。至于事实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里面有无一定的缘由,却很少有人作深层次的思考与探讨。即使有所涉及,也大都限于少数问题或个别论文。仅以词汇而言,系统而全面地考察词语形成动因的专著,《汉语的语词理据》还是我国第一部。这部著作应该说是填补了这个领域的一项空白。
词汇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如果我们既能对词语的含义和用法准确地加以说明,又能对它们采取这一说法的原因加以解释,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已达到或接近了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境界。当然,这样的工作是相当艰巨的。因为除了要解决许多理论性质的问题以外,还要参阅大量古代、近代、现代的语料,要研究各种有关的人文资料,有时还需要考察语音、句法等现象。可以想见,撰写这部著作是花费了大量心血与劳动的。
书中渗透着的两个重要观点(这两个观点在他们的另外一本书稿中有较详细的论述)值得重视。这两个观点不但饶有新意,而且是书中实例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个观点是,理据并不等同于内部形式。作者认为,过去有些语言学论著常常把它们混淆起来,因而造成了分析上的偏误。事实上,理据虽与内部形式有密切联系,但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要区别二者的界限,首先应该确认单纯符号与合成符号的不同。为了有助于理解作者的观点,书中还附有理据与内部形式关系的示意图。
另一个观点是任意性和理据性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势如水火的。我们知道,索绪尔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论点: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这一论点在国内外语言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比如,目前国内“语言学概论”一类的著作大多持有如下看法:“音义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没有道理可言的。”而一些反对任意性的人又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任意性是一个“虚构的原则”。本书作者经过严密论证和对语言事实的深入分析,认为理据性和任意性是同样重要的原则,二者并非不可调和,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我们赞赏作者的看法,因为它不但覆盖面宽,可以解释大量的语言现象,而且也因为真理往往就在截然对立的两个极端的中间。
从全书的格局看,大体而言,前半部侧重方法方面的研讨,后半部侧重本体方面的研讨,此外书中还有大量的、有关汉语词语理据的实例。这些实例知识性强,而且大都十分富于情趣。比如“原来”本写作“元来”,因明代朱元璋推翻元朝以后,再说“元来”就有让元朝复辟、卷土重来之嫌,所以改“元”为“原”。“两个小时”中的“小时”何以称为“小”?书中告诉我们:我国古代用“日晷”、“铜壶滴漏”计时,将一昼夜分作十二个时辰。钟表传入我国后,逐步使用了新的计时制度。因为新制一个钟头相当于古代一个时辰的二分之一,于是把新制的一个钟头叫“小时”,而把旧制的一个时辰叫“大时”。再如,“桥牌”中的“桥”,我们都知道这是英语bridge的意译,但这种牌到底与“桥”有何关联,书中也十分生动地叙述了它的得名由来。
当然,探讨词语的理据有时相当困难,也可能引起一些争议。比如“熊猫”一词。许多人把这个词理解为“如熊之猫”。王艾录先生在《汉语理据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中指出这个词的理据是“体形若猫似熊”。本书里作者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50年代初期,重庆北碚博物馆首次展出这种动物时,标牌上横写着“猫熊”两个大字。参观者按照当时习惯,从右到左误读成“熊猫”。从此以讹传讹,“猫熊”就逐渐为“熊猫”所代替了。这个例子说明,探讨理据同不断深入挖掘语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一些理据不明或无法找到理据的词语,更需花费很多时间去搜索材料,进行分析或论证。
理据研究十分重要。除了我们开头部分提到的以外,它对语言规范化、对词典编纂、对确定某些词语的书写形式、甚至对研究文化与民俗,都很有助益。这在本书已有不少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有关两位作者的话。王艾录先生我过去并不认识,只是经常读到他的文章,觉得他视野开阔,勇于探索,所论颇多新意。我在给研究生授课时,也常常提到王艾录先生的观点,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司富珍是王先生的研究生,她的主攻方向是借鉴自组织理论研究汉语理据,并和她的导师一起撰写了这部专著。能在就读研究生期间作出这样的成绩,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果今后条件许可,我希望他们能进一步深化汉语理据问题的研究,继续撰写汉语句法理据的论著,以推动这方面研究的开展。
是为序。
1998年8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