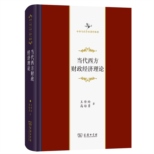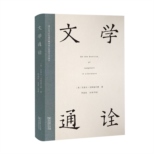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3><STRONG> 英 译 者 序
</STRONG></FONT>
一位学识渊博的法国物理教师对这门最精确的实验科学的逻辑和历史面貌以及教育状况作了生动的描述。本书就是为了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人而翻译的。而在此以前,他关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方面的名著还没有过任何英文译本。
迪昂曾在法国教授过经典力学、电磁理论和热力学,并且在他的许多自成体系的著作中对它们作了详细阐述,此外还作了大量的历史研究。本书写于1905年,那正是这些学科刚刚受到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冲击的时候。今天,在本书发表的在迪昂、马赫、彭加勒、哈达马德和其他科学家之间进行的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中,留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当时他们是用灵敏而宽大的哲学分析天平来权衡物理理论的整个目的和结构的。迪昂关于科学中深奥和基本问题的阐述是极其清楚的,对非物理学家来说,他所作的阐述要比他1916年逝世以后所出版的关于物理学理论的大多数专著更容易懂得多。
如果由于缺少关于一代代科学思想的基本连续性本身的历史知识(就像迪昂在书中大量告诉我们的那样),而认为所有的物理学原理都是短命的,就像关于“最终”粒子数的特定科学假说或最近关于宇宙论的假设那样,那就错了。
不可否认,在迪昂关于现代物理学中的革命性变化的哲学分析和历史考察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关于精确物理科学的逻辑结构和进展的研究中有所得益。就像一门语言的语法不如它的通俗方言变化得那么快一样,物理学逻辑的变化也不像实验发现以及让许多人相信的新理论的飞快进步那样彻底。
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当他们在专搞数学时如果没有离开他们对可观测物理世界的关心,他们就仍会发现有必要思考迪昂在本书所讨论和分析的许多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包括物理理论与形而上学解释的关系;假说、定律和理论在预言中的作用;模型和抽象假说的作用;可观测量与不可观测量的关系;数学演绎与实验验证的关系;测量的性质与理论的近似证实,假说的选择;以及“普通常识”与科学知识的关系等等。
迪昂对数学符号和数学演绎的作用以及实验在建立物理理论中的作用的分析,要比晚近的哲学分析家对逻辑句法和语义学问题的分析更为详细,因为不像迪昂的观点那样,认为逻辑句法和语义学与物理学的实验语言和实践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当然,对于他的观点将会有而且也应当有批评,但是,批评家必须使他自己的思想符合迪昂用来证实其解释的那些实验科学的具体现象以其历史发展相一致。这种对科学实践中的方法和假说的哲学思考,与历史考察相结合的做法,肯定能满足普通教育中哲学和科学教学研究的最高目的。
附录的内容是迪昂针对阿贝尔•雷伊的机械观而作的实用主义辩护,同时也说明了迪昂是如何把实证科学与形而上学和神学区分开来的。译者虽然不同意迪昂的天主教思想,但还是认为他为物理科学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所表明的独立性,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论据。
我非常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小约翰•欧文先生和其他成员非常有益的合作。我还要特别感谢法兰西科学院终身院士普林斯•路易斯•德布罗意先生的慷慨和及时的帮助,他为本书写了有趣的和非常有价值的前言。
菲利普•P.维纳
1953年于纽约
<STRONG><FONT size=3> 作者第二版序
</FONT></STRONG>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06年;它是把1904年和1905年陆续发表在《哲学杂志》上的文章汇集而成的。从那时起,一系列关于物理理论的争论又在哲学家中展开了,物理学家又提出了一些新理论。但这些讨论和这些新发现,都没有为我们显示任何理由要怀疑我们曾经阐述过的原则。相反,我们比以前更加坚信,这些原则应当坚持。的确,某些学派藐视这些原则,以为摆脱它们的限制就能够更容易和更快地从一个发现走向另一发现;但这股追逐新观念的狂热急流完全搅乱了整个物理理论领域,并导致一场真正的混乱:逻辑失去了它的地位,普通常识也被吓跑了。
因此,对我们来说,回顾一下逻辑的法则以及维护普通常识的权利似乎不无益处;重复一下大约十年前我们说过的话,对于我们也并非明显无用;所以,这第二版重版了第一版全书的内容。
如果说岁月的流逝没有提供任何理由使我们怀疑我们的原则,那么,时间又给了我们机会去发展这些原则并使它们精确化。这些机会导致我们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信教者的物理学”,它发表在《基督教哲学年鉴》上;另一篇是“物理理论的价值”,它刊登在《纯科学与应用科学评论》上。读者也许觉得,仔细阅读这两篇文章给本书所提供的澄清和补充多少是值得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版末尾把这两篇文章转载在附录中。
</STRONG></FONT>
一位学识渊博的法国物理教师对这门最精确的实验科学的逻辑和历史面貌以及教育状况作了生动的描述。本书就是为了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人而翻译的。而在此以前,他关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方面的名著还没有过任何英文译本。
迪昂曾在法国教授过经典力学、电磁理论和热力学,并且在他的许多自成体系的著作中对它们作了详细阐述,此外还作了大量的历史研究。本书写于1905年,那正是这些学科刚刚受到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冲击的时候。今天,在本书发表的在迪昂、马赫、彭加勒、哈达马德和其他科学家之间进行的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中,留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当时他们是用灵敏而宽大的哲学分析天平来权衡物理理论的整个目的和结构的。迪昂关于科学中深奥和基本问题的阐述是极其清楚的,对非物理学家来说,他所作的阐述要比他1916年逝世以后所出版的关于物理学理论的大多数专著更容易懂得多。
如果由于缺少关于一代代科学思想的基本连续性本身的历史知识(就像迪昂在书中大量告诉我们的那样),而认为所有的物理学原理都是短命的,就像关于“最终”粒子数的特定科学假说或最近关于宇宙论的假设那样,那就错了。
不可否认,在迪昂关于现代物理学中的革命性变化的哲学分析和历史考察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关于精确物理科学的逻辑结构和进展的研究中有所得益。就像一门语言的语法不如它的通俗方言变化得那么快一样,物理学逻辑的变化也不像实验发现以及让许多人相信的新理论的飞快进步那样彻底。
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当他们在专搞数学时如果没有离开他们对可观测物理世界的关心,他们就仍会发现有必要思考迪昂在本书所讨论和分析的许多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包括物理理论与形而上学解释的关系;假说、定律和理论在预言中的作用;模型和抽象假说的作用;可观测量与不可观测量的关系;数学演绎与实验验证的关系;测量的性质与理论的近似证实,假说的选择;以及“普通常识”与科学知识的关系等等。
迪昂对数学符号和数学演绎的作用以及实验在建立物理理论中的作用的分析,要比晚近的哲学分析家对逻辑句法和语义学问题的分析更为详细,因为不像迪昂的观点那样,认为逻辑句法和语义学与物理学的实验语言和实践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当然,对于他的观点将会有而且也应当有批评,但是,批评家必须使他自己的思想符合迪昂用来证实其解释的那些实验科学的具体现象以其历史发展相一致。这种对科学实践中的方法和假说的哲学思考,与历史考察相结合的做法,肯定能满足普通教育中哲学和科学教学研究的最高目的。
附录的内容是迪昂针对阿贝尔•雷伊的机械观而作的实用主义辩护,同时也说明了迪昂是如何把实证科学与形而上学和神学区分开来的。译者虽然不同意迪昂的天主教思想,但还是认为他为物理科学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所表明的独立性,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论据。
我非常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小约翰•欧文先生和其他成员非常有益的合作。我还要特别感谢法兰西科学院终身院士普林斯•路易斯•德布罗意先生的慷慨和及时的帮助,他为本书写了有趣的和非常有价值的前言。
菲利普•P.维纳
1953年于纽约
<STRONG><FONT size=3> 作者第二版序
</FONT></STRONG>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06年;它是把1904年和1905年陆续发表在《哲学杂志》上的文章汇集而成的。从那时起,一系列关于物理理论的争论又在哲学家中展开了,物理学家又提出了一些新理论。但这些讨论和这些新发现,都没有为我们显示任何理由要怀疑我们曾经阐述过的原则。相反,我们比以前更加坚信,这些原则应当坚持。的确,某些学派藐视这些原则,以为摆脱它们的限制就能够更容易和更快地从一个发现走向另一发现;但这股追逐新观念的狂热急流完全搅乱了整个物理理论领域,并导致一场真正的混乱:逻辑失去了它的地位,普通常识也被吓跑了。
因此,对我们来说,回顾一下逻辑的法则以及维护普通常识的权利似乎不无益处;重复一下大约十年前我们说过的话,对于我们也并非明显无用;所以,这第二版重版了第一版全书的内容。
如果说岁月的流逝没有提供任何理由使我们怀疑我们的原则,那么,时间又给了我们机会去发展这些原则并使它们精确化。这些机会导致我们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信教者的物理学”,它发表在《基督教哲学年鉴》上;另一篇是“物理理论的价值”,它刊登在《纯科学与应用科学评论》上。读者也许觉得,仔细阅读这两篇文章给本书所提供的澄清和补充多少是值得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版末尾把这两篇文章转载在附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