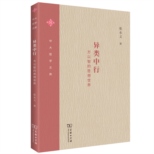显示全部后记
从特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去特殊的发达国家(德国)自费学习六年哲学,这句话听起来就很不妙,因为它的几乎每个成分都预示着无尽的辛酸和苦难。读者手上的这本伽达默尔《哲学生涯》中文版的一部分便是译者当时化解辛酸、消磨苦难留下的痕迹。学术圈的朋友劝我将余下部分也翻译出来,尽快让它与中国读者见面。看得出,很多人知道这本书.想看到这本书。这使我颇感犹豫。从许多方面讲我应该翻译它,这不仅因为它帮助过我,慰藉过我,而且它能帮助和慰藉更多中国读者,尤其从事真正的哲学和教育事业的人。有责任将它翻出来。但另一方面,潜心研习海德格尔、穿越海德格尔的思想文本是我自费去德国的惟一目标,我被海德格尔所吸引几近二十年。我喜欢海氏文本的磁性,喜欢海氏思想的纯粹、宁静与深沉,喜欢海氏语言的爆发力和解构力,喜欢海氏俯瞰整个思想山脉的山神之气,喜欢海氏跨越思想文本的自由力量,喜欢这位在思想上有千年价值的孤独者……。我视解读和翻译海氏著作为崇高事业,誓言只译海氏著作,此译务必达到德国美学文化固有的文本性。文本是思想的核心。近代中国在与西方学术遭遇的两百多年里,之所以没有出现世界意义上的真正思想家,之所以始终采取拿来主义(事实上拿是拿不来的),之所以有真理价值的东西扎不下根,从根本上说还是没有出现中西交融中自然形成的文本。没有独立又自然的文本就谈不上真正的思想,只能对西方花样翻新的“主义”反应式地亦步亦趋,以为新的就是好的、对的、深的,始终掌握不住思想的自在尺度,左右思想界的始终是思想之外的因素。翻译事业应该瞄准文本,以锤炼文本为目标。否则就容易沦为贩卖。在现代西方思想家中,真正有文本价值的大概只有海德格尔,从某种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是个例外。因此,我回到兰州大学哲学系之后,主要精力就集中在释读海氏文本的寂寞活动中,每年的海德格尔研讨班都是语言较量的战场,真正能经受住较量的人寥寥无几,但经受住考验的人将不可避免地走上真正思想的道路。我们这一代完不成文本使命,他们有可能完成,至少认识到这一使命能否完成是中国思想界的症结所在。当汉语与现代西方语言、现代西方语言与希腊语僵持不下时,思想疲惫、紧张而快乐,语言的对流层不时撒落几颗语滴,真少啊。海氏很喜欢讲赫拉克利特的冲突,是啊,不冲突露不出底线,不见底线怎么划界,划不出界限怎么思想,何谈界定?不去界定怎么讲真理?语言要有真正的对手,人也要有真正的对手(而不是敌手),在对峙中提高,伟大的对手必然珍视伟大的对峙,在伟大的对峙中必然熏陶出伟大的人。中西交融中的语言如何言说?必将在伟大的对峙中言说,相互逼出一身又一身的冷汗,语词才慢慢开始萌芽,一旦萌芽“一夜庭前绿遍”,文本则缓缓浮现,有了文本思想就扎下了根。因此,思想者必须保持住这种对峙,不让对峙的任何一方垮掉,这样才能达到海氏所说的语词如花。翻译大概就是思想本身的寥寥缓行吧?我想,这就是我喜欢翻译海氏著作的真正原因。翻译伽达默尔自然也有快乐,但无论如何不是文本分延的快乐,不是纯粹思想的快乐。也许读者会问,翻译伽达默尔为什么说了这么多海德格尔? 我的回答是:没有海德格尔就根本不存在读者现在读到的伽达默尔。其实何止伽达默尔一人,20世纪后半期活跃在世界上的许多重量级思想家,包括现在仍很活跃的一些思想家,在回顾自己思想的成长历程时,有几人能脱开海德格尔的干系?在西方,海德格尔出生前的思想世界和海德格尔出生后的思想世界迥然不同,而且是因海德格尔而不同。20世纪欧洲思想界,尤其是法德两国在评价一个学术新秀的分量时往往会或明或暗地问,他读过海德格尔没有?这不是盲从,而是思想的力量!伽达默尔在这本并不算厚的自传中,除去专写海德格尔一章外,另有27处提到海德格尔,几乎不论写谁都绕不开他。是啊,海德格尔这颗巨星突然升起,划过天空,在这缕强光的照射之下,已经做完博士论文的伽达默尔才发现,原来自已什么都没学到,居然连思想的皮毛都没碰着。他的博士头衔也不是随便混来的,是从当时世界思想中心(马堡的新康德主义学派)的中心人物那托尔普那里挣来的,用概念游戏的标准看也是货真价实的、一流的。他在新康德主义圈子里充满了学术自信,但在遭遇海德格尔真正的思想风暴后,不仅意识到白己要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做起,而且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经过痛苦怀疑的人一旦认定目标就把整个生命交给了这个目标。他有所成就并成为一代宗师启示我们:纯粹的思想需要纯粹的虔诚。我不认为伽达默尔的天分很高,可以说直到他读完博士他是既无天分又无虔诚。天分莫可奈何,天造地设,但虔诚是可人为的。他在虔诚中不仅走上了真正的思想道路,而且原本不算好的身体居然能长命百岁。
一个哲学家写自己的传记,其可读性与思想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解释学思想以及这种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内在关系我就不在这里仔细探讨了。懂海德格尔的人自然就知道伽达默尔的价值,读懂了伽达默尔也有助于理解某个层面中的海德格尔。我想,对中国读者来说,读这本传记的价值更在于对学术生态的认识。这不仅因为伽氏横跨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两大学派,而且有横跨两种社会制度(西德与东德)的经历,更重要的,他不仅是哲学家,而且当过不同社会制度中的校长和系主任,其中的酸甜苦辣尤耐人寻味。我在阅读和翻译这本传记时就一再想起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我们民族不乏天才,不乏悟性高的人,也不乏献身纯粹学术事业的人,但我们的学术生态不是为他们献身纯粹学术的“事物本身”创造条件,而是不谋而合地把他们拉到“事物本身”之外,扼杀他们,毁灭他们,让其在不断加剧的痛苦中放弃“事物本身”,被迫转入“事物本身”之外的价值标准。天才磨炼天才,伟人激励伟人。没有纯洁的学术生态怎能指望学术大师的出现?没有层出不穷的学术宗师何谈民族精神的自由创造?当今可有蔡元培、伽达默尔这样的校长?纵然有,当今中国的学术生态和政治生态能容忍蔡元培、伽达默尔这样的人当校长?他们能干得下去?我不喜欢下结论,想必这本传记中“莱比锡”、“法兰克福插曲”和“海德堡”部分有助于读者您寻求答案。从这个角度说,伽达默尔这本传记相对于哲学读者言更值得教育界的读者一读。
传记有不同的写法。我个人更喜欢“我生了,劳作了,死了”这种海德格尔式的传记。这是思想中生命最基本语汇最肃穆的显示,如伽达默尔在这本传记中引述诗人保罗•策兰对与海德格尔相遇的描述:
兰花与兰花
各自独语
……
烂木的路
走走停停
许多的潮湿
思者的路是独语的路,思者的对话也是“各自独语”的对话,这对话“走走停停”,充满了“潮湿”和泥泞。但伽达默尔的传记不是写给自己的,而是写给读者您的。他没有独语,而是希望与您恳谈,为自己的一生辩护,为他认为正确、有益的人或事辩护。既然是辩护,它的重心就不是简化自己、削弱自己、突出自己的缺陷,而是列举自己工作的重点、成绩的重点和成长的重点。这加深了我对自传的偏见,觉得传记还是由别人写好,尤其是思想家的传记。这本传记无疑对所有读者都有益处,但我相信,它对哲学家本人将是一个损失。不知读者是否也有同感。
本书的中文版沿用了德文版的目录结构。为了便于中文读者的阅读,我给德文大标题下的小标题加了序号。中文版中第一次出现的人名一般都在括号里标出原名,便于读者查阅相关文献,只有妇孺尽知的人除外,如黑格尔、马克思、荷马、康德等等。个别无关紧要的人没有标出原名,考虑到这些人没有多大的查阅价值。我尽可能给在其他领域很有名望但哲学界不太熟悉的人加一个译注,便于读者在阅读时能及时了解哲学与哲学以外事件的交叉。对翻译界已有惯例可循但又颇具歧义的哲学概念也尽力加上译注,如Mythos,Kehre,Person等等。伽达默尔写这本自传时已是七十五岁高龄,行文中经常出现引申句、突然的插入和突然的中断,一个高龄的哲学家写自传想必很难吧?大量复合句的使用就足以证明一个老人与语言战斗的辛苦。中译本试图使行文更加流畅,但译者水平有限,虽心有余而力不足。如获读者厚爱,指出中文版中的错漏之处,译者不胜感激,并择机改过。请读者允许译者在此事先表示谢意。
最后,感谢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劳心费神的朋友们。尤其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江怡教授、商务印书馆陈小文副主任。我想,如果伽达默尔得知该书有了中文版,他也会高兴并感谢上述几位先生。不过,惟恐他指责我没有使本书的中文版更臻完美。尊敬的伽达默尔教授,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以来的思想是美的,韵汉语是美的,我的翻译并没有满足两种不同的美的共同要求。这既有我的原因,也有语言自身的原因。我会更多地考虑我的原因。
2002年4月3日
于兰州大学古草园
译者补记:
就在译者拟向出版社交稿之际,从德国友人处得知,伽达默尔教授在宁静地度过他102岁生日后,于今年3月仙逝。原木想送给这位世纪老人一份礼物,转瞬间已是一种纪念。德意志这个民族的幸与不幸均在于它视精神为实体,德意志民族的这一特性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伽达默尔无疑是20世纪德意志精神实体的塑造者之一。我曾说过,德国人骨子里都是漫游者。伽达默尔在世上漫游了一个世纪,牵住了两个世纪的手。他的去世也自然是世纪的损失,他给世人留下的不只是生命的句号,还有解释学的问号、思想壮观的感叹号和一切有关意义的省略号。祝福他能继续在天堂幸福地漫游。
伽达默尔是思者。对这位刚刚告别我们的世纪思者,还有比学会思想更好的纪念吗?但愿我们都以学会思想的方式纪念他。
2002年4月6日
于古草园
一个哲学家写自己的传记,其可读性与思想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解释学思想以及这种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内在关系我就不在这里仔细探讨了。懂海德格尔的人自然就知道伽达默尔的价值,读懂了伽达默尔也有助于理解某个层面中的海德格尔。我想,对中国读者来说,读这本传记的价值更在于对学术生态的认识。这不仅因为伽氏横跨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两大学派,而且有横跨两种社会制度(西德与东德)的经历,更重要的,他不仅是哲学家,而且当过不同社会制度中的校长和系主任,其中的酸甜苦辣尤耐人寻味。我在阅读和翻译这本传记时就一再想起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我们民族不乏天才,不乏悟性高的人,也不乏献身纯粹学术事业的人,但我们的学术生态不是为他们献身纯粹学术的“事物本身”创造条件,而是不谋而合地把他们拉到“事物本身”之外,扼杀他们,毁灭他们,让其在不断加剧的痛苦中放弃“事物本身”,被迫转入“事物本身”之外的价值标准。天才磨炼天才,伟人激励伟人。没有纯洁的学术生态怎能指望学术大师的出现?没有层出不穷的学术宗师何谈民族精神的自由创造?当今可有蔡元培、伽达默尔这样的校长?纵然有,当今中国的学术生态和政治生态能容忍蔡元培、伽达默尔这样的人当校长?他们能干得下去?我不喜欢下结论,想必这本传记中“莱比锡”、“法兰克福插曲”和“海德堡”部分有助于读者您寻求答案。从这个角度说,伽达默尔这本传记相对于哲学读者言更值得教育界的读者一读。
传记有不同的写法。我个人更喜欢“我生了,劳作了,死了”这种海德格尔式的传记。这是思想中生命最基本语汇最肃穆的显示,如伽达默尔在这本传记中引述诗人保罗•策兰对与海德格尔相遇的描述:
兰花与兰花
各自独语
……
烂木的路
走走停停
许多的潮湿
思者的路是独语的路,思者的对话也是“各自独语”的对话,这对话“走走停停”,充满了“潮湿”和泥泞。但伽达默尔的传记不是写给自己的,而是写给读者您的。他没有独语,而是希望与您恳谈,为自己的一生辩护,为他认为正确、有益的人或事辩护。既然是辩护,它的重心就不是简化自己、削弱自己、突出自己的缺陷,而是列举自己工作的重点、成绩的重点和成长的重点。这加深了我对自传的偏见,觉得传记还是由别人写好,尤其是思想家的传记。这本传记无疑对所有读者都有益处,但我相信,它对哲学家本人将是一个损失。不知读者是否也有同感。
本书的中文版沿用了德文版的目录结构。为了便于中文读者的阅读,我给德文大标题下的小标题加了序号。中文版中第一次出现的人名一般都在括号里标出原名,便于读者查阅相关文献,只有妇孺尽知的人除外,如黑格尔、马克思、荷马、康德等等。个别无关紧要的人没有标出原名,考虑到这些人没有多大的查阅价值。我尽可能给在其他领域很有名望但哲学界不太熟悉的人加一个译注,便于读者在阅读时能及时了解哲学与哲学以外事件的交叉。对翻译界已有惯例可循但又颇具歧义的哲学概念也尽力加上译注,如Mythos,Kehre,Person等等。伽达默尔写这本自传时已是七十五岁高龄,行文中经常出现引申句、突然的插入和突然的中断,一个高龄的哲学家写自传想必很难吧?大量复合句的使用就足以证明一个老人与语言战斗的辛苦。中译本试图使行文更加流畅,但译者水平有限,虽心有余而力不足。如获读者厚爱,指出中文版中的错漏之处,译者不胜感激,并择机改过。请读者允许译者在此事先表示谢意。
最后,感谢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劳心费神的朋友们。尤其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江怡教授、商务印书馆陈小文副主任。我想,如果伽达默尔得知该书有了中文版,他也会高兴并感谢上述几位先生。不过,惟恐他指责我没有使本书的中文版更臻完美。尊敬的伽达默尔教授,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以来的思想是美的,韵汉语是美的,我的翻译并没有满足两种不同的美的共同要求。这既有我的原因,也有语言自身的原因。我会更多地考虑我的原因。
2002年4月3日
于兰州大学古草园
译者补记:
就在译者拟向出版社交稿之际,从德国友人处得知,伽达默尔教授在宁静地度过他102岁生日后,于今年3月仙逝。原木想送给这位世纪老人一份礼物,转瞬间已是一种纪念。德意志这个民族的幸与不幸均在于它视精神为实体,德意志民族的这一特性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伽达默尔无疑是20世纪德意志精神实体的塑造者之一。我曾说过,德国人骨子里都是漫游者。伽达默尔在世上漫游了一个世纪,牵住了两个世纪的手。他的去世也自然是世纪的损失,他给世人留下的不只是生命的句号,还有解释学的问号、思想壮观的感叹号和一切有关意义的省略号。祝福他能继续在天堂幸福地漫游。
伽达默尔是思者。对这位刚刚告别我们的世纪思者,还有比学会思想更好的纪念吗?但愿我们都以学会思想的方式纪念他。
2002年4月6日
于古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