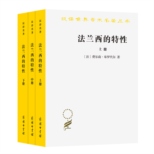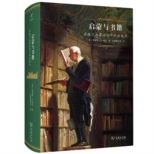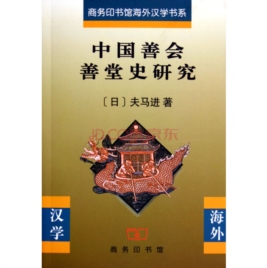显示全部序言
中 文 版 序 言
在本书的日文版出版之后不久,曾经有过数次欲将本书译成中文出版的计划,其间还有过不少与翻译出版有关的传闻。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传闻”是,中国国务院下属民政部(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负责人曾经推荐将本书译成中文出版。当然,我个人无法判断这一“传闻”是否属实。不过在当代中国,对于社会福利问题的关心前所未有地高涨,所以我觉得上述“传闻”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本书是区别于论述当代中国的一般读物,属于历史研究的专门性著作。例如,在对本书内容的理解方面,仅仅依靠通晓日语是远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关于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而且,本书在日本出版发行的中国历史研究的专著中属于分量最大者之一,仅以页数而论已经超过一般专著的一倍以上。内容较为专门,除了一般叙述之外,更多的是关于具体历史事实的描述。坦白地说,我曾经很担心能否有人胜任如此困难重重的专著翻译工作。
由于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的提议,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被正式提上日程。中文翻译分别由伍跃教授(大阪经挤法科大学)、杨文信博士(香港大学)、张学锋教授(南京大学)三人担任。这三位翻译者不仅具有很好的研究和日语能力,而且他们在京都大学学习期间都曾经听过我讲授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在他们之外很难再找到如此合适的翻译者。因此,我立即同意了范金民教授的建议,翻译工作随之全面展开。
如同本书“后记”中所说,我本人开始这项研究是在1979年或1980年初,首次发表有关论文则是在1982年。那时,无论在哪里都根本无人提到“善会、善堂”。这种情况激发了我研究这一问题的兴趣,而且我当时预计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恐怕最快还要等上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地球实在是太狭小了。直到1988年,我才知道美国的韩德琳(Joanna Handlin Smith)博士于1987年发表了关于明末同善会的研究论文,而台湾的梁其姿教授则早在1984年就发表论文,讨论江南地区育婴堂在清代初年诞生的问题。梁其姿教授原是在香港和法国专攻历史学并从事研究活动的,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上述三人都可以称为在“中国”(中国大陆)以外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者。据我所知,“中国”(中国大陆)学者正式开始考察善会、善堂问题的当属陈宝良教授(1996年)。此外,在日本广岛大学留学的王卫平教授(苏州大学)提交了包括有善会善堂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是在1997年。在今天的日本,比我年轻的小浜正子教授(鸣门教育大学)和吉泽诚一郎教授(东京大学)等新一代的研究者们将善堂问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进行着深入的研究。现今的研究状况与根本听不到“善会、善堂”的1980年前后相比,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本书的“序论”中,我曾经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美国的中国史学会将善会、善堂问题作为与哈贝马斯(J.Habarmas)所提出的“市民的公共性”,即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等问题相关的重要问题,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在本书的“后记”中,我也提到过这一研究的动机,其一是对中国前近代地方自治萌芽问题的关心,另一个则是对中国早期社会福利史问题的关心。但是,我最初阅读哈贝马斯所著《公共性的构造转换》(细谷贞雄译,东京,未来社,1973年)的时候,恰恰是我刚刚开始本研究的前后。我之所以能记住这一时间是由于以下原因。因为告诉我这本书的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野村雅一教授,他于1979年4月至1982年3月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持了共同研究班,而我本人正好参加了这一研究班。在当时只有中国史研究者们聚集的研究会上,根本不会提到哈贝马斯的名字。我被该书中所论述的“市民的公共性”所吸引,立即感到可以将这一理论和我当时刚刚开始着手的善会、善堂史研究结合在一起。不过,我在研究中没有将哈贝马斯的观点置于主要的地位。其原因之一是我对哈贝马斯的观点尚不能全部理解,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公共领域”和“市民的公共性”这一模式原产于欧洲,在这一点上与“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如果采用在中国前近代中寻找“公共领域”和“市民的公共性”模式的研究方法的话,最终无疑会与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方法一样,走入死胡同。
1989年至1990年,我作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获得了赴美研究的机会。当时,我了解到美国的中国史学界正在进行着可以称为“寻找公共领域”的研究。本书中介绍的玛丽•兰钦(Mary B.Rankin)教授、罗威廉(William T.Rowe)教授的著作也正是我在赴美期间阅读的。至今我还记得,1990年4月,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亚洲学会(AAS)的年会上,首次见到来自霍普金斯大学的罗威廉教授,并在一起讨论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的情景。那时,罗威廉教授亲手给我即将在《近代中国》(<EM>Modern China</EM>)第16卷第3期(1990年)上发表的新作——《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而且,我当时还了解到1962年用德文首次出版的哈贝马斯的著作直到1989年才有英译本问世,罗威廉教授就是在该书英译本出版的刺激之下发表上述论文的。相比之下,哈贝马斯该书日文译本的出版远早于英译本问世的1973年,这一点反映了日本社会学界的特异性。罗威廉教授的上述论文不仅给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们以很大的刺激,也大大地影响到中国的学者们。1992年5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振常教授将他于1991年12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一文亲手给我,该文就是以罗威廉教授的上述论文为前提论述近代上海的。根据我的印象,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开始讨论“公共领域”问题,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从本书的日文版问世至今已经过去5年多了。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出现了很多与本书有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但是我想尚无必要对本书的基本观点进行修订,除了表达上的个别问题之外,中文版中做了较大修改的只有第八章的注释(51)(本书页437)。其原因请参见该条注释及其所引拙稿。此外,中文版还新增了征引书目。
以下两点是在日文版执笔时如果知道的话必定会写入的内容。
其一是关于蔡元培所著《清节堂记》。曾经声援过“五四”运动的思想家蔡元培和他所撰写的《清节堂记》,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曾感到这两者之间并不吻合。我甚至怀疑过该文是否果真是蔡元培所撰,并曾经设想该文写于清末,而且是胸襟恢宏的蔡元培受故乡绍兴府的熟人所托、不情愿地为嵊县清节堂撰写的。在本书出版之后,我读到了蔡建国教授所著《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得知蔡元培撰写《清节堂记》至少是因为存在着他无法回绝的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他在11岁丧父之后,是慈母历尽千辛万苦将他抚育成人,而且还因为他受到了慈母的深刻影响。我在阅读蔡建国教授的著作时,脑海中几乎完好无缺地重叠着蔡元培和他母亲以及在上百年前构想了贞苦堂(清节堂)的考据学者汪中和他母亲的身影。倘若我在执笔以前稍微留意一下幼年时期的蔡元培,肯定会在叙述汪中的贞苦堂构想时提到蔡元培。
其二是关于史料的问题。本书第一章第二节曾经提到,根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题本户科赈济类的史料,与养济院有关的记载始见于雍正十三年(1735)。这一点基本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当时我没有考虑到康熙年间及其前后的有关史料在编纂《乾隆大清会典》之前可能已经散佚。顾及这一点是因为两年前,我在阅读中朝关系史史料时得知,负责清朝对外事务的官僚们常常引以为据的档案在乾隆年间已经散失。如果确实存在着养济院档案散失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就会在第一章第二节叙述这一情况,而且倘若今后发现了有关的档案史料的话,就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增订。
现在,在中国清代史和民国史的研究中,档案史料的发掘与利用都在积极地展开。今后,在善会、善堂史的研究上将会更多地利用档案史料。本书在善会、善堂史研究方面,仅仅是根据各种《征信录》、《申报》和文集随笔等史料描述了善会和善堂的轮廓。随着新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利用,本书在将来也许有必要做大幅度的修订。但是,对于著者来说还有比这更值得高兴的吗?
在本书的执笔以及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海外学者的帮助。除了上述从事与善会善堂有关的研究的各位先生之外,特向丁义忠先生、居蜜先生、任道斌先生、王鹤鸣先生、朱金甫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并谨向提议将本书译成中文的范金民先生以及从事了这一困难的翻译工作的伍跃先生、杨文信先生和张学锋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夫马进
2002年4月7日,时逢54岁生日
在本书的日文版出版之后不久,曾经有过数次欲将本书译成中文出版的计划,其间还有过不少与翻译出版有关的传闻。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传闻”是,中国国务院下属民政部(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负责人曾经推荐将本书译成中文出版。当然,我个人无法判断这一“传闻”是否属实。不过在当代中国,对于社会福利问题的关心前所未有地高涨,所以我觉得上述“传闻”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本书是区别于论述当代中国的一般读物,属于历史研究的专门性著作。例如,在对本书内容的理解方面,仅仅依靠通晓日语是远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关于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而且,本书在日本出版发行的中国历史研究的专著中属于分量最大者之一,仅以页数而论已经超过一般专著的一倍以上。内容较为专门,除了一般叙述之外,更多的是关于具体历史事实的描述。坦白地说,我曾经很担心能否有人胜任如此困难重重的专著翻译工作。
由于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的提议,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被正式提上日程。中文翻译分别由伍跃教授(大阪经挤法科大学)、杨文信博士(香港大学)、张学锋教授(南京大学)三人担任。这三位翻译者不仅具有很好的研究和日语能力,而且他们在京都大学学习期间都曾经听过我讲授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在他们之外很难再找到如此合适的翻译者。因此,我立即同意了范金民教授的建议,翻译工作随之全面展开。
如同本书“后记”中所说,我本人开始这项研究是在1979年或1980年初,首次发表有关论文则是在1982年。那时,无论在哪里都根本无人提到“善会、善堂”。这种情况激发了我研究这一问题的兴趣,而且我当时预计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恐怕最快还要等上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地球实在是太狭小了。直到1988年,我才知道美国的韩德琳(Joanna Handlin Smith)博士于1987年发表了关于明末同善会的研究论文,而台湾的梁其姿教授则早在1984年就发表论文,讨论江南地区育婴堂在清代初年诞生的问题。梁其姿教授原是在香港和法国专攻历史学并从事研究活动的,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上述三人都可以称为在“中国”(中国大陆)以外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者。据我所知,“中国”(中国大陆)学者正式开始考察善会、善堂问题的当属陈宝良教授(1996年)。此外,在日本广岛大学留学的王卫平教授(苏州大学)提交了包括有善会善堂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是在1997年。在今天的日本,比我年轻的小浜正子教授(鸣门教育大学)和吉泽诚一郎教授(东京大学)等新一代的研究者们将善堂问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进行着深入的研究。现今的研究状况与根本听不到“善会、善堂”的1980年前后相比,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本书的“序论”中,我曾经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美国的中国史学会将善会、善堂问题作为与哈贝马斯(J.Habarmas)所提出的“市民的公共性”,即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等问题相关的重要问题,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在本书的“后记”中,我也提到过这一研究的动机,其一是对中国前近代地方自治萌芽问题的关心,另一个则是对中国早期社会福利史问题的关心。但是,我最初阅读哈贝马斯所著《公共性的构造转换》(细谷贞雄译,东京,未来社,1973年)的时候,恰恰是我刚刚开始本研究的前后。我之所以能记住这一时间是由于以下原因。因为告诉我这本书的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野村雅一教授,他于1979年4月至1982年3月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持了共同研究班,而我本人正好参加了这一研究班。在当时只有中国史研究者们聚集的研究会上,根本不会提到哈贝马斯的名字。我被该书中所论述的“市民的公共性”所吸引,立即感到可以将这一理论和我当时刚刚开始着手的善会、善堂史研究结合在一起。不过,我在研究中没有将哈贝马斯的观点置于主要的地位。其原因之一是我对哈贝马斯的观点尚不能全部理解,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公共领域”和“市民的公共性”这一模式原产于欧洲,在这一点上与“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如果采用在中国前近代中寻找“公共领域”和“市民的公共性”模式的研究方法的话,最终无疑会与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方法一样,走入死胡同。
1989年至1990年,我作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获得了赴美研究的机会。当时,我了解到美国的中国史学界正在进行着可以称为“寻找公共领域”的研究。本书中介绍的玛丽•兰钦(Mary B.Rankin)教授、罗威廉(William T.Rowe)教授的著作也正是我在赴美期间阅读的。至今我还记得,1990年4月,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亚洲学会(AAS)的年会上,首次见到来自霍普金斯大学的罗威廉教授,并在一起讨论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的情景。那时,罗威廉教授亲手给我即将在《近代中国》(<EM>Modern China</EM>)第16卷第3期(1990年)上发表的新作——《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而且,我当时还了解到1962年用德文首次出版的哈贝马斯的著作直到1989年才有英译本问世,罗威廉教授就是在该书英译本出版的刺激之下发表上述论文的。相比之下,哈贝马斯该书日文译本的出版远早于英译本问世的1973年,这一点反映了日本社会学界的特异性。罗威廉教授的上述论文不仅给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们以很大的刺激,也大大地影响到中国的学者们。1992年5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振常教授将他于1991年12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一文亲手给我,该文就是以罗威廉教授的上述论文为前提论述近代上海的。根据我的印象,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开始讨论“公共领域”问题,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从本书的日文版问世至今已经过去5年多了。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出现了很多与本书有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但是我想尚无必要对本书的基本观点进行修订,除了表达上的个别问题之外,中文版中做了较大修改的只有第八章的注释(51)(本书页437)。其原因请参见该条注释及其所引拙稿。此外,中文版还新增了征引书目。
以下两点是在日文版执笔时如果知道的话必定会写入的内容。
其一是关于蔡元培所著《清节堂记》。曾经声援过“五四”运动的思想家蔡元培和他所撰写的《清节堂记》,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曾感到这两者之间并不吻合。我甚至怀疑过该文是否果真是蔡元培所撰,并曾经设想该文写于清末,而且是胸襟恢宏的蔡元培受故乡绍兴府的熟人所托、不情愿地为嵊县清节堂撰写的。在本书出版之后,我读到了蔡建国教授所著《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得知蔡元培撰写《清节堂记》至少是因为存在着他无法回绝的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他在11岁丧父之后,是慈母历尽千辛万苦将他抚育成人,而且还因为他受到了慈母的深刻影响。我在阅读蔡建国教授的著作时,脑海中几乎完好无缺地重叠着蔡元培和他母亲以及在上百年前构想了贞苦堂(清节堂)的考据学者汪中和他母亲的身影。倘若我在执笔以前稍微留意一下幼年时期的蔡元培,肯定会在叙述汪中的贞苦堂构想时提到蔡元培。
其二是关于史料的问题。本书第一章第二节曾经提到,根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题本户科赈济类的史料,与养济院有关的记载始见于雍正十三年(1735)。这一点基本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当时我没有考虑到康熙年间及其前后的有关史料在编纂《乾隆大清会典》之前可能已经散佚。顾及这一点是因为两年前,我在阅读中朝关系史史料时得知,负责清朝对外事务的官僚们常常引以为据的档案在乾隆年间已经散失。如果确实存在着养济院档案散失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就会在第一章第二节叙述这一情况,而且倘若今后发现了有关的档案史料的话,就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增订。
现在,在中国清代史和民国史的研究中,档案史料的发掘与利用都在积极地展开。今后,在善会、善堂史的研究上将会更多地利用档案史料。本书在善会、善堂史研究方面,仅仅是根据各种《征信录》、《申报》和文集随笔等史料描述了善会和善堂的轮廓。随着新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利用,本书在将来也许有必要做大幅度的修订。但是,对于著者来说还有比这更值得高兴的吗?
在本书的执笔以及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海外学者的帮助。除了上述从事与善会善堂有关的研究的各位先生之外,特向丁义忠先生、居蜜先生、任道斌先生、王鹤鸣先生、朱金甫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并谨向提议将本书译成中文的范金民先生以及从事了这一困难的翻译工作的伍跃先生、杨文信先生和张学锋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夫马进
2002年4月7日,时逢54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