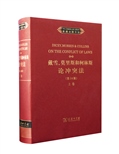显示全部后记
译后记
这几天,雅典正在开奥运会。一场全人类身体竞技的狂欢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奥林匹克回到雅典,这当然是回到了一个圆的原点,人类有足够的理由狂欢。
谈人类,自然要有一个类的尺度,这样才能把人统起来。这个类的尺度是从希腊人那里来的,是从希腊人的哲学中来的。哲学说希腊话,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无论是演绎还是递归,都要遵循种加属差的逻辑。这是哲学的源头,也是科学的源头,希腊人把科学(物理)和哲学(后物理)一并提出的奥秘就在这里。统合在希腊哲学尺度中的人才有了共同的类的概念,而随着希腊哲学在近代欧洲的复兴和放大,出现了以近代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以及西方文明的全球化,并在接受了以希腊哲学为母体的“人类”概念的情况下,对地球上其他精神存在的方式和价值体系构成了挑战,在这种挑战和冲突中有了种种刺耳的说法,如“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等。这些说词产生于人种的比较中,产生于文化单元的比较中,不管在这些比较中生产出多少差异,它们仍然是“人”与人的游戏方式。而在“人”与非人的游戏中也生产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说法。
“人类中心主义”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自然人意义上的人与非人的关系。如人与动物、植物、资源、能源的关系,把人置于目的的位置,人是其他动物的目的,人是其他植物的目的,人是一切资源和能源的目的,不仅限于地球,而且包括了地球以外的资源和能源。月球探测,火星探测,水星探测……这都是人类生存目的的延伸。人类有了保护动物、植物的意识,有了生物链和生态环境的意识,有了地球家园的意识,这些意识仍是服从于人类生存永续的目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第二层意思是按地球人的尺度在无限的太空中复制人,寻觅地球人的影子。随着地球村概念的形成,地球上的人作为一个类已无实质差异,早已类化于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等一系列的科学网格中,并形成了人类学的共同话语模式,说到底,人类、人类学作为一个类和类化的解释方式,是基于共同的希腊哲学公约出来的人认知自己的能力和方式。人已经失去了发现新大陆时的奇异的陌生力量,在共同的解释系统和话语方式中,人已经完全同质化了,不仅异国情调褪色了,而且诸种基于历史积淀的神秘感也黯然失色。地球上已经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可以停泊“人类”的寄托。地球上的“人类”与“人类”栖居的地球同样孤单,一样的无依无靠,同样裸露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在科学的暗指中,地球以及地球负载的人类不过是太空中的一粒尘埃而已。孤单制造着孤单的人,孤单的人寻觅孤单的人,本意是分享孤单,而实际上却在倍增着孤单。人类开始把目光指向地球之外,在地球之外任何可能的地点(依我们共同的希腊哲学和科学的指引)寻找我们的同伴,可伴我们的同类。老虎伴人,人虎各有其怕,蛇狗相伴,也各有其怕,不同类就不可同伴,纵然猫狗可以伴人,也是各有各的世界,各有各的期许,猫狗不能人事,人也不能行猫狗之事。人还得找“人”,不论怎样的滑稽,人怎么可能走出自己的世界呢?即便人有可能走出“人”,又怎么可能走出人呢?我们在地球之外能寻觅的,要么是理论上的人”,要么是见证意义上的人,除此,即便出现比人还人的人,我们也是视而不见的。一波又一波的UF0浪潮不是已让我们足够的眩目了吗?我们的演技不是已足够的笨手笨脚了吗?不论是“人”还是人,我们(我们?)能寻找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能见证的还是我们自己。我偶尔在想,一个在平面中爬行的虫子何以能见证人的世界?一个据说只生活在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中的人何以能够见证这些维度之外的世界呢?
“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的无奈。虫子信赖“虫子主义”,细菌信赖“细菌主义”,这都无可厚非,各有各的无奈。但用虫子的眼光找细菌,或用细菌的眼光找虫子,就会衍生一系列能不能、该不该的问题。而评判能不能、该不该的还是人。人总归不能设身到虫子和细菌的世界,按理说没有评判的资格,但人可以举取一箩筐非评判不可的理由,而且听上去还委屈得不得了,并且还是一些在人看来无比崇高的理由。其实,人并没有理解虫子或细菌的世界,人做的只是依据自己的理由让什么样的虫子和细菌存在,什么样的不能存在,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等等。这实际上都是人的世界的延伸,不管是人的生存世界,还是人的价值世界。我们被自己的世界紧紧地禁锢着。他人有可能是自己的天堂,但自己绝对是自己的地狱。即便是开满鲜花的地狱,可仍然还是地狱,被无岸的边界锁闭着的地狱。
各个地狱都紧紧地把守着自己的门。利益之门,价值之门,好恶之门,权势之门,性情之门,语言之门和生死之门,这些门狭窄而龌龊,阴暗且潮湿,隐藏着诸多机关,门的多少也许可以无穷列举,但门的定义从根本上说不是敞开和开放,而是锁闭,随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每个人在自己的门前都一样,守望多于遥望。谁都在自己的守望中渲染神圣和不可替代,谁都在为这种神圣和不可替代寻找更神圣和更不可替代的理由。如此一来,我们的世界更加密不透风,我们的门更加紧闭,我们的边际更加擦磨拥挤,我们的爱和恨更加悬浮诡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索拉里斯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遥望的天窗。
什么是小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什么是艺术?艺术是创作在语言中的超越?是什么在创作?是什么在语言中超越?如此一问,莱姆的《索拉里斯星》一书是不是小说似乎已是问题。莱姆学过哲学,学过控制论,学过心理学,也学过什么不伦不类的科学方法论。在他的写作中,这些表面上的学习背景都能找到一些痕迹。《索拉里斯星》这本书既不是通常的小说,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更不是科学一科幻著作,很难界定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也许应该视其为一本天书吧。它的可读之处也许就在于它是一本天书,因为只有天书才能浑然开释人为的痕迹,才能解开人类的类结,才能抛开文学的一般流程,才能避开以“光秃秃的数学”为基本言说方式的科学的桎梏,才能总揽人类作为类的种种形迹和问题。《索拉里斯星》的言说者凯尔文带着地球的问题和托付奔向索拉里斯星球,他和其他去索拉里斯的科学家一样,是为了去那里实现地球人的心愿的,是去寻找人类的同伴的,不管这个同伴在心智水平和生命等级上比地球人高还是低,总归是以地球人的“人”的尺度来衡量的。但当他到达索拉里斯时,在经历一系列地球人的惯常作派和定势思维的挫折后,他才渐渐明白,在索拉里斯面前,地球人简直就是哑巴和傻瓜,一窍不通,根本就不得要领。地球人惯有的征服者面孔变得幼稚可笑,威胁者不断受到威胁的病态感觉像心理魔幻师一样捉摸不定,无所适从。征服索拉里斯,破译索拉里斯的生命信息,带着征服者装满战利品的行囊光荣地返回地球,燃起人类征服整个宇宙的雄心壮志,这是凯尔文及其他科考队员的初衷。但在经历了索拉里斯无穷尽的幻生幻灭之后,地球已经不可能是他们的家园,而是他们的伤心地,是屡生绝望的牢狱,是包藏着无尽的是非之地。地球人的征服欲,征服者的血腥必然带来的自身恐惧反被索拉里斯无尽的单纯所消弭,在索拉里斯无法用地球人语言理解的单纯中,地球成了极不单纯的地方,令人恐惧的地方,原本的家园变成记忆中的牢狱,聚集着各种狭隘、傲慢、怨恨和自以为是的牢狱。画地为牢的地球人不仅偏执狭隘,而且极度自我膨胀,故作神圣,自以为是宇宙之精灵,而且还炮制出各种神来伪善自己,抬高自己的身价。凯尔文在经历了索拉里斯的洗脑之后才终于有能力在神的话语中澄清自己,剥去地球人造神的伪善,他这时才发现,真正的神,唯一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不需要为它的苦痛去赎罪,不拯救任何东西,谁也不效忠,它只是存在着。只存在着,没有意义,没有理由,没有为什么,存在着的中性力量抵御和消解一切人为的侵袭和剥蚀。神存在,别无其他,这是神保障人无罪的唯一途径。地球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无法听任神的存在不受侵扰,作为授神者的地球人不可避免地为种种罪迹所缠身。地球已注定是回不去的地方。家园消逝了,消逝在索拉里斯大洋变幻不定的地平线的交错往复中,地球以及地球所负载的地球人的一切已融合在索拉里斯大洋的永恒的无时间的律动中。
每一个记忆和回忆的瞬间都能产生生命形体,生命完全成了幻生幻灭的东西,这充满恐惧和绚烂的一幕幕在索拉里斯上实现了。我相信它是真的。其实也无所谓真不真,我信,这就足够了。其实也无所谓我不我,随着幻生幻灭的大洋波浪漂浮就足够了。随记忆而出现,再忆再出现,这还不够美妙吗?在没有时间的永恒里,记忆、回忆也已是无限的,无限的重复,无所谓生与死,这不就是地球人在美学上期待的瞬间化作永恒吗?在地球上、在科学上实属奢望的记忆符号在索拉里斯上实现了,这不是妙不可言吗?还能期待什么呢?凯尔文在索拉里斯大洋的惠顾下,在无时间的永恒中,实现了他与海若(大洋版的阿芙罗狄特)若即若离的中性拥有,这不是超出一切情爱、性爱、爱情和友情的神性之诗吗?地球人可曾敢奢望过?
作者是地球人,译者是地球人,读者您想必也是地球人,我们谁都无法摆脱地球的束缚。作者带着地球的局限写作,译者也在地球的层层桎梏中翻译,但作者和译者都希望您在读这本书时,能创造自由的阅读空间,能在思想上抵消地球引力和文化惰性对您的约束。能够生长自由的阅读无疑是美妙的,但自由的参照系在哪里?在地球?在人类?在索拉里斯?在大洋?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答案,解释自由的语言力量源于读者心灵自由的创造,无论作者还是译者都无权侵犯读者自由解释的权利。但译者也许可以代表作者对读者只提几个问题:您有过话语解放的冲动吗?您有过人类自我超越的挣扎吗?您在地球云层的包围下,在琐屑的社会事务、生存事务的日常纠缠中,有过眺望无际星空的冲动吗?您在聆听地球人关于地球人的价值体系、信仰体系、政治经济体系的高谈阔论时,心头曾闪过一丝的悲凉吗?您在目睹和经受了地球人生生死死的欢欣与悲哀时,曾经萌生过解脱缠绵红尘的郁闷吗?那您就读这本书吧。我不知道这本书出了多少波兰文版和英文版,但德文版自从1983年出了第一版后,到2001年已出了16版,几乎每年再版一次。想必这个数字已透露出这本小说的阅读魅力。
眼下,地球上的人类正忙于星际探测和太空旅行,这些活动当然都是服务于地球人生存目标的,不管这种生存目标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或者国际的、人类的。也许您就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一个科学主义者、一个异教徒……,不论您属于哪一种,在陌生的语言森林中进行一次小小的郊游,总是一件快意的事,哪怕是为了寻找心仪的猎物也值得您花上一点时间,毕竟,这里的猎物与您常识中的猎物有所不同。
这是一本天书。商务印书馆的朋友盛意托付,授我译它。我不知天高地厚,虽有迟疑,还是应了下来。一叶知秋,没译几页,就知道自己领了苦差事,呕心沥血、连滚带爬地译完之后,自己仿佛害了一场大病,苦不堪言。翻译苦,这一点人所共知。但翻译《索拉里斯星》这种书何其苦也,恐怕并无几人晓得。作者是用波兰文写作的,我从德文译,是经过翻译的作品,是再加工过的,我很少读过这么别扭的德文,想必波兰文的原作品不会如此别扭。当然,我也能体会德译者的艰辛,同样的呕心沥血、连滚带爬,知人苦者最苦。在对比《索拉里斯星》的德文版和英文版时,心里暗自嘀咕,文学翻译的差异居然可以如此悬殊,长了一些见识。相比之下,德译者似乎在字面上更忠实于原文,而英译者则遵循了意译的原则,删减幅度较大,有些再创作的味道,据商务印书馆的朋友说,原作者希望依据德文版翻译成中文本,想必作者有自己的评判,我倒觉得,德译、英译各有千秋。我依照的是德文本,虽也参考了英译,毕竟风格上还要跟着德文走,这就苦上加苦了。
据友人说,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几经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我并不感到惊异。就其写作视角的独特性和对虚拟世界预言家般的敏锐来说,无论是获诺贝尔奖提名还是最终获得诺贝尔奖,均属实至名归。但对一个试图向人类语言本身发起挑战的作家来说,诺贝尔奖真的能成为评判他的尺度吗?
作者自己也备尝了写作的艰辛。在小说中,作者自己声明,他也是用地球语言强说其所不能说,语言的缺斤短两、词不达意之处甚多。这让译者颇感为难,译者的译者就更加死去活来了。凭鄙人的这点耐心根本就完不成这个任务,幸有夫人相助,她不仅在文字技术上为我提供帮助,而且每逢疑惑处都掌灯相磋。更重要的是,每当我被《索拉里斯星》折磨得意志消沉、声言放弃时,夫人都及时鞭策鼓励,这才在万般艰难中完成了该书的中译。我们已经尽了所能。错讹之处,恭请方家读者指教。译完之后,我只想说一句话:在当今中国读书界,译这种书实属不幸,读这种书则是万幸的。
2004年8月15日,兰州大学古草园
这几天,雅典正在开奥运会。一场全人类身体竞技的狂欢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奥林匹克回到雅典,这当然是回到了一个圆的原点,人类有足够的理由狂欢。
谈人类,自然要有一个类的尺度,这样才能把人统起来。这个类的尺度是从希腊人那里来的,是从希腊人的哲学中来的。哲学说希腊话,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无论是演绎还是递归,都要遵循种加属差的逻辑。这是哲学的源头,也是科学的源头,希腊人把科学(物理)和哲学(后物理)一并提出的奥秘就在这里。统合在希腊哲学尺度中的人才有了共同的类的概念,而随着希腊哲学在近代欧洲的复兴和放大,出现了以近代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以及西方文明的全球化,并在接受了以希腊哲学为母体的“人类”概念的情况下,对地球上其他精神存在的方式和价值体系构成了挑战,在这种挑战和冲突中有了种种刺耳的说法,如“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等。这些说词产生于人种的比较中,产生于文化单元的比较中,不管在这些比较中生产出多少差异,它们仍然是“人”与人的游戏方式。而在“人”与非人的游戏中也生产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说法。
“人类中心主义”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自然人意义上的人与非人的关系。如人与动物、植物、资源、能源的关系,把人置于目的的位置,人是其他动物的目的,人是其他植物的目的,人是一切资源和能源的目的,不仅限于地球,而且包括了地球以外的资源和能源。月球探测,火星探测,水星探测……这都是人类生存目的的延伸。人类有了保护动物、植物的意识,有了生物链和生态环境的意识,有了地球家园的意识,这些意识仍是服从于人类生存永续的目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第二层意思是按地球人的尺度在无限的太空中复制人,寻觅地球人的影子。随着地球村概念的形成,地球上的人作为一个类已无实质差异,早已类化于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等一系列的科学网格中,并形成了人类学的共同话语模式,说到底,人类、人类学作为一个类和类化的解释方式,是基于共同的希腊哲学公约出来的人认知自己的能力和方式。人已经失去了发现新大陆时的奇异的陌生力量,在共同的解释系统和话语方式中,人已经完全同质化了,不仅异国情调褪色了,而且诸种基于历史积淀的神秘感也黯然失色。地球上已经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可以停泊“人类”的寄托。地球上的“人类”与“人类”栖居的地球同样孤单,一样的无依无靠,同样裸露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在科学的暗指中,地球以及地球负载的人类不过是太空中的一粒尘埃而已。孤单制造着孤单的人,孤单的人寻觅孤单的人,本意是分享孤单,而实际上却在倍增着孤单。人类开始把目光指向地球之外,在地球之外任何可能的地点(依我们共同的希腊哲学和科学的指引)寻找我们的同伴,可伴我们的同类。老虎伴人,人虎各有其怕,蛇狗相伴,也各有其怕,不同类就不可同伴,纵然猫狗可以伴人,也是各有各的世界,各有各的期许,猫狗不能人事,人也不能行猫狗之事。人还得找“人”,不论怎样的滑稽,人怎么可能走出自己的世界呢?即便人有可能走出“人”,又怎么可能走出人呢?我们在地球之外能寻觅的,要么是理论上的人”,要么是见证意义上的人,除此,即便出现比人还人的人,我们也是视而不见的。一波又一波的UF0浪潮不是已让我们足够的眩目了吗?我们的演技不是已足够的笨手笨脚了吗?不论是“人”还是人,我们(我们?)能寻找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能见证的还是我们自己。我偶尔在想,一个在平面中爬行的虫子何以能见证人的世界?一个据说只生活在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中的人何以能够见证这些维度之外的世界呢?
“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的无奈。虫子信赖“虫子主义”,细菌信赖“细菌主义”,这都无可厚非,各有各的无奈。但用虫子的眼光找细菌,或用细菌的眼光找虫子,就会衍生一系列能不能、该不该的问题。而评判能不能、该不该的还是人。人总归不能设身到虫子和细菌的世界,按理说没有评判的资格,但人可以举取一箩筐非评判不可的理由,而且听上去还委屈得不得了,并且还是一些在人看来无比崇高的理由。其实,人并没有理解虫子或细菌的世界,人做的只是依据自己的理由让什么样的虫子和细菌存在,什么样的不能存在,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等等。这实际上都是人的世界的延伸,不管是人的生存世界,还是人的价值世界。我们被自己的世界紧紧地禁锢着。他人有可能是自己的天堂,但自己绝对是自己的地狱。即便是开满鲜花的地狱,可仍然还是地狱,被无岸的边界锁闭着的地狱。
各个地狱都紧紧地把守着自己的门。利益之门,价值之门,好恶之门,权势之门,性情之门,语言之门和生死之门,这些门狭窄而龌龊,阴暗且潮湿,隐藏着诸多机关,门的多少也许可以无穷列举,但门的定义从根本上说不是敞开和开放,而是锁闭,随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每个人在自己的门前都一样,守望多于遥望。谁都在自己的守望中渲染神圣和不可替代,谁都在为这种神圣和不可替代寻找更神圣和更不可替代的理由。如此一来,我们的世界更加密不透风,我们的门更加紧闭,我们的边际更加擦磨拥挤,我们的爱和恨更加悬浮诡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索拉里斯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遥望的天窗。
什么是小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什么是艺术?艺术是创作在语言中的超越?是什么在创作?是什么在语言中超越?如此一问,莱姆的《索拉里斯星》一书是不是小说似乎已是问题。莱姆学过哲学,学过控制论,学过心理学,也学过什么不伦不类的科学方法论。在他的写作中,这些表面上的学习背景都能找到一些痕迹。《索拉里斯星》这本书既不是通常的小说,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更不是科学一科幻著作,很难界定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也许应该视其为一本天书吧。它的可读之处也许就在于它是一本天书,因为只有天书才能浑然开释人为的痕迹,才能解开人类的类结,才能抛开文学的一般流程,才能避开以“光秃秃的数学”为基本言说方式的科学的桎梏,才能总揽人类作为类的种种形迹和问题。《索拉里斯星》的言说者凯尔文带着地球的问题和托付奔向索拉里斯星球,他和其他去索拉里斯的科学家一样,是为了去那里实现地球人的心愿的,是去寻找人类的同伴的,不管这个同伴在心智水平和生命等级上比地球人高还是低,总归是以地球人的“人”的尺度来衡量的。但当他到达索拉里斯时,在经历一系列地球人的惯常作派和定势思维的挫折后,他才渐渐明白,在索拉里斯面前,地球人简直就是哑巴和傻瓜,一窍不通,根本就不得要领。地球人惯有的征服者面孔变得幼稚可笑,威胁者不断受到威胁的病态感觉像心理魔幻师一样捉摸不定,无所适从。征服索拉里斯,破译索拉里斯的生命信息,带着征服者装满战利品的行囊光荣地返回地球,燃起人类征服整个宇宙的雄心壮志,这是凯尔文及其他科考队员的初衷。但在经历了索拉里斯无穷尽的幻生幻灭之后,地球已经不可能是他们的家园,而是他们的伤心地,是屡生绝望的牢狱,是包藏着无尽的是非之地。地球人的征服欲,征服者的血腥必然带来的自身恐惧反被索拉里斯无尽的单纯所消弭,在索拉里斯无法用地球人语言理解的单纯中,地球成了极不单纯的地方,令人恐惧的地方,原本的家园变成记忆中的牢狱,聚集着各种狭隘、傲慢、怨恨和自以为是的牢狱。画地为牢的地球人不仅偏执狭隘,而且极度自我膨胀,故作神圣,自以为是宇宙之精灵,而且还炮制出各种神来伪善自己,抬高自己的身价。凯尔文在经历了索拉里斯的洗脑之后才终于有能力在神的话语中澄清自己,剥去地球人造神的伪善,他这时才发现,真正的神,唯一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不需要为它的苦痛去赎罪,不拯救任何东西,谁也不效忠,它只是存在着。只存在着,没有意义,没有理由,没有为什么,存在着的中性力量抵御和消解一切人为的侵袭和剥蚀。神存在,别无其他,这是神保障人无罪的唯一途径。地球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无法听任神的存在不受侵扰,作为授神者的地球人不可避免地为种种罪迹所缠身。地球已注定是回不去的地方。家园消逝了,消逝在索拉里斯大洋变幻不定的地平线的交错往复中,地球以及地球所负载的地球人的一切已融合在索拉里斯大洋的永恒的无时间的律动中。
每一个记忆和回忆的瞬间都能产生生命形体,生命完全成了幻生幻灭的东西,这充满恐惧和绚烂的一幕幕在索拉里斯上实现了。我相信它是真的。其实也无所谓真不真,我信,这就足够了。其实也无所谓我不我,随着幻生幻灭的大洋波浪漂浮就足够了。随记忆而出现,再忆再出现,这还不够美妙吗?在没有时间的永恒里,记忆、回忆也已是无限的,无限的重复,无所谓生与死,这不就是地球人在美学上期待的瞬间化作永恒吗?在地球上、在科学上实属奢望的记忆符号在索拉里斯上实现了,这不是妙不可言吗?还能期待什么呢?凯尔文在索拉里斯大洋的惠顾下,在无时间的永恒中,实现了他与海若(大洋版的阿芙罗狄特)若即若离的中性拥有,这不是超出一切情爱、性爱、爱情和友情的神性之诗吗?地球人可曾敢奢望过?
作者是地球人,译者是地球人,读者您想必也是地球人,我们谁都无法摆脱地球的束缚。作者带着地球的局限写作,译者也在地球的层层桎梏中翻译,但作者和译者都希望您在读这本书时,能创造自由的阅读空间,能在思想上抵消地球引力和文化惰性对您的约束。能够生长自由的阅读无疑是美妙的,但自由的参照系在哪里?在地球?在人类?在索拉里斯?在大洋?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答案,解释自由的语言力量源于读者心灵自由的创造,无论作者还是译者都无权侵犯读者自由解释的权利。但译者也许可以代表作者对读者只提几个问题:您有过话语解放的冲动吗?您有过人类自我超越的挣扎吗?您在地球云层的包围下,在琐屑的社会事务、生存事务的日常纠缠中,有过眺望无际星空的冲动吗?您在聆听地球人关于地球人的价值体系、信仰体系、政治经济体系的高谈阔论时,心头曾闪过一丝的悲凉吗?您在目睹和经受了地球人生生死死的欢欣与悲哀时,曾经萌生过解脱缠绵红尘的郁闷吗?那您就读这本书吧。我不知道这本书出了多少波兰文版和英文版,但德文版自从1983年出了第一版后,到2001年已出了16版,几乎每年再版一次。想必这个数字已透露出这本小说的阅读魅力。
眼下,地球上的人类正忙于星际探测和太空旅行,这些活动当然都是服务于地球人生存目标的,不管这种生存目标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或者国际的、人类的。也许您就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一个科学主义者、一个异教徒……,不论您属于哪一种,在陌生的语言森林中进行一次小小的郊游,总是一件快意的事,哪怕是为了寻找心仪的猎物也值得您花上一点时间,毕竟,这里的猎物与您常识中的猎物有所不同。
这是一本天书。商务印书馆的朋友盛意托付,授我译它。我不知天高地厚,虽有迟疑,还是应了下来。一叶知秋,没译几页,就知道自己领了苦差事,呕心沥血、连滚带爬地译完之后,自己仿佛害了一场大病,苦不堪言。翻译苦,这一点人所共知。但翻译《索拉里斯星》这种书何其苦也,恐怕并无几人晓得。作者是用波兰文写作的,我从德文译,是经过翻译的作品,是再加工过的,我很少读过这么别扭的德文,想必波兰文的原作品不会如此别扭。当然,我也能体会德译者的艰辛,同样的呕心沥血、连滚带爬,知人苦者最苦。在对比《索拉里斯星》的德文版和英文版时,心里暗自嘀咕,文学翻译的差异居然可以如此悬殊,长了一些见识。相比之下,德译者似乎在字面上更忠实于原文,而英译者则遵循了意译的原则,删减幅度较大,有些再创作的味道,据商务印书馆的朋友说,原作者希望依据德文版翻译成中文本,想必作者有自己的评判,我倒觉得,德译、英译各有千秋。我依照的是德文本,虽也参考了英译,毕竟风格上还要跟着德文走,这就苦上加苦了。
据友人说,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几经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我并不感到惊异。就其写作视角的独特性和对虚拟世界预言家般的敏锐来说,无论是获诺贝尔奖提名还是最终获得诺贝尔奖,均属实至名归。但对一个试图向人类语言本身发起挑战的作家来说,诺贝尔奖真的能成为评判他的尺度吗?
作者自己也备尝了写作的艰辛。在小说中,作者自己声明,他也是用地球语言强说其所不能说,语言的缺斤短两、词不达意之处甚多。这让译者颇感为难,译者的译者就更加死去活来了。凭鄙人的这点耐心根本就完不成这个任务,幸有夫人相助,她不仅在文字技术上为我提供帮助,而且每逢疑惑处都掌灯相磋。更重要的是,每当我被《索拉里斯星》折磨得意志消沉、声言放弃时,夫人都及时鞭策鼓励,这才在万般艰难中完成了该书的中译。我们已经尽了所能。错讹之处,恭请方家读者指教。译完之后,我只想说一句话:在当今中国读书界,译这种书实属不幸,读这种书则是万幸的。
2004年8月15日,兰州大学古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