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一窥突厥汗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若干重要历史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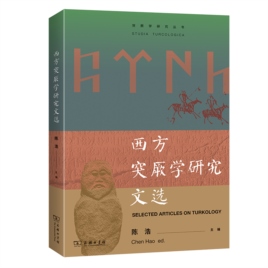
定价:¥68.00
一窥突厥汗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若干重要历史问题
作为商务印书馆“突厥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既是一部突厥简史——读者从中可以管窥突厥汗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若干重要历史问题,也是20 世纪西方突厥历史研究的一部学术史,可以借此了解西方学者研究突厥历史的路径和范式。作为该领域内的第一部“文选”,我们希望《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能对读者了解突厥汗国和突厥语人群的历史有所裨益。
本书所收9 篇文章和1 篇书评,都是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德国、美国、俄国和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有研究突厥历史和语言的深厚传统。当然,中国学者对突厥的研究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考虑到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汉语文献相对容易获得,所以就没有将其纳入本书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一取舍,也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外国学者在研究突厥和突厥语人群历史时的关怀和问题意识,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导 读
(节选)
作为商务印书馆“突厥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既是一部突厥简史—读者从中可以管窥突厥汗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若干重要历史问题,也是20 世纪西方突厥历史研究的一部学术史,可以借此了解西方学者研究突厥历史的路径和范式。作为该领域内的第一部“文选”,我们希望《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能对读者了解突厥汗国和突厥语人群的历史有所裨益。
本书所收9 篇文章和1 篇书评,都是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德国、美国、俄国和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有研究突厥历史和语言的深厚传统。当然,中国学者对突厥的研究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考虑到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汉语文献相对容易获得,所以就没有将其纳入本书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一取舍,也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外国学者在研究突厥和突厥语人群历史时的关怀和问题意识,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们反复强调,汉文中的“突厥”专指公元6—8 世纪中国北方的游牧政权—突厥汗国。突厥汗国瓦解之后,“突厥”的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不同文化语境和不同历史时期,“突厥”的指称都是不一样的(详见“总序”)。用一句话来概括突厥概念的变迁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8 世纪以后在语言上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不同部落、民族或政治体,统称为“突厥语人群”或“操突厥语的人群”(Turkic-speakingpeople)。
本书的第1 篇文章讨论拓跋鲜卑的语言属性,系笔者在北大攻读硕士学位期间(2009—2012 年)翻译,收入本书时对个别参考文献做了修订。卜弼德认为它是一种突厥语,而不是蒙古语。读者可以借此文来了解突厥汗国兴起之前(可能)操突厥语人群的历史,相当于“突厥前史”。卜弼德是俄裔美国学者,以汉学研究见长。他利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围绕中古汉文史料中北族名号的阿尔泰语词源,撰写了一系列学术札记,编成《胡天汉月方诸》一书,享誉学林。
作为6—8 世纪欧亚大陆的草原帝国,突厥与中原王朝和拜占庭在外交、军事、贸易等各方面都有互动。因此,有关突厥的史料主要保存在汉语、希腊语的文献中,因为这些定居民族有书写历史的传统。难能可贵的是,与匈奴、柔然、鲜卑等草原政权不同,突厥留下了用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和语言书写的石刻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用“他者”书写的历史。
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的石刻史料,大型且相对完整的只有一通《布古特碑》,且用粟特语和粟特文书写。我们很难仅凭这一个例子,就推断第一突厥汗国的统治精英使用的是粟特语而不是突厥语。本书第2 篇文章,是苏联突厥史名家克利亚什托尔内和伊朗学家列维谢茨共同对布古特碑文的解读,历史背景是木杆可汗执政前后。作为最早的研究者,他们的解读难免会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例如,他们认为布古特碑碑首是一个母狼的形象,这是过于执泥于突厥母狼起源传说的后果,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螭首形象。另外,日本学者在20 世纪90 年代曾对包括布古特碑在内的突厥碑铭重新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录文。从常理上讲,考虑到风蚀等自然因素,年代越早的实地勘察,碑文的可辨识度越高。即便如此,日本学者吉田丰还是提出了不少新的解读,例如他认为nwh snk’’ wst“建立新的僧伽”应当读作nwm snk’’ wst“建立教法之石”,更有道理。
…………
东突厥汗国衰亡的环境和社会政治因素*
〔美〕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 撰
陈浩 译
突厥游牧政权在公元6 世纪中叶兴起于中亚和蒙古草原(Sinor1990)。551 年(译按:一说552 年),在反对旧主柔然的叛乱之后,突厥人肇建了自己的汗国,并开始向西扩张。突厥汗国很快便分成东、西两翼,西突厥隶属于东突厥汗国,都是由阿史那家族统治。两翼的势力逐渐独立,甚至互相敌对,最后发展成东、西两个汗国。东突厥汗国在7 世纪早期,利用隋末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向中原政权索要贡赋。在7 世纪20 年代,东突厥汗国的颉利可汗严重威胁着唐朝的北方。颉利可汗的军队于626 年抵达渭水,与唐都长安仅有一箭之遥,不过在从唐朝获得大量物资之后便撤军了(Graff 2002)。然而,东突厥汗国在630 年遭受唐朝的打击之后便在政治上瓦解了。
历史学家把东突厥汗国的衰亡归因于一场内部危机—招致唐太宗对突厥进行军事干预。此事件以突厥军队的失败和突厥可汗的被俘而终结(Graff 2002; Eisenberg 1997)。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汉文史料中有大量关于627 年突厥境内强降雪及其所导致的大面积饥馑和牲畜死亡的记载(《旧唐书》卷194 上《突厥传上》,第5158—5159 页)。由气候异常所导致的经济困境,很快演变成一场广泛的政治危机—或许部分是由早前的政治动荡和内部分化所导致的。对突厥政权来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国内属部的反叛,以及他们的统治正当性在内部受到了挑战。
费杰等人(Fei et al. 2007; Fei 2008)从汉文史料中选择了一些关于极端天气和饥荒的事件,来说明气候可能在突厥汗国的骤亡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们还怀疑,当时的环境变化,是由626 年左右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所引起的。最近对两极地区冰川的化学分析表明,这一波动大致发生于北半球的温带地区(Sigl et al.2015)。虽然626 年气候变化的迹象在南极地区不是很明显,但是当地的硫化物异常却是此事件最好的佐证,这是北格陵兰岛NEEM(译按:NEEM 是指一个从北格陵兰岛探取冰核的项目)2000 年的记录中除了1783—1784 年冰岛拉基火山喷发以外的最大痕迹(Thordason and Self 2003)。在南极地区没有迹象说明这次火山喷发发生于北半球纬度较高的区域。Stothers 和Rampino(1983),以及Stothers(2002)列举了(年代较晚的)中世纪拜占庭和叙利亚史料中的证据,来证明626 年左右有一股平流层悬浮体存在。不过,文献中的年代以及他对文献的解读,还不是很明确。
众所周知,大型的、富含硫化物的火山喷发可以造成好几年连续的夏季异常变冷(Robock 2000; Cole-Dai 2010)。但是,如果往届火山喷发的地点、时间和硫化物的产量不能得到有效的限定,那么气候模式的准确性是要打折扣的(Timmreck 2012),有碍它们与以标准量为基础的气候重构数据进行对比(Esper et al. 2013; Stoff elet al. 2015),以及任何的历史学解读(Büntgen et al. 2011; Büntgenet al. 2015; Guillet et al. 2017; Oppenheimer et al. 2017)。即便是在火山喷发事件为人所熟知的区域,在评估距离火山较远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影响时,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因果关系,还是需要十分谨慎,而且还要考虑到其他的因素(Oppenheimer 2011, 2015; Büntgenet al. 2016)。
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火山喷发所导致的夏季变冷,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东突厥汗国的衰亡,如果是,又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它的衰亡?我们以跨学科团队合作的形式,遣用历史、年轮和冰核的证据,来重构并阐释东突厥汗国晚期的气候和环境变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人口转型的时空模式。
…………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