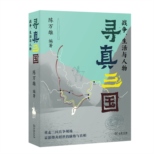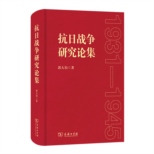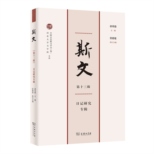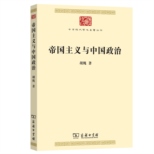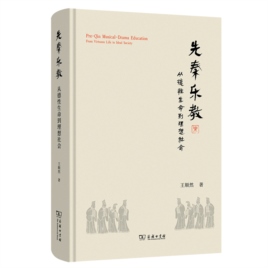从哲学的视角看,欲讨论先秦乐教,首先要解释清楚“声”“音”“乐”等基本概念,而这一点并不容易。
从文本上讲,如孔颖达说:“周衰礼废,其乐先微,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为乐官,颇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孔颖达讲的,是汉初《乐记》文本形成的基本背景:其一,春秋以降,周之乐、礼的政治、文化传统崩坏,乐与礼的内在关系错位,且相较于礼而言,乐传统的断裂尤甚;其二,在乐传统崩坏、娱乐化的过程中,其最基本的音律规范也被郑、卫之新声混淆破坏,律制产生的依据、原则未得到保存;其三,汉初乐官能记下来的,多是传世乐章之音律曲调,个中思想内涵不能确准。如此看来,《乐记》虽是“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在传世文献中,已经代表着汉初学者对周乐之制度、思想最集中、最有体系的总结。但汉初对传统生疏的状况,在孔颖达看来,已经给《乐记》解释周乐思想的可靠性打了折扣。
从学说上讲,《乐记》是汉初儒生集体编纂的,其思想总体上是偏向儒家的。比如,很多在《荀子·乐论》中与墨家对辨的论述,在《乐记》中成为陈述性的结论。这样的思想倾向,将一种心性论的立场嵌入《乐记》对“声”“音”“乐”概念的说明当中,构建了人性论意义下的“声”“音”理论。这究竟是周乐理论的本意,还是儒家的特色,有待于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逐一分辨。
有鉴于以上情况,在本章对“声”“音”“乐”概念的梳理中,我们把目标文本就集中在《乐记·乐本篇》。只讨论这数百言的文字,既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文献编纂所导致的杂乱,又能给“声”“音”“乐”概念确定一个基本的解释。而有了这一基本的解释,我们也能在面对其他涉及礼乐传统的文本时展开比较、判别,以形成对观念转变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