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一部通史式的岭南禅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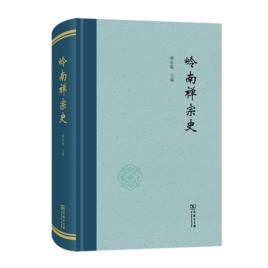
定价:¥98.00
一部通史式的岭南禅宗史
本书是首部通史式的“岭南禅宗史”,它从地方史和禅宗史的叠合视角,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岭南禅宗的产生、传播、发展、演变的历史,重点考察了岭南佛教史与禅宗史、禅宗与禅学的关系、禅僧的活动、唐五代和明末清初两个高潮时期等。就作为历史运动的禅宗而言,可说高僧大德是主体,思想是灵魂,著述是载体,寺庙是道场,环境是助力,本书对这些环节皆有重点关注。对诸如禅宗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禅门大德的生平事迹、禅门文献著述的基本情况、禅宗寺院的分布和兴替、禅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等方面均有论述和剖析。
岭南禅宗史研究的范围界定及学术史回顾
近二十年来,岭南的禅宗文化研究和推广活动好戏连台,高潮迭起,特别是连续五次“禅宗六祖文化节”的举办,更是让人觉得岭南禅宗研究似乎进入了全盛时期。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岭南禅宗史研究的成果并不多,有关岭南禅宗发展史的许多问题仍然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任何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和推进的,岭南禅宗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所以,作为本书的绪论,我们将从岭南禅宗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入手,在厘清岭南禅宗史研究边界的基础上,试图对岭南禅宗史的学术研究历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为本书的研究做一点基础性的铺垫工作。
一、岭南禅宗史研究的范围和内容
岭南禅宗史,顾名思义就是岭南禅宗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问题似乎简单明了,但如果考虑到岭南在佛教传入中的特殊地位,佛教传播发展过程中整体性与地域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寺院分布的地域性和僧人弘法活动的跨地域性特点,以及不同宗派之间既交融又矛盾的互动关系,就需要对岭南禅宗史研究的范围和内容进行界定。
(一)研究范围界定
如何界定岭南禅宗史的研究范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既涉及区域,即岭南的界定,也涉及禅宗史本身的界定,但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标准,至少以下五个方面必须加以考虑。
第一,由于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与整个中国佛教的传播、发展史密不可分,受整个佛教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讨论岭南禅宗史不能不涉及岭南佛教的发展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和印度的佛教发展历史,尤其要处理好岭南佛教史与禅宗史的关系,即岭南佛教史中哪些是属于当地禅宗史的内容,这样就必须有一个取舍的标准,不能将禅宗史当佛教史写。就禅宗本身而言,禅宗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派,研究岭南禅宗史必然会涉及全国甚至其他国家禅宗的发展,那么,在讨论岭南禅宗与其他地方禅宗发展的关系时,应花多大篇幅论及其他地方的情况就值得考究。如果完全避而不谈,则无法厘清源流和影响;如果笔墨花费太多,又会喧宾夺主。因此,这里必须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限和范围。
第二,禅宗与禅学的关系。禅宗与“三学”“六度”中的“定学”,即禅定是不相同的,但又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禅定可以说是佛教各派,甚至是世界各大宗教的共法,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言:“禅那(Dhyāna)的境界,释迦也曾说过,这是一种共法,所谓共法,并不是佛法所独特专有的,凡普通世俗的人,与其他宗教,异派学术的人,只要深明学理,努力修证,都可以做到类似的定境。”台湾印顺法师也指出,“禅定是共世间法”。所以,禅门中人也修习禅定,禅宗吸收了禅定的一些方法和思想,至少禅学是禅宗的渊源之一。那么在叙述禅宗产生的渊源时,势必要谈到各种禅学经典的翻译、流布,中国佛门禅修活动的历史,但禅宗之前的禅学历史中哪些部分该纳入禅宗的范围,比如在初祖达摩来华之前,一些禅僧在岭南的弘法活动是否应纳入禅宗史的范围,或者哪些内容该纳入禅宗史的范围,也应该有相关的原则。
第三,禅僧的弘法活动与地域之关系。禅僧活动的一大特点就是行脚参访、交流心得、印证所学,一个著名的禅师往往四处参学问道,开悟成名之后其驻锡寺庙往往也非止一处,其学说思想的形成也不能说就属于某一地区。也许只有六祖慧能大师是一个例外,其出生、闻道、出家、弘法、圆寂都在岭南,其中只有短短八个月的黄梅印证接法活动是在岭南之外,其一生的行迹、思想都明确属于岭南,没有疑义。但其他大多数祖师大德,包括六祖门下的许多弟子,其弘法活动都非止一地。以近代的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为例,他在粤振兴曹溪和云门两大禅宗祖庭,对岭南禅宗的复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其一生参学弘法、建寺安僧、兼祧五宗、培养后学,行脚遍亚洲,弟子满天下,他在粤的弘法活动只是其一生弘法事业的一小部分。他在粤事迹比较清楚,但讨论其思想时,应该掌握一个怎样的限度也是值得推敲的问题。
第四,岭南是海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印度东来传法的梵僧首先在这里登岸,中国西行求法的僧俗大多在这里启程。无论来华梵僧还是求法华僧,其中不少人都与禅学和禅宗有关,如求那跋陀罗,他作为早期禅宗宗经《楞伽经》的传译者,在达摩祖师之前就曾泛海来粤并弘传禅法,此外,还有许多中国禅僧沿海路赴印求法,他们的事迹是否应包括在岭南禅宗史之内?对许多求法僧而言,岭南只是他们求法途中的一个驿站,他们的所有求法活动是否应纳入岭南禅宗史?
第五,岭南作为地理概念并不像行政区划那样有一个十分明晰的地域界线。从理论上讲,除广东一带外,它应该还包括广西的一部分、海南省和今越南的北部;因此在叙述岭南禅宗的发展史时,如何将以上三地,特别是广西、越南北部(宋以前)的禅宗史实纳入岭南禅宗史的框架之内,这也是一个需要审慎处理的问题。
所以,要写出一部岭南禅宗史,就必须处理好上述五个方面的关系,既要兼顾岭南禅宗史与整个佛教发展史,以及其他宗派、其他地域的互动关系,又要在材料的剪裁取舍上恰到好处;既要阐明岭南禅宗自身发展的脉络和特点,又要展示它与其他地区、其他宗派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
(二)岭南禅宗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禅宗作为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经历了一个思想由隐到显、僧众由少到多、寺庙由寡到众、内部管理体制由简略到完善、影响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与其说禅宗是一个宗派,不如说它是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人(高僧大德)是主体,思想是灵魂,著述是载体,寺庙是道场,环境是助力,这些因素的隐显兴衰导致了禅宗发展的曲折隆替。因此,岭南禅宗史的研究,既要描述禅宗作为一种思想和社会运动整体的发展过程,又要揭示构成这场运动的各种要素的兴替变化和相互关系。具体而言,岭南禅宗史的研究至少应包括如下六个方面:
1. 禅宗发展演变过程的整体描述
岭南禅宗史首先必须从整体上勾勒出禅宗在岭南形成、传播、发展、演变的基本轮廓。从历时性上展示其消长变化的大致轨迹,从共时性上揭示其地域分布以及各要素之间的构成情况;从横向联系上揭示其与其他宗派、其他地域以及其生存发展之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纵向内涵上展示岭南禅宗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自身特征和属性。
2.禅宗思想形成发展的基本轨迹
禅宗作为一个宗派,除了佛教的共同理论之外,它还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思想,考察禅宗基本思想的源流、内涵及其演变历程是禅宗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众多的禅宗史著作中,不同学者对此都进行了翔实的梳理和考察,但目前尚无专门论著对岭南禅宗之基本思想和义理进行全面的考察。如果要对岭南禅宗史进行全面研究,岭南禅宗思想史的整体考察无疑是其重要内容,而其中的问题在于,在禅宗的整体理论中,哪些思想内容是岭南所独有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这是一个要审慎处理的难点。
3.禅门大德的生平事迹
禅门的祖师大德影响着禅宗发展的方向和状态,他们的思想行为、著作法语构成了禅宗史的主要内容,因此,禅门祖师大德的生平事迹是撰写岭南禅宗史最为核心的内容。要处理好这一部分内容,需要对粤籍禅门大德和来粤弘化之禅门大德进行恰如其分的考察。粤籍禅僧,有的主要在粤弘化(如六祖和天然禅师),也有许多主要在其他地方弘法(如石头希迁和木陈道忞);入粤弘法的高僧大德,有的一世都在南粤弘化(如澹归今释和石濂大汕),有的只是一部分时间在粤传法(如憨山德清和虚云长老)。对这些粤籍禅僧的外地弘法活动以及外地来粤弘化大德的生平事迹进行怎样的取舍,才能真实反映岭南禅宗的历史面貌,也是颇费斟酌的问题。
4.禅门文献著述的基本情况
禅宗虽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特点,然在《大藏经》中,本土著述绝大多数是有关禅宗的文献,如禅宗的传记、灯录、公案、谱牒等等。岭南禅僧在漫长的岁月中也留下了许多文献和著述,对这些禅宗文献加以介绍和整理,对其所反映的禅宗风貌的变化进行归纳总结,也是岭南禅宗史的重要内容。
5.禅宗寺院的分布和兴替
古代中国佛教的弘法活动常常是以寺院为依托,形成一种佛教文化中心,进而辐射并影响其周围民众的社会生活,禅宗也是如此,一个宗派和法系常常由一个或几个寺院形成一个活动中心(如云门宗以乳源云门寺为中心)。岭南是禅宗南派的发源地,有众多的禅宗祖庭,禅宗寺院的分布和变化往往反映了禅宗兴衰变化的情况,所以禅宗寺院的分布和变化情况也是岭南禅宗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6.禅宗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禅宗与禅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一种修行方式,一个是一种生活方式,禅宗将禅定由一种修行方式转变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直面人生问题的心态,用心态的调整取代了姿势的调整。将过去禅修者离群索居、山栖涧饮的头陀行变成了行住坐卧、心定即禅的生活态度,将禅修融入生活之中,因此,也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禅宗与生活的这种互动关系,既是岭南禅宗的特色,也是岭南禅宗发展壮大的源泉。因而,阐明岭南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与禅宗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是禅宗史的重要内容,也是探讨岭南禅宗特色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岭南禅宗史研究的基本情况
明确了岭南禅宗史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之后,我们再来回顾既往有关岭南禅宗史研究的基本情况,就会更加准确地了解前辈和时贤有关岭南禅宗史研究的关注重点和主要成果,把握当下岭南禅宗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一)岭南禅宗史研究最受关注的两个阶段
就现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第一本岭南禅宗史研究的著作是1996年出版的覃召文的《岭南禅文化》,虽然该书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但也简要介绍了岭南禅宗的形成发展过程,岭南禅门的主要祖师大德和主要禅宗寺院,并对岭南禅文化的特点进行了初步探讨。紧接着,于1997年出版的第二本禅宗研究方面的专著是胡京国的《慧能与禅宗》,书稿虽以介绍慧能生平和《六祖坛经》(也简称为《坛经》)的内容为主,也简要介绍了岭南禅宗的发展历史,内容包括祖师禅以前的习禅僧人行迹,禅宗的兴起、演变,以至近代的八指头陀和太虚大师等,所述内容虽然并不仅仅是岭南禅宗史,但毕竟勾勒出了岭南禅宗史发展演变的大致轮廓。
就总体而论,岭南禅宗发展史上有两个阶段最受重视,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一个是唐五代时期;一个是明末清初。前一阶段是曹溪禅形成和云门宗兴起的阶段;后一阶段则是明清易代之际,遗民逃禅,庄臣故士大量削发为僧的时期,是岭南禅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六祖慧能大师创立南宗,在曹溪宝林说法三十七年,其生平事迹和开示法语被结集为《六祖坛经》,并成为禅宗宗经,其弟子将顿悟法门推向全国,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宗派。所以《坛经》和慧能生平历来都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不仅岭南禅宗史,中国禅宗的研究也都是如此,每一本研究禅宗的专著都会花大量篇幅讨论慧能的生平和《坛经》的思想,研究《坛经》和慧能的著作和论文可说汗牛充栋。近年,广东省佛教协会出版了《六祖坛经集成》,收集了各种版本和文字的《坛经》;正在编辑《禅宗研究大全》,将搜集中外学者禅宗研究方面所有论著,包括中文和外文的论著,并结集出版,这将是一项浩大而有学术价值的文化工程。
云门宗是“五家七宗”中唯一形成于岭南的分灯禅,所以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研究著作中除了许多单篇的论文之外,已出版了冯学成的专著《云门宗史话》。此前有由岑学吕居士编写的《云门山志》,其中也有大量篇幅讨论文偃祖师和云门宗的历史。可以说,云门宗是岭南禅宗史研究中成果较多的一个部分。
学术界关注的第二个时期的重点是明清之际的遗民僧群体,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蔡鸿生的《清初岭南佛门事略》。虽然该书并非禅宗专史,但书稿研究的主体却是明清之际的遗民僧群体,对清初佛门与官府的关系、禅门僧人的临终偈、清初三大著名禅僧(天然、剩人、成鹫)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可说是明清之际岭南禅宗史的开创性著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明末清初的遗民僧研究渐成热点,广东学术界召开了数次专门的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一批有学术水准的论文,使明清之际的岭南禅宗史,特别是曹洞宗高僧群体的生平事迹和著作诗文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二)岭南禅宗史研究最受重视的两项内容
在既往的研究中,禅门人物研究和禅宗文献研究格外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成果也相对较多。这实际是两个相关联的内容,著名禅师往往有著作语录存世,而禅门著述的作者常常也是著名的高僧大德,所以,人物研究与文献研究可以说是互为表里。
1.岭南禅宗史人物研究
在岭南禅宗人物的研究中,慧能、文偃、德清、天然、澹归、大汕、成鹫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这其中尤以禅宗南派的实际开创者六祖慧能的研究成果为最。在“中国知网”上以“慧能”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显示近三十年来有关慧能的研究论著达5508篇(部)之多,而涉及慧能与岭南禅宗发展关系的文章亦达百篇之数,其内容涉及慧能的生平、事迹,慧能的思想、著作,慧能的法嗣、弟子,慧能与岭南文化的关系,等等。近来,学者对慧能的研究之细密,连其名讳也有专文进行研究商榷。这些研究成果从总体上肯定了慧能作为佛教禅宗的实际开创者和中国文化伟人的地位,并对他的顿悟思想的渊源、特点、影响进行了专门探讨,对慧能思想与岭南社会文化背景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虽然慧能的生平事迹、思想特点、著述文献都有专门的研究,但慧能在岭南的行迹活动并非已经全部清楚了然,仍然有些问题尚待澄清,例如,慧能隐藏怀集、四会十五年的具体行迹和活动,慧能与岭南士人的关系,慧能著述(包括《坛经》)中所引证的佛教经典以及慧能是否真是一字不识的文盲,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前人有所涉及,但并未彻底澄清,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除六祖慧能之外,岭南禅宗史上最受关注的人物就是明末清初的大汕、天然和澹归禅师了。作为明清之际岭南遗民僧的精神领袖,天然禅师自民国以来就受到关注,1942年汪宗衍就撰有《天然和尚年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天然为代表的曹洞宗法脉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天然的生平事迹、诗文著述、法嗣传人及其与官府的关系都受到了全方位的重视,广东学界召开了数次专题学术会议,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
除天然之外,其嗣法弟子中最受关注的是澹归禅师。1987年吴天任就在香港出版了《澹归禅师年谱》,详细梳理了其生平著述。广东学术界也召开了有关澹归的专题研讨会,并整理出版了其诗文著作。目前虽无研究他的专著出版,但却有众多具有相当学术质量的论文发表,对其出家前后的生平事迹、诗文著述、鼎建丹霞山别传寺的经历以及与平南王尚可喜的关系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大汕虽非天然一系的禅师,但在清初的广东也有巨大影响,且曾泛海至越南弘法,著有《海外纪事》一书叙述其弘法越南的事迹,后因各种人事纠纷而被官府逮捕,死于羁押途中。对他的研究有姜伯勤先生的专著《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翔实探讨了他的生平事迹、诗文著述、弘法海外的经历、他与天然一系的人事交往,以及他与澳门禅史的复杂关系。
除上述三人外,屈大均、今无(阿字无)、剩人函可、成鹫、唐代的大颠、宋代来粤的大慧宗杲、明末来粤的憨山德清、近代的虚云长老也受到学界关注,并有专门论著进行研究。
2.岭南禅宗史文献研究
历史研究离不开文献资料,岭南禅宗史的研究也是如此。第一个对岭南禅宗史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冼玉清先生,她所编撰的《广东释道著述考》第一部分为“释家著述考”,以题要和节录的形式著录了广东历代佛门中的诗文著述、志书传记,其中大部分为禅门大德的著述,可以说是对禅宗文献的一次系统整理,包含始自唐代六祖慧能,止于近代岑学吕、苏曼殊等人的著作,并且还著录了明清士人编纂的寺志和经注以及近代岭南学者有关佛教研究的著述。对于每一部著作,先介绍作者、版本,再介绍其内容、结构和特点,特别是有些章节所附的作者按语,简要介绍了作者对这一著作的流传情况、相关问题的研究心得和评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就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言,冼先生的这一著作至今仍未被超越,是研究岭南禅宗史的指南性著作。
对于岭南禅宗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开始着手进行,如民国初年广东省教育厅就曾资助出版《光孝寺志》,还有学者整理出版明清之际禅门僧人的著作,但大规模地整理出版岭南禅宗文献资料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1981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了澹归今释在南明为官时的文稿《岭海梵余》;1989年,香港佛教志莲图书馆据清宣统年间上海国学扶轮学社印行之版本重印出版了澹归今释的《徧行堂续集》b;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教、学两界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清初岭南佛门史料丛刊》,系统地整理出版了明末清初岭南佛教僧人的著作,对天然、澹归、大汕、成鹫、今无、函可、二严、弘赞、一机、开沩、顾光、道忞等禅门僧人的著作诗文进行点校、注释,可谓是岭南佛教史和禅宗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同时展开的另一项基础性的文献整理工作是“岭南名寺系列”丛书。丛书分为古志整理系列和今志编纂系列,已点校整理出版的古志包括《光孝寺志》《鼎湖山志》《丹霞山志》《曹溪通志》等寺志,今志已出版的有《丹霞山锦石岩寺志》,正在编纂的有《光孝寺志》《华林寺志》。由各个寺院自己编纂出版的寺志,还有《六榕寺志》《潮州开元寺志》《南华寺志》等今人编纂的寺志。寺庙是佛法僧汇聚之所,其兴衰存毁向来是佛法兴衰的标志之一,广东作为禅宗南派的发祥地,绝大多数寺庙为禅宗寺院,所以寺志的整理和编纂也是岭南禅宗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所保存和提供的一些史料是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
(三)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了人物、著述的研究和唐代、明清之际的禅宗史研究之外,其他部分和时段的研究就显得比较薄弱或沉寂。特别是达摩以前的岭南佛教史和禅学史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前贤的相关研究有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它对沿南海道赴印求法的僧人史料有较为系统的搜集和钩沉,今人的学术著作则只有《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算是对汉唐岭南海路求法活动的一个总体研究,其中包括了岭南禅宗史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菩提达摩、求那跋陀罗、求那跋摩、般剌密谛(《楞严经》的翻译者)、真谛、智药三藏等禅师的生平事迹。此外,由雷雨田等编撰的《广东宗教简史》、广东省民宗委组织力量编纂的《广东省志·宗教志》对岭南禅宗史的相关内容也有涉猎,但都以介绍性为主,缺乏深入原创性的研究。
对宋元明和近代的岭南禅宗史的研究也成果寥寥,只有零散的论文见诸报纸杂志。所以,通观整个岭南禅宗史的学术研究,两个时段(唐中后期、明末清初)热门,其他阶段冷落,两项内容(人物和文献)成果较多,其他内容关注较少,这种状态说明要撰写一部内容翔实、点面周到的岭南禅宗史,还需要对唐以前、宋元明和晚清、近代的岭南禅宗史进行全方位的资料搜集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探讨,才能为岭南禅宗史的撰写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结语
任何研究都是前人研究工作的扩展和继续,只有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有了整体的把握和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吸收前贤和同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推陈出新,填补空白,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性研究。岭南禅宗史的研究也是如此。禅宗强调以心传心、见性成佛,认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以不立文字相标榜。如果仅从文字资料着手,那么了解到的或许只是禅宗的形式,而非神韵。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文献却是最为主要的资料,事实上不立文字的禅门大德也给后世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字资料。如何从这些文字资料中揭示岭南禅宗发展、演变的历史真相并非易事,只有竭泽而渔地全面搜集资料,深入其中而又出乎其外,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才能对岭南禅宗的历史发展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从而写出一部真实可信的岭南禅宗史。
作为第一部通史式的《岭南禅宗史》,在纵向的时间上限方面,本书没有设定,力求追寻岭南禅宗的最早踪迹;而在时间下限方面,则止于新中国成立。因为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不但岭南禅宗自身会有新的气象,且岭南禅宗研究也会有新的篇章。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