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文献学专家仓修良先生的论集,附序跋集,以及仓先生著述目录、学术活动年表。
仓修良先生在谱牒学和历史文献学领域造诣颇深,本书收录主要收录仓先生在谱牒学和历史文献学领域的论文,体现了其学术建树。此外收录的仓先生学术自述及序言、前言,可以使读者得以了解仓先生的学术脉络及当时学界的人际往来。由后学整理的《仓修良先生学术论著目录》《仓修良先生学术活动年表》,既是对仓先生学术生涯的回顾总结,也是对他的追忆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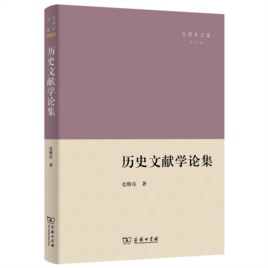
定价:¥128.00
文献学专家仓修良先生的论集,附序跋集,以及仓先生著述目录、学术活动年表。
仓修良先生在谱牒学和历史文献学领域造诣颇深,本书收录主要收录仓先生在谱牒学和历史文献学领域的论文,体现了其学术建树。此外收录的仓先生学术自述及序言、前言,可以使读者得以了解仓先生的学术脉络及当时学界的人际往来。由后学整理的《仓修良先生学术论著目录》《仓修良先生学术活动年表》,既是对仓先生学术生涯的回顾总结,也是对他的追忆纪念。
本书是《仓修良文集》的一种,收录了仓修良先生在谱牒学和历史文献学领域的论文若干篇。这些论文集中展现了作者的研究和开拓,是仓先生一生精研谱牒学与历史文献学的论文荟萃,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一些论文堪称我国相关领域的奠基之作。此外,同时收入作者的《我与中国史学史》、《我与方志学》2篇学术自述和为其他著作撰写的序言、前言、后记18篇,反映作者在广义的历史文献学领域的有关思考,并以附录形式收入《仓修良先生学术论著目录》《仓修良先生学术活动年表》。
阅读古籍应当注意选择版本
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这部书不仅在校点方面做到字斟句酌,精审允当,而且装帧美观大方,给人以美的感受(这一点十分重要,希望各出版家能引起重视),更重要的还在于校点者沈芝盈先生通过比较研究,选择了一种好的版本,这就为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黄氏这部学术巨著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每当我翻阅此书时,往往感到很内疚,因为拙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对这部书的介绍由于当时未注意选择版本,而向读者传播了错误的说法,总想找个机会,向广大读者表示道歉。
20世纪80年代初,在修改《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书稿时,由于时间紧迫,在评介《明儒学案》时,又由于相信《四库全书》所收之书,没有注意研究该书的版本,以致铸成了错误。事实上从黄宗羲在84岁时所作的自序中可见,作者在世时已有许氏刻本、万氏刻本和贾氏刻本三种。不过前两种刻本均未刻全,贾氏刻本虽全而宗羲本人却未曾见过。至于抄本流传之多,那就可想而知了。雍正十三年(1735),慈溪郑性承接万氏刻本,“续完万氏之未刻”,于乾隆四年(1739)刻完,这就是后来流传比较广的“二老阁本”。光绪八年(1882),冯全垓再刻“二老阁本”,并在所作跋中说,对该本仅作了“修其疏烂,补其缺失”的工作,所以内容并无不同。道光元年(1821),会稽莫晋根据家藏抄本,参校万氏原刻,重加订正。他在序中说:“予家旧有抄本,谨据万氏原刻,重加订正,以复其初,并校亥豕之讹,寿诸梨枣。”光绪十四年(1888),南昌又根据莫氏刻本刊刻。这样万氏刻本就有两个系统的本子流传下来。这两个系统的刻本在内容上也确实有些不同,故范希曾在《书目答问补正》中说“会稽莫晋刻本善”。所以这个刻本流传最广。而流传于北方的便是贾氏刻本。贾润盛赞该书学术价值之高,决定刻印,但尚未开始便去世了。其子贾朴继承父志,历14年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完,因贾润斋名紫筠,故亦称紫筠斋本。这个刻本问题较大,一直被认为有失黄氏原意。郑性在序中说:“康熙辛未,鄞万氏刻本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辍。嗣后故城贾氏一刻,杂以臆见,失黄子著书本意。”莫晋在序中更具体指出:“是书清河贾氏刻本行世已久,但原本首康斋,贾本改为首敬轩,原本《王门学案》,贾本皆改为《相传学案》。与万立河原刻本不同,似非先生本旨。”可见贾氏所刻,未能忠实于原作,编排顺序既已变动,著作意图自然就无从反映。不仅如此,正如沈芝盈、陈祖武二位所指出,就连他们约请黄宗羲所撰写的序言亦作了改动,以致造成许多不应发生的混乱。万贞一与黄宗羲关系密切,刻本自属可信。《四库全书》所收《明儒学案》,用的是山东巡抚采进本,从《提要》介绍可知是为贾氏刻本。《提要》曰:“初周汝登作《圣学宗传》,孙钟元又作《理学宗传》,宗羲以其书未粹,且多所缺遗,因搜采明一代讲学诸人文集语录,辨别宗派,辑为此书。凡《河东学案》两卷,列薛瑄以下十五人。《三原学案》一卷,列王恕以下六人。《崇仁学案》四卷,列吴与弼以下十人。《白沙学案》二卷,列陈献章以下十二人。《姚江学案》一卷,列王守仁一人,附录二人。《浙中相传学案》五卷,列徐爱以下十八人。《江右相传学案》九卷,列邹守益以下二十七人,附录六人。《南中相传学案》三卷,列黄省曾以下十一人。《楚中学案》一卷,列蒋信等二人。《北方相传学案》一卷,列穆孔晖以下七人。《闽越相传学案》一卷,列薛侃等二人。《止修学案》一卷,列李材一人。《泰州学案》五卷,列王艮以下十八人。《甘泉学案》六卷,列湛若水以下十一人。《诸儒学案上》四卷,列方孝孺以下十五人;《诸儒学案中》七卷,列罗钦顺以下十人;《诸儒学案下》五卷,列李中以下十八人。《东林学案》四卷,列顾宪成以下十七人。《蕺山学案》一卷,列刘宗周一人。而以《师说》一首冠之卷端。”很明显,这个排列顺序,确实如莫晋所说,与万氏刻本不同,自然就有违黄宗羲著作之本意。因为作者原著之排列,不仅考虑到时代先后之顺序,而且注意阐述学术思想的流派发展分合关系。笔者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一书中仅根据上述这种编排进行客观介绍,所作结论,既无法说明黄宗羲如此编排的意图,又无法阐述明初儒学两大派在学术上发展之大势。
《明儒学案》所列学案的排列顺序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实际上体现了作者的著书宗旨与意图,而不是任意罗列。从全书所列19个学案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四个部分。明初九卷,以程朱之学为主,陆象山派为次,故先立崇仁、白沙两学案,将两个学派对峙局面一开始就向人们作出交代,如同摆开两方之阵势。崇仁以吴与弼为首,这个学案的小序说:“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故必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於戏!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此论正是饮水思源,说明吴与弼乃是有明一代学术思想之先导,上承宋人成说,有继往开来之功,“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故将《崇仁学案》列为首位,自然是名正则言顺。只此一点,就足以证明贾氏刻本确实有违于作者本意。次即《白沙学案》,以陈献章为主,此则为陆学一派,开后来王学之基,故其小序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又于《姚江学案》小序曰:“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在黄宗羲看来,陈献章实际上是陆王之学的中介人,所谓“白沙开其端”,就是指陆学在明代开始传播之端,所以这个学案就被列在第二。至于《河东学案》,皆属程朱之学。明初九案之中,还另有《三原学案》,小序云:“吴学大概食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节气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这就是说,这个学派本出河东薛氏,但其学术宗旨又不尽相同,乃成为派生出来的别派。这些事实说明,此书对各个学派的源流委曲,是条理得非常分明的。而在分立学案之时,既照顾到各个学派各家之间相互关系与影响,又尽量区分出各派各家之间学说宗旨之不同,如果对于这些学者的著作、思想特别是其学术宗旨不是了如指掌,要做到这样脉络分明是不可能的,这也足见作者学问之博大精深。中期则专述王学,首立《姚江学案》,叙述这一学派创始人王守仁的学术思想,以下依次分立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各学案,并皆冠以“王门”二字,以见其传授之系统。同时还另立止修、泰州、甘泉三个学案,虽都出于王学,但各有其不同宗旨,故别立学案,以示区别。如止修学派,虽出王门,已另立宗派,与王学是同中有异。而泰州学派,亦出于王学,但对王学提出了重大的修正,别立宗旨,成为王学之左派,既已另打旗号,与王学宗旨分道扬镳,自然也就不能再统属于王学之门下了。至于《甘泉学案》之立,黄宗羲认为,湛若水亦曾从学于白沙,而“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必王氏之盛”,但“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甘泉学案·序》)。这三个学案,尽管渊源均与王学有过不同关系,但因各自别立宗旨,已不同于王学,故学案之上皆无“王门”字样。末期则立东林、蕺山两学案。东林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蕺山则仅刘宗周一人,此人乃宗羲之本师。在中期与末期之间,又另立《诸儒学案》,以收各学派以外之学者,这正是他在凡例中所提出“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者,“正宜着眼理会”原则的体现。综观整个编排顺序,完全是按照有明一代理学发展之趋势而定,确有较为严密的内在联系,一经变动,其内在联系自然就要受到影响。
谈到《明儒学案》,人们不约而同地都会肯定这是黄宗羲所作的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史专著,至于它在史学发展上究竟应当居于何种地位,由此书的产生而创立的“学案体”应作何评价,至今仍很少有人涉及,近年来新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众多著作中,甚至连“学案体”都不曾提及,其他论著就更可想而知了。因而在许多评介史籍的论著中,大多将《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附在传记一类,这不仅是很不恰当的,而且是无视这种文体的存在,否定了黄宗羲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体。基于上述情况,笔者曾写过一篇《要给学案体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短文,希望学术界能够重视黄宗羲创造“学案体”的重要性,而在各种有关学术论著中都要给它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最近美国有位访问学者又问我:“《高僧传》为什么不能看作是学案体?”这是针对海外有的学者将《高僧传》视作“学案体裁的远祖”而提出的。至于国内有的学者将朱熹的《伊洛渊源录》称作最早的学案体,自然更不妥当,笔者当另撰文论述。对于上面这一问题,我的回答还是否定的,因为这种说法既忽略了产生一种史学体裁的时代背景,更未考虑作为一种史书体裁是必须具有一定的结构组成形式。首先应当看到,这种史体,是以学派为前提而“立案”,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学术发展中真正形成学派要从宋代才开始,而历史著作是要反映社会现实的;其次从史体而言,每一种史体都必然有特定的组织结构形式,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一般来说,必须具备纪、表、传、志四个组成部分。政书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等,也都有各自的组成形式。就“学案体”而言,它的编次顺序是,每一学案之前,先作小序一篇,简述这个学派的源流及宗旨,接着便是案主各学者的小传(有的案主不止一人),对每个人的生平经历、著作情况、学术思想及学术传授,作扼要评述。然后便是学者本人著作节录或语录选辑,间有作者自己的按语。可见这种“学案体”既不同于普通的学术思想史,更非各种简单的人物传记所能比拟。因为它是由三种体裁有机地结合在一种文体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完整的新体系。很显然,这种结合是经过黄宗羲的精心安排,使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和作用,这自然是一种创造。后来全祖望在续补《宋元学案》过程中,对这种史体又进一步加以补充而使之更加完善。在每个学案之首,先立“学案表”,备列该学派师友弟子,以明其师承关系及传授情况,有的学者在书中已立案,则于表中注明“别见某学案”,或已附于他学案者,则注曰“附见某学案”,这就给读者了解这些学派、学者在学术上的来龙去脉提供了方便。又在学案之中设立“附录”,载录学者的轶闻逸事,尤其是记述当时或后世人的评论,为后人研究和判断某位学者的得失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种史体在我们的各种史学论著中或目录学著作中尚未取得应有的独立地位。这一则是因为这种史体著作为数太少,除上述两种外,只有徐世昌招收门客所编的《清儒学案》一书是真正的学案体;再则便是对这种新的史体结构并不了解,因而就出现了近来有些著作将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也称之为《清儒学案》了。总之,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所创立的“学案体”不能再任意抹杀了。当然,用这种史体来写学术史难度很大,非功底深厚的人所不能为,因为要为一人立案,非通读此人全部著作不可,一个学派、一个朝代就更可想而知了。这也是影响“学案体”流传的重要原因。
(原载《书品》1990年第1期。收入《史家·史籍·史学》)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