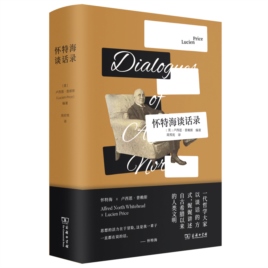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一代哲学大家以谈话的方式,娓娓讲述自古希腊以来的人类文明。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理论家,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和哈佛大学。他对20世纪的哲学、科学思想影响巨大。
自1932年起,《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卢西恩·普赖斯,把怀特海的谈话记录下来,形成这本包含四十三节谈话的谈话录。在轻松的交谈中,怀特海就哲学、文学、历史等议题发表了很多睿智的见解。
怀特海兴趣广泛、风趣幽默、思想充满了活力。他对日常事件总有新颖的想法,更大的聚会则引发了他思想的更多方面,揭示了他个性的更多方面。与他以往的学术著作不同,本书中大多数话题是新颖的,在他的书中并不多见。而且普通读者在他著作中感到难以理解的那些抽象观念,出现在随意的谈话中,就变得相当容易理解。
本书对理解20世纪的思想史,理解怀特海,具有重要意义。 这不是一部高头讲章, 而是哲学家与朋友的随意交谈。它犹如一缕亲切的阳光射入读者的心灵,使人恍然大悟:原来高深的哲思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
怀特海希望能让人明白这一认识:人面临着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选择、令人激动的实验的转机、一望无垠的远景。只要我们不断尝试,只要我们维持着这种进步的可能性,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就是鲜活的。
思想停滞是人类易犯的错误。仅把此书推荐给那些内心充满恐惧和不确定感的人,推荐给那些为了安全而放弃冒险的人。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即使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仍然觉得人生是一段漫长而激动人心的旅程。怀特海说:“思想的活力在于冒险,这是我一辈子一直都在说的话。”从剑桥到哈佛,他的思想的冒险从未停歇。
相关评论:
我认为,对于所有与他有过接触的、有才干的青年人来说,他的启迪是非常实在的,且具有持续的感染力,正如他对我的启迪和感染力一样。
——﹝英﹞伯特兰·罗素 英国哲学家
我之所以在20世纪的所有著作家和思想家中唯独选择怀特海,主要是因为他最接近于提供出一种综合性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是世界克服这个世纪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所普遍需要的。
——﹝美﹞小约翰·柯布 过程哲学家,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讲述怀特海其人,讲述一个兴趣广泛、谈话总显睿智、时而妙语连珠的怀特海,普赖斯先生此书,则无疑是大手笔!
——﹝英﹞大卫·罗斯爵士 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
怀特海是当代英美第一大哲,他的思想贯穿了科学、哲学与宗教,不仅博大圆融,而且迭创新境。
——傅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