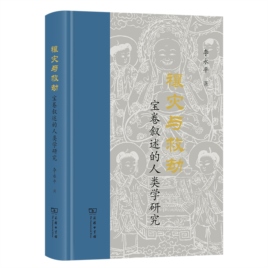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读者对象:中国社会史研究者,人类学研究者,中国民间宗教史研究者
宣传语:禳灾祈福——宝卷的主要功能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广泛阅读宝卷文献的基础上,对无锡、靖江、张掖、酒泉存在的宣卷做会活动进行田野考察,结合田野作业,从禳灾救劫与天书传统,禳灾的诗学特征、藏卷、抄卷动机、宝卷仪式的神圣场域,功德修炼与苦修救助,宣卷禳灾与社会秩序守阈六个方面深入分析回答在“如此广阔的地域,民间编创、抄写、刊印、宣讲、收藏如此卷帙浩繁的宝卷,其社会功能和群体动力是什么?”的问题。以文学禳灾功能切入,以文化大传统中的问题为导向,在材料使用上打破了文学、文献、神话、宗教等学科界限,有利于贯通口语文化与书写文化,寻找叙述传统背后的动力机制,这对探讨民间信仰的观念渊源和驱动力,促进本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李永平,陕西彬县人,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波士顿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陕西关陇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有俗文学、文学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近年来在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禳灾救劫与天书传统:宝卷文类的人类学解读
一、创世神话与民间“神谕”叙述
二、“佛头”与早期文化传统中的“萨满”
三、禳灾度厄与《香山宝卷》:“神授”与禳解传统
第二章 禳灾叙述的神话观念与文类传统
一、宝卷做会禳灾的神话观念
二、神圣言说与宝卷的禳灾文类
三、沟通天人的神圣言说与七言禳灾传统
第三章 宝卷信仰中的禳灾叙述结构
一、修炼飞升与度脱成仙叙述结构
二、游离冥府与审判:镇魂、超幽与洗冤叙述模式
三、“大闹”与“伏魔”:《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的禳灾结构
第四章 斋供、斋醮仪式与天时—人事禳灾
一、“天时”、循环时间与禳灾仪式
二、“人事”禳灾:庚申会、明路会、破血湖仪式
三、宝卷做会中的“度关”“安宅”与“荐亡”
第五章 禳灾与救劫:宝卷仪式叙述与神圣场域
一、仪式的功能理论
二、禳灾与救劫:宝卷宣卷仪式
三、藏卷、宣卷仪式之神圣空间
第六章 功德修炼与苦修救助:宣卷禳灾与社会秩序守阈
一、宣卷、抄卷、助刻:祈愿、分享与修炼救助仪式
二、宗教的循环时间与修身归正的秩序守阈
三、记忆共同体、宝卷的功德信仰与集体禳灾仪式
参考文献
后记
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