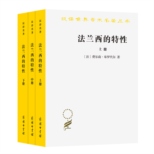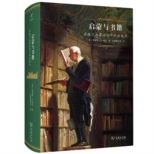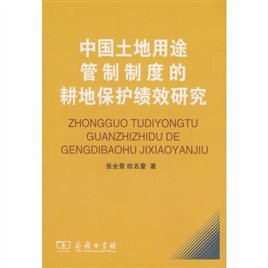显示全部序言
持续了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使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经济建设中占用大量农地(尤其是耕地),对我国的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严重削弱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统计资料看,1978—2004年,我国耕地面积从13 394.32万公顷下降到12 244.43万公顷,年均减少44.23万公顷。且从1996年开始出现加速减少趋势,八年间耕地净减少7 600万公顷,平均每年减少95.28万公顷,人均耕地降到0.094公顷。
为保护农地资源,特别是耕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国实行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把“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作为基本国策,通过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指国家为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通过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的制度。农用地的用途管制包括农地非农化的管制和农地农用的管制两方面,坚持“农地、农有、农用”的原则,限制农地非农化,鼓励维持农用。建设用地的用途管制按建成区和规划区的不同有不同的管制规则。
在我国,土地用途管制的产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且土地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剧增,我国人地关系呈人增地减趋势。在这种国情下,在土地管理方面,由于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利用的比较利益差别悬殊,单纯采用价格杠杆调节,常常出现不发生作用或作用不明显的现象,即出现了所谓“市场失灵”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保护耕地和粮食安全供给,借鉴国际上处理类似事件的成功经验,采取政府干预手段,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就成为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必然选择。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利用方式方面的重大变革。它对保护我国农用地特别是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粮食供给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土地用途管制的目的在于合理保护耕地资源,严格控制农用地转做他用,寻求既保护耕地和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安全,又保障非农用地的合理需求得到满足,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以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
从1998年开始,我国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已实施了十年,应该说在保护耕地,控制农地非农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政府寻租行为、政策措施协调性不强、法律责任不明确以及技术保障缺乏等原因的限制,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导致非农建设用地需求量居高不下的推动下,我国耕地数量减少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耕地保护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这项制度是否应该继续坚持?如何坚持?因此,定量研究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我国耕地保护中的绩效,分析耕地保护绩效的区域差异,揭示绩效的潜力空间,探讨提高耕地保护绩效的对策措施,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是基于以上背景,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心的欧名豪教授及其博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的张全景教授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下,选择“我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耕地保护绩效及其区域差异研究”这一课题,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形成了专著《中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耕地保护绩效研究》一书。该书从我国耕地数量的变动趋势与耕地保护的时代背景入手,在对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内涵全面认识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构建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耕地保护绩效分析的理论框架和模型,定量测算了全国的耕地保护绩效及其省际间的差异,并以山东为例对省区层面的耕地保护绩效进行了测算。该书还从耕地保护的外部性特征、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土地收益分配机制、耕地保护的制度成本以及土地利用规划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耕地保护绩效发挥的障碍因素,并从完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和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等方面探讨了提高耕地保护绩效的对策。
近一时期全球性的粮食价格上涨和供应紧张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只能依靠我们自己解决。我国仍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耕地保护的压力仍然非常巨大。作为一名老土地科学工作者和两位作者曾经的导师,我欣然为本书作序,一是希望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要以南京农业大学雄厚的土地资源管理学科背景为基础,不断推进中国土地用途管制与耕地保护的理论创新;二是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从事土地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从而不断提高我国土地资源管理事业的决策水平。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 万 茂
2008年5月5日
为保护农地资源,特别是耕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国实行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把“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作为基本国策,通过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指国家为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通过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的制度。农用地的用途管制包括农地非农化的管制和农地农用的管制两方面,坚持“农地、农有、农用”的原则,限制农地非农化,鼓励维持农用。建设用地的用途管制按建成区和规划区的不同有不同的管制规则。
在我国,土地用途管制的产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且土地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剧增,我国人地关系呈人增地减趋势。在这种国情下,在土地管理方面,由于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利用的比较利益差别悬殊,单纯采用价格杠杆调节,常常出现不发生作用或作用不明显的现象,即出现了所谓“市场失灵”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保护耕地和粮食安全供给,借鉴国际上处理类似事件的成功经验,采取政府干预手段,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就成为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必然选择。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利用方式方面的重大变革。它对保护我国农用地特别是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粮食供给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土地用途管制的目的在于合理保护耕地资源,严格控制农用地转做他用,寻求既保护耕地和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安全,又保障非农用地的合理需求得到满足,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以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
从1998年开始,我国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已实施了十年,应该说在保护耕地,控制农地非农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政府寻租行为、政策措施协调性不强、法律责任不明确以及技术保障缺乏等原因的限制,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导致非农建设用地需求量居高不下的推动下,我国耕地数量减少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耕地保护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这项制度是否应该继续坚持?如何坚持?因此,定量研究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我国耕地保护中的绩效,分析耕地保护绩效的区域差异,揭示绩效的潜力空间,探讨提高耕地保护绩效的对策措施,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是基于以上背景,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心的欧名豪教授及其博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的张全景教授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下,选择“我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耕地保护绩效及其区域差异研究”这一课题,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形成了专著《中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耕地保护绩效研究》一书。该书从我国耕地数量的变动趋势与耕地保护的时代背景入手,在对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内涵全面认识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构建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耕地保护绩效分析的理论框架和模型,定量测算了全国的耕地保护绩效及其省际间的差异,并以山东为例对省区层面的耕地保护绩效进行了测算。该书还从耕地保护的外部性特征、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土地收益分配机制、耕地保护的制度成本以及土地利用规划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耕地保护绩效发挥的障碍因素,并从完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和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等方面探讨了提高耕地保护绩效的对策。
近一时期全球性的粮食价格上涨和供应紧张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只能依靠我们自己解决。我国仍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耕地保护的压力仍然非常巨大。作为一名老土地科学工作者和两位作者曾经的导师,我欣然为本书作序,一是希望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要以南京农业大学雄厚的土地资源管理学科背景为基础,不断推进中国土地用途管制与耕地保护的理论创新;二是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从事土地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从而不断提高我国土地资源管理事业的决策水平。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 万 茂
2008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