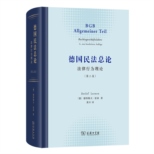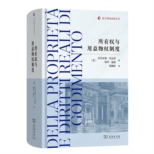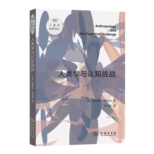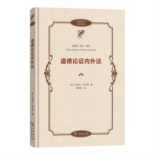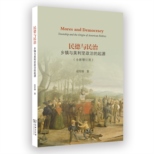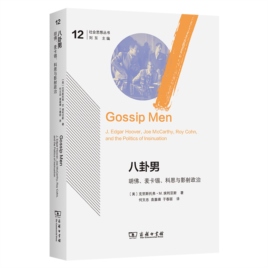第一章 现代性图景(节选)
胡佛的早年经历揭示了男性气质的社会关切如何影响他的个人发展。胡佛的性别认同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两个有所交集的运动:一是男女工作性质与不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剧变,由此产生对男性气质的焦虑情绪;二是这些世俗的焦虑情绪,通过新教的男性化倾向得以展现和迭代。为实现白人男性基督徒的理想形象,年轻的埃德加努力满足所处阶级对男性的期望,同时为跻身上流社会做好准备,打磨自身形象。
在胡佛的青年时代,美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1880—1920年间,美国人口翻了一番,从5000万增加到1.06亿。随着美国城乡人口分布重新洗牌,人口密度也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口结构(包括种族构成、城市中单身年轻人的数量、家庭规模等)、交通系统、经济组织与财富分配、国际地位、娱乐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可能是1880—1920年间的移民潮,特别是来自西欧地区的移民潮。在此期间,美国接收了约2800万移民。截至1900年,37.8%的美国居民不是在外国出生,就是移民的后代。出生率和平均寿命的上升使得美国总人口增多,移民的涌入更助长了这一趋势。移民潮、人口增长,以及工业经济的日益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快速扩张。
另一个变化是(通过印第安人战争和种族主义法律政策)对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实行人身、社会、经济和文化控制。与此同时,美国利用帝国主义新政策影响或控制南美、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屿,扩大其全球影响力。这种扩张得到了美国经济巨头的支持,其发生得益于企业制度的发展、管理阶层的出现、科学管理理论的应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工人衰落)和商业资本的增加。
文化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革命性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剧,以全新的方式将美国人民彼此联结在一起,促进了文化交流。媒体迅速发展,报刊杂志的读者数量达到空前水平,新兴新闻业(小报)迅速发展,图书出版的业务领域扩展到更受欢迎的低俗小说和廉价小说,广告即将成为媒体的重要收入来源。新闻业的扩展催生了新的文化英雄,包括运动员(尤其是拳击手和大学橄榄球队队员)、电台主播、歌舞杂耍演员。这些明星的走红离不开摄影和电影等新兴大众媒体的支持。在家庭领域,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他们不愿承担来自家庭和社区的责任,也抗拒参与时新的娱乐活动,由此出现了一位历史学家口中的“单身汉时代”(the age of the bachelor)。
社会各个领域几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引发了人们内心的担忧:美国男性是否变得太过文质彬彬了,特别是他们倾向于选择白领中层管理岗位而避免体力劳动。1870—1910年间,白领工作岗位增加了六倍以上。另外,1873—1879年、1884年、1893年的经济恐慌造成了家庭内部动荡,导致出现了一批无法养家糊口的荏弱男性。
这些问题深刻地影响着那个时代男性的成长方式。很多指南声称要教会父母如何培养儿子的男性气质,如凯特·厄普森·克拉克(Kate Upson Clark)的《如何教养男孩》(Bringing Up Boys: A Study,1899)和弗兰克·奥尔曼·贝克(Frank Orman Beck)的《迈向男人:一项关于男孩的研究》(Marching Manward: A Study of the Boy,1913)。总的来说,这些指南建议青年男性应该保持精力充沛、信仰虔诚、遵守纪律、道德高尚,同时尽力避免走上任何歧路,包括异常的性行为或其他反常行为。
克拉克的研究针对的是中上层阶级的家庭或那些渴望跻身中上层的家庭,胡佛家族就属于后者。她主要建议男孩应该保持活力和勤勉,他们的外表和举止彰显了其内心性格。这些积极特质可以通过玩游戏和参加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加以磨炼,这是“对道德本质的重要考验”。棒球就特别有助于培养诚实和韧性等可取的品质。与此同时,体育确实存在道德危险。克拉克对运动员时常爆出赌博丑闻感到惋惜,比如1877年路易斯维尔灰人队的球员故意输掉比赛以换取赌徒的贿赂。她也不赞成那些更为激烈、可能致伤的运动,特别是橄榄球。虽然《如何教养男孩》强调男孩要衣着整洁、举止得体,但克拉克不希望这种精致优雅有损男子的阳刚气概。和其他人一样,克拉克抱怨说男孩的都市化损害了他们的职业道德,她担心非体力工作会削弱劳动与成功的联系。作为证据,克拉克列举了许多“乡下小伙”经过童年的努力奋斗后成为伟人的例子,包括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大卫·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纳撒尼尔·鲍迪奇(Nathaniel Bowditch)、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亨利·克莱(Henry Clay)、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
弗兰克·奥尔曼·贝克也是类似的思路,并在著名心理学家G. 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的研究基础上塑造了一个10岁男孩的理想形象:精力充沛、体格健壮、组织性强、充满好奇、忠诚节俭。如果一个男孩表现出“不受约束的行为爆发”,他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发泄“被压抑的本能”罢了。贝克认为游戏有益于身心发展,可以为躁动不安的人提供发泄精力的途径,也可以作为男孩保持活力的手段。
(……)
胡佛选择接受基督教影响下的男性气质和道德观,以此应对现代化的种种挑战;与此同时,美国小报和八卦杂志的版面上也在讨论这些话题,不过立场与之大相径庭。20世纪初的八卦产业大多离不开对城市化、外来移民、工业化、企业化、性别角色变化的焦虑情绪,这也是胡佛宣誓效忠的那些保守组织诞生的起因。但这些让改革者夜不能寐的社会问题却被八卦媒体商业化了,八卦媒体试图取悦读者,而非吓唬他们。最重要的是,不同背景的美国人可以透过小报和八卦杂志一睹现代都市的精彩之处,同时以其为框架理解不断变化的社会格局。
尽管美国八卦杂志的发展脉络悠长而模糊,现代美国八卦杂志还是可以追溯到《都市话题:社会杂志》(Town Topics, the Journal of Society)。该杂志创立于1879年,最初名叫《安德鲁斯的美国女王:国家社会杂志》(Andrews’ American Queen: A National Society Journal),主要发布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名单。这个模式并没有带来商业上的成功,尽管为了盈利又改名为《都市话题》,杂志还是在1885 年被迫宣布破产。29岁的律师尤金·曼恩(Eugene Mann)以最低价收购了该杂志,他没有任何出版方面的经验。曼恩接手后的杂志采用更轻快活泼的语调,“谦逊”地宣称自己是“有史以来最紧跟时事、最前途光明、最诙谐幽默、最机警明智、最新颖独特、最具娱乐性的报刊”。这次转型的关键是“闲逛”(Saunterings)栏目,相较于其他刊物,这个轻松愉快的八卦专栏上的故事实在是有伤风化。接下来的六年里,“闲逛”使得杂志的发行量从5000份增至63000份,广告费用涨至原来的8倍。
杂志的转型方向引起了不必要的关注,尤其是那些得罪人的话题报道。受害人时常会出现在《都市话题》的办公楼,要求当面会见冒犯他们的作者或编辑。他们的来访太过频繁,于是编辑部制定了新对策,就是告诉愤怒的人们,他们要找的人“昨天刚刚去世”,再眼泪汪汪地表示那些冒犯性的文章正是“他最后写下的遗作”。关于这个计策是否成功,目前没有任何记录。受害人的愤怒还表现在诉讼数量的上升,罪名包括诽谤中伤和发送低俗邮件。1887年,曼恩被判犯有猥亵罪,但执行了缓刑。1891年,他又因同样的罪名被捕,这可能是因为“闲逛”栏目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堕胎在年轻女性群体中越发普遍。
曼恩知道,二次犯罪的服刑时间可能会大大延长,于是谎称生病,逃之夭夭,把《都市话题》的编辑工作留给了他的哥哥威廉·道尔顿·曼恩上校(William d’Alton Mann)。1864年退伍后,曼恩上校花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开展各种创业计划,包括为骑兵用枪的平衡装置申请专利、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勘探石油、设计有轨车辆,但无一例外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失败。
在接手《都市话题》前,曼恩上校也曾涉足过媒体行业。他通过合并阿拉巴马州沿海三家规模较小的报社,成了《莫比尔纪事报》(Mobile Register)的老板。曼恩上校利用这份报纸支持民主党,宣传新成立的三K党(Ku Klux Klan)的政见,由此建立了一个忠实的拥护者网络,这对一个重建事业的内战老兵来说无疑是个壮举。1869年,在阿拉巴马州重新加入联邦后举行的特别选举中,曼恩上校以民主党人身份竞选国会议员,但因失去黑人选票而落选。他在莫比尔市又待了三年多,然后前往纽约和伦敦,那时他的主要工作是有轨车辆制造。
将近二十年后,曼恩上校又回到了主编的位子上。1885年弟弟买下《都市话题》后,曼恩上校可能已经拥有了三分之一的股份,但直到1889年他的有轨车辆业务倒闭后,他才开始在报社发挥重要作用。曼恩上校可能是在目睹了诸如《世界与真理》(World and Truth)等伦敦色情小报的成功后,才建议弟弟将《都市话题》向下流猥亵转型。
从任何意义上说,他那惊人的直觉都高过生活本身,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每天到麦迪逊广场公园的戴尔莫尼科餐厅用餐的结果。曼恩上校在沿用弟弟做法的基础上加以拓展,把《都市话题》周刊变成造谣和影射纽约精英人士的杂志,其中包括阿斯特家族(Astors)和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s)。人们认为是他创造了“盲闻”(blind item)。“盲闻”是当时八卦刊物的普遍特征,指在不指明对象的情况下印刷散播谣言。曼恩上校从不讲求细节,他会在临近的段落旁边(通常在对开页)写上对象的名字,这样就不会显得内容太过隐晦。他还开创了维持各种线人的策略,包括酒店职员、剧院舞台工作人员和餐厅老板。
“闲逛”充斥着被其他社会杂志视为禁忌的话题:酗酒、婚前性行为、性病、通奸、非婚生子女、同性恋、离婚。曼恩上校曾表示,“纽约的社会不会变得比今天更毫无价值、更空虚无聊、更做作浮夸。这里住的都是些蠢蛋、浪子和暴发户”。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位采访者称,他的抱负是“通过让社会名流感到自我厌弃,停止他们那愚蠢、空洞的生活方式”,以此完成改造。用曼恩上校自己的话说,他是在“教导伟大的美国民众不要关注这些愚蠢的傻瓜”,就算他不出版《都市话题》,也会有“没有道德责任感”的竞争对手这么做的。他总结道,“我做这项工作,是为了社区,为了伟大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