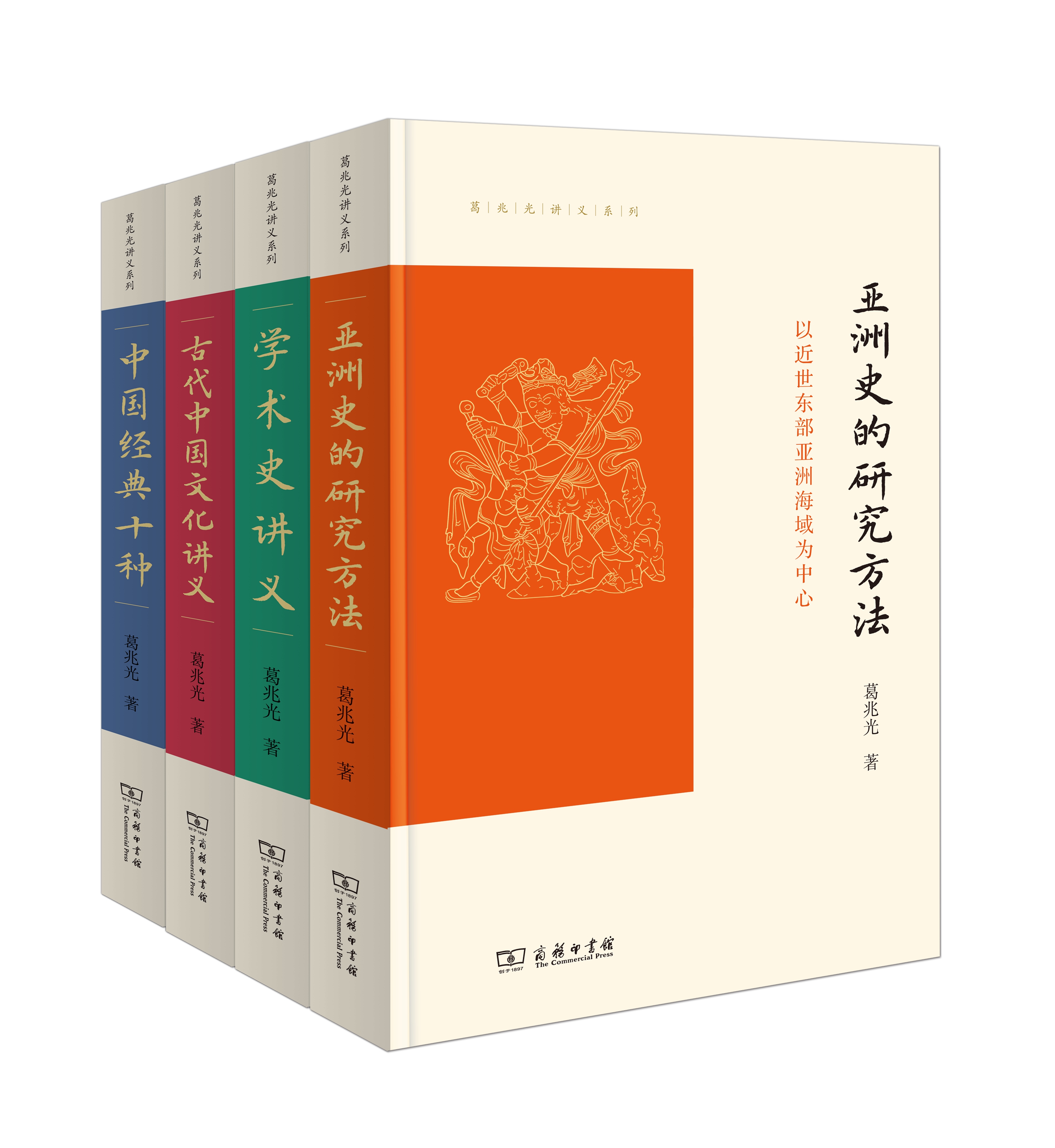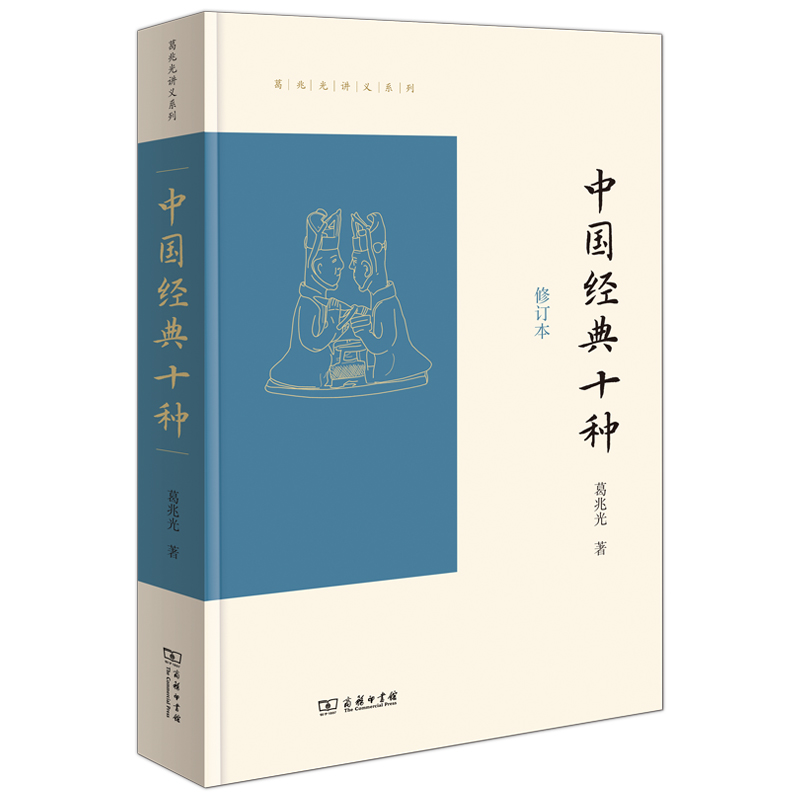推荐 | 葛兆光:中国传统绝不是"单数的",而应当是"复数的"
2023-09-01作者:官网报道新闻来源:商务印书馆浏览人次:65
“葛兆光讲义系列”(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何谓经典?葛兆光认为:
经典是在历史中不断被解释、被整理而形成的;经典不是神圣的、权威的、不可以被改变的东西;我们不要死守经典的神圣光环,要把反思和理解知识的权利返给读者。
中国的经典是杂糅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封闭的,纯之又纯的东西,我们应该对所有文化持开放的心态。
葛兆光教授的思考总是能直达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他对经典的诠释,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在当今学术界,葛兆光教授是少有的兼通文史哲研究的大家。纵观葛教授的学术历程,从宗教史到文学史,再到思想史、学术史、史学理论等,他始终在不断变换研究视野和领域,并出版了一系列在海内外都颇具影响力的专著。葛兆光教授擅于用通俗的方式表达精深的理论,语言明白流畅,深受读者喜爱。可以说,翻开葛兆光的任何一本书,读者都可在其独到的见解中有所感悟。
202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葛兆光讲义系列”,已陆续出版《中国经典十种(修订本)》《古代中国文化讲义(重订增补本)》《学术史讲义:给硕士生的七堂课》《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等四种,不仅提供了知识,更提供了思想和洞见。现摘选《中国经典十种》的序言,从中可一窥葛教授的深刻洞见。

《中国经典十种》序言
近来常有一种风气。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急急忙忙把它转换成“儒家经典”。我总觉得这种观念有些偏狭。其实,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绝不是“单数的”传统,而应当是“复数的”传统一样。我一直建议,今天我们重新回看中国的经典和传统,似乎应当超越单一的儒家学说,也应当关涉古代中国更多的知识、思想和信仰,这样,一部介绍中国经典的书,就应当涵盖和包容古代中国更广泛的重要著作。
简单地说有两点。第一,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以及东方的日、韩,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如宋孝宗、明太祖、清雍正皇帝),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仅仅说儒家,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比如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社会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第二,也许还不止是儒、道、佛,传统中国有很多思想、知识和信仰,可能记载在其他著述里面,“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广泛些?比如历史学中的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通鉴》之类,是否可以进入经典?西方人从来就把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算成是必读经典的。重建文化认同和进行传统溯源,也从来少不了历史著作,为什么不可以把它们叫作“经典”来重新阅读?至于古代中国支持经典研读(那算是“大学”)的基础知识(也叫“小学”),就是文字之学,其中的那些重要著作,《尔雅》是早就成“经”了的,而《说文》呢,更是可以毫不愧疚地列入“经典”之林的。道理很简单,古人早说过“通经由识字始”,不识字能读经典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也不妨让它们拥有“经典”的资格,莎士比亚那些曾被称为粗鄙的北方人的剧作,不也列入了西方经典之林了吗?因此,我在这部《中国经典十种》里面,既选有传统儒家的经典,也选了佛教、道教的经典,既有诸子的思想著作,也有史著和字典。
说到经典,还必须补充说明,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得它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还有的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和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历史里重新理解。所谓“放回历史里面”,就是说,这些经典需要先放在那个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就比如《周易》打一开始,就不是那么哲学和抽象,在那个时代可能就是占筮;《史记》在那个文史不分的时代,不必那么拘泥于历史学的谨严,就是可以有想象和渲染。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用一句理论的话讲,就是要“创造性的转化”。

《中国经典十种》原来是我在大学里讲通识课程的讲义,在理想中,大学应当是理解文化传统和提倡精神自由的岛屿,阅读经典也许正是实践这一理想的重要途径。布鲁姆(Allan Bloom ,1930-1992)在《美国精神的封闭》(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中曾说,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以便人们在共同问题和丰富知识基础上,建立“今人和古人在思想上的友好联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圣贤原则是必须遵循的教条,也不意味着古代经典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对经典的看法很简单: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不大可能纯之又纯、原汁原味,以为我们今天可以重新扪摸圣贤之心,可以隔千载而不走样,那是“原教旨”的想象;第四,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我也希望我所诠释的“旧经典”,能够成为今天生活中起作用的“新经典”。
《中国经典十种》(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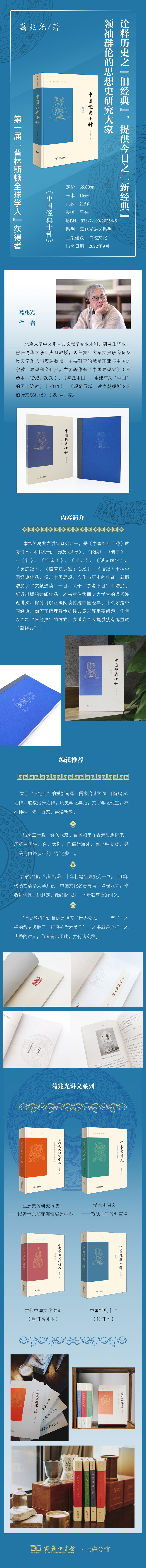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