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图书
-
思想的邮差¥88.00
思想的邮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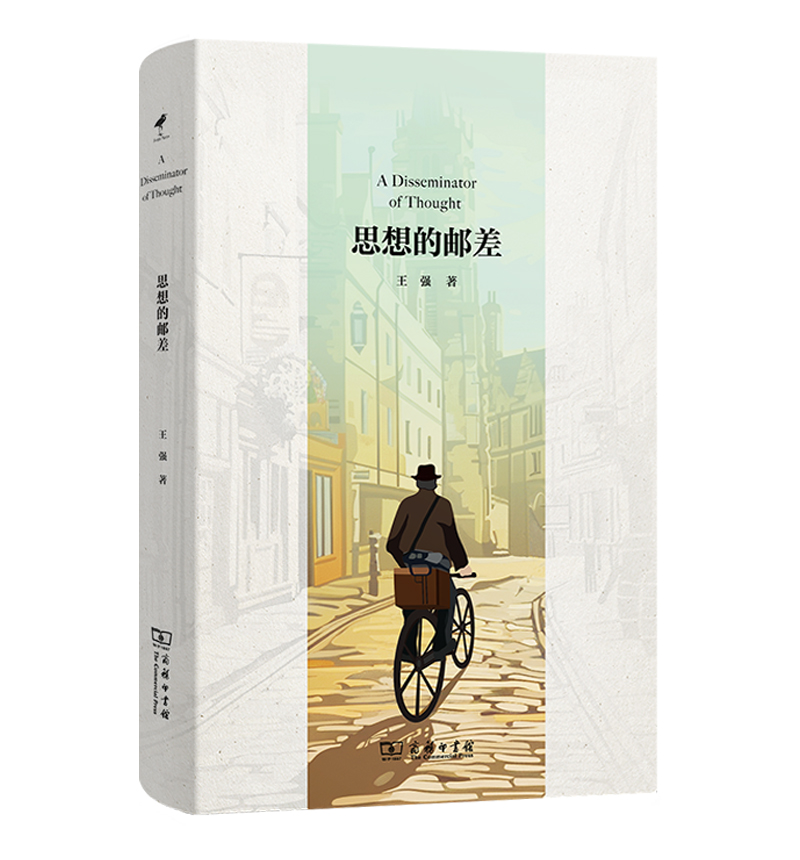
《思想的邮差》(商务印书馆2024年出版)
“在我们这个可思虑的时代里最可思虑的是我们尚未思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海德格尔即对他所处的时代下了这样的断语。在这个万物都变得飘忽不定的时代,更多的人恰似水上浮萍,随波逐流,沉浸于瞬息万变的数字洪流,“思”与“想”似乎正越来越遥远。海德格尔如果生在此际,不知又会发出何种嗟叹。至少我这个厕身于媒介学术研究的人,对于社交媒体环境中思想稀薄的状况总是会生出些杞人忧天之感。
非常偶然地得知王强出版了新书《思想的邮差》。久闻王强的大名,缘于他此前出版的《读书毁了我》《书蠹牛津消夏记》,特别是后者,因我做过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的缘故,特地买了一册海豚出版社的精装本,以为收藏。在那本书中,王强对经典书籍的追寻以及对书对于人生之意义的探讨,令人读之难忘。这次,王强将上述两书修订之后与《思想的邮差》一起交付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一并出版。甫一看到坊间书影,便觉三书样貌不凡,不由得又重新收集一套。到手过目,无论设计,还是材质,果然让人欣喜。
王强是新东方三位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真格基金的联合创始人。最近大火的、连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都颇为关注的《黑神话·悟空》的投资人亦曾在他的真格基金历练过。从这个角度看,他是了不起的实业家。
放眼全球,实业家不少,但实业家中爱书“爱到死脱”(沈昌文老先生谓王强语)的人恐怕极少。爱书,不仅是收藏书,且热爱书中思想。尤为重要的是,爱书人自己又精于思想者,恐怕更是少之又少。如果说读书有姿态,王强读书的姿态是回归读书人本该有的姿态——爱值得爱的书本身,爱所爱之书中思想的魅力。
或是因此之故,他将新出之书命名为《思想的邮差》。“思想的邮差”是该书第一篇,是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先生米寿而作。在王强看来,作为出版家的沈昌文先生像极了“思想的邮差”,一生以书为业,将思想之光、启蒙之思传递到万千读者之中,实在是厥功至伟。
“思想的邮差”的确是一个精彩的妙语。作为出版者,将作者的所思所想传递给社会公众,当然可以看作“思想的邮差”;作为写作者,撰写书人书话或者在写作中将前人精妙的思想介绍给读者,自然也可视为“思想的邮差”。
其实,细细想来,“邮差”是将邮品从此地此人手中传递到彼地彼人手中,在此过程中,一般而言,作为物品的邮品是没有什么损益的。“思想”与此不同。传播思想史学者约翰·彼得斯有一部讨论人类思想交流的著作,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何道宽教授翻译为《交流的无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邓建国教授翻译为《对空言说》。“无奈”也罢,“对空”也罢,都昭示了人类的交流与思想的传播,恐怕是相当不易的。彼得斯的观点是,完美的思想交流几无可能。
完美的思想交流几无可能,预示的其实是参与其间的各个环节(当然包括人)都有重塑思想的可能性。对于沈昌文先生这样的出版者而言,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观念是他想传播给社会公众的,相信凡是看过老先生晚年相关回忆录及书信集的读者,自会感知到他于此是颇有个人见解和洞见的。同样的,王强先生推崇的知堂老人读书、译书、写作的路径,写作者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不仅传达了他们所依凭的、推崇的人物的思想,也将自己的思想凝聚其中。换言之,将哪些思想者的哪些思想,纳入自己的出版实践和运思框架中,已经是在思想了。
一个事物总是在生成着,生成的过程,即是一件事物向着它所不是的新事物转变的历程,这是法国思想家德勒兹的观念之一。出版者的工作其实超越了“邮差”(事实上,作为思想的邮差,任务也是难以达成的),写作者的事业也超越了“邮差”——邮差,是负责将东西送到,东西不会有损益,但思想在传递过程中总是发生损益。使传播的思想发生损益,恰恰彰显了出版者和写作者的价值——因为他们生成了新的思想。
在我看来,无论是沈昌文先生,还是王强先生,都不只是“思想的邮差”,他们自身都是“思想者”。通过各自的工作,他们不仅传递了别人的思想,也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万千读者。人与书之间这样的互动,超越了“邮差”之责,这是思想的姿态。
(原载于《解放日报》2024年11月16日06版)
- 探寻老子思想的“启迪来裔”之路2023-11-11
- 哲学往往是革命性科学思想的“助产士”2023-07-28
- 理解商鞅思想的捷径2023-03-24
- 思想之光,当薪火相传——评傅道彬随笔集《一个被思想照亮的夜晚》2022-09-04
- 《符号学思想论》:一场从“意义世界”出发的跨时空对话2022-02-07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