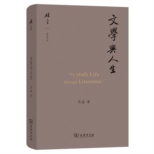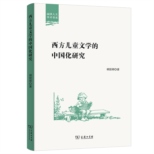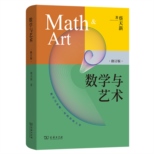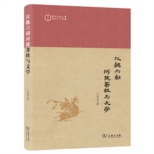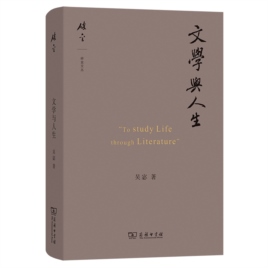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旧墨重痕留新知
重新整理珍藏近百年的授课手稿
再现大师的文学思想和人生思考
吴宓被认为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创始人,《文学与人生》这部授课提纲集中体现了其比较文学思想,以跨国别、跨学科的文学宗旨和人生伦理为基础,构建了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
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吴宓“一多并在,情智双修”。本书融通中西思想,强调给予人主体自由和诗意生活。书中选取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兼重经典和通俗,借此探究“什么是人”和“人要过怎样的人生”。同时,重视“诗”传统,以“爱欲”为主题,从文学透视人生,由人生理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