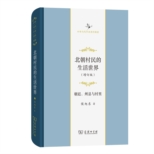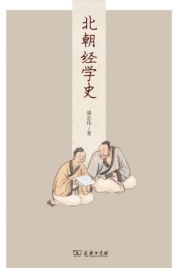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迄今为止国内最为全面的北朝经学专著,首次提出“北学主导南学”独创性见解
关于北朝经学的研究专著,迄今不多,本书之问世,可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大步。
经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成见以为,隋唐的一统在政治军事上是北方人征服了南方,在学术文化上却是南学征服北方。然而,本书作者却独具慧眼,修正了以往学界的共识,认为这一时期是以北方经学为主,而不是以南方经学为主。
本书详论北朝经学的起源、流派、学官制度、争论历程及其影响,对于中原少数部族政权的汉化、平城拓跋氏与中原士族的关联,以及孔颖达学派的崛起,无不一一考辨和论述。对于北魏时期的河北经学、宗教制度和学官系统,都有新见。对于北魏的政治改革,作者纳入经学的视野,做了饶有兴味的评议。对于北周的河西学者、关中学者与流亡名族学者的聚集,也各有专论。故而,本书观点较为新颖,水准较高,内容也较为完善,是一本难得的佳作。
乱世时期,经学之延续如丝缕,但始终未曾彻底灭绝,它体现的是传经之人的坚韧不拔和绍述微学的精神。有斯人,斯有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