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一卷览尽潮剧风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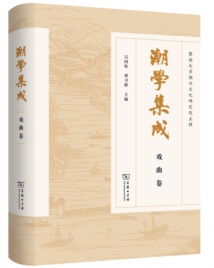
定价:¥168.00
一卷览尽潮剧风华
《潮学集成·戏曲卷》除卷首导言外,共收录文章51篇,分为“潮剧溯源”“潮剧艺术本体”“明本潮州戏文”“声腔、音乐与唱腔”“行当与表演艺术”“剧目与演员”六辑,展现潮学研究中戏曲研究的突出成果,总结回顾潮汕戏曲的发展脉络,以为推动潮学研究的不断深化提供借鉴。
潮音戏寻源
萧遥天
潮州之乡土戏剧,当推今日盛行之潮音戏为代表,其余若唱秧歌、关戏童,乃前代雏形之遗存,未可列于纯粹之戏剧者也。潮音戏颇多异名:曰白字戏,因潮州旧有正音戏,曰白字,所以识别于正字;曰童子班,则以其优伶泰半以童稚充之而名,南洋群岛恒有以苦班戏名之者,又指其俳优多施夏楚严教而成者也,国人则咸呼为福佬戏,谓此乃福老人之戏也。观夫潮音之为戏,唱调柔曼,鼓乐清扬,稚声清脆,童优灵妙,持与各地戏剧比较,实能自成风格,且与潮州之地理环境及民族性相谐。岂乐记所谓“以爱心感者和以柔”者耶?潮音戏流布之区域,除大埔外几遍于全境,以逮南洋群岛、闽南、琼崖诸地,间有至港沪演出者,盖凡潮人足迹之所届,莫不有其流播,其观众,何止千万计也。然潮州因何而产生此种戏剧?自来演者自演,观者自观,弗求甚解,蒙昧既久,考寻綦难。世俗拾取优伶典实,谓唐书明皇曾选来部伎三百人教于梨园,声有错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子弟,潮音戏以至百戏,皆轫始于是云,此腐儒之论耳,不足援以为据。溯厥源流,潮音戏岂绝无依傍,凭空产生者耶?余窃憾向时士流,鄙薄戏剧为稗官小道,不屑论列,致令采风问俗之政,湮沦沉霾,因欲钩稽载籍,著之篇章,且礼失求诸野,此数百万潮人共有之乡土艺术,数百万人之口耳相授,乃一部活辞书,苟就中理棼廓雾,亦当必有所获。爰就乡老、伶工,以及乡人之老于江湖者,博访周咨,以所得片段消息,连缀归纳,复旁搜僻索,与昔日流入潮州各种戏剧比较研究,探幽钩沉,斩尽葛藤,以冀重见青山之本来面目。
夫古之戏剧,始见巫舞,献神娱人,渐成风习,《诗经》十五国风地方剧之权舆也。秦汉以降,设乐府,陈百戏,杂百乐,变夏声,代面,拨头,踏摇娘等,雏形剧渐次以兴。其后唐置梨园教坊,诗变为词,自宋如下,词变为曲,曲复有南北曲之分。戏曲至元代始具规模,明清以来,渐次发展。今全国各种地方戏剧,虽派衍纷繁,溯其源流,皆南北曲二宗之流变也。故中国之戏剧,明以前为一总源,分立门户,则为明以后事。潮州戏剧之滥觞,固肇自有明中叶。而潮音戏较潮州外来诸戏,又为后起之变体也。
晚明以来,异方戏剧相继叩潮州之门。正音乃自浙东赣南趋闽南,接诏安东山诸县而至。西秦、花鼓乃自湖南入粤北,经惠阳、海丰、陆丰诸县而至。外江则自安徽播赣南、闽西,经客族之嘉应州而至。花鼓在古远之时,久已变为潮调秧歌。若正音、西秦、外江,其始也各以异方本色为戏,过境演唱,继而州人习其腔调,踵其旧规,自组戏班,亦榜正音、西秦诸名,辗转相承,面目渐变。唯白恒混入土语土腔,台词自成戏棚官话,笑柄百出。外江因入潮稍晚,腔板音韵,典型保存,然亦有咸水班,与西秦、正音之末流犹一辙耳。
考此种异方戏剧渐与囝腔混合之现象,实为潮音戏萌蘖之初征也。潮音戏之组织成为成熟之戏剧,年代虽无可考,然清乾隆时李调元著《南越笔记》云:“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戏。潮音似闽,多有声而无字。有一字而演为二三字,其歌轻婉,闽广相半。”是时已见潮州戏之称矣。大抵潮音戏之逐渐形成,始于清初,而其确立则历史甚浅,询诸乡党八十老者,佥曰:五十年前潮俗列正音、外江、西秦等戏为四大班,而潮音戏地位殊下,聘金甚低,士大夫未置齿颊间,独妇孺喜之,未厕大班之选也。譬如祀神赛会,其原定系聘演四大班戏者,及后因故障改聘潮音,则依例凡四大班一台,潮音须增抵一台半,其声价远逊诸班,乡社赛会账簿历历可稽,此一也。旧时之乡社大赛会,如演梨园多班,诸登班台,各布置妥当,必待正音班开锣,潮音班最末,收锣亦如之。是以行辈为序,应推正音班资格最老,潮音为后进,此二也。父老复言:五十年前之潮音,道具服饰,均较诸戏落色,戏袍非黑布镶白则白布镶黑,朝服多以白布绘彩,今澄海外砂王姓尚藏存此类服饰。故潮谚有嘲潮音戏者云:“戏囊九脚(只),戏角十三,老生七十一,花旦十三,相刣(对仗)出耙担(扁担),扮仙穿长衫。”言其道具脚色,零落不堪,须生耄耋,花旦童稚,以扁担充刀枪,便服当戏袍也,恶谑刻画,淋漓尽致矣。当时潮音班优伶生活至苦,每于收锣后,辄至人家乞取腌菜佐膳,旧亦有“陈世美讨无咸菜”之谚,以饰演陈世美之薄幸,惟妙惟肖,妇人痛恶之,忘其为优,竟拒所求,事虽谐谈,亦可觇其草创时之现象,此三也。据此三者,足征潮音戏之酝酿,虽近二三百年间事,而潮音戏之成熟,则不逾百年,更推而进之,潮音戏之酿成,亦可谓乃融化外来诸戏剧者也。试就诸剧探索,清其本源,察其演变,则知潮音戏者其本质源于秧歌弹词,铸入于正音戏之楷模,而其他西秦、外江诸戏,皆与有影响而合流者也。今就管见,次第陈之。
潮音戏与正音戏之关系
关于潮音戏之源于正音戏,论据约有数点。其一,现在之潮音各班,其开锣之吉祥戏(艳段),若《唐明皇》《八仙寿》《仙姬送子》,及收锣之《团圆》诸出,皆说戏棚官语,脚色中之净,则无论在任何剧出,俱以假嗓说官语,此老狐化人,尾尚未掩,旧时正音之遗腔,仍未尽泯除也。其二,正音戏之做场,台面中央挂三竹帘,潮音戏亦循其旧规,挂三竹帘(改用画幕为近廿年事)。按此盖祖肇于元剧者也。忆昔曾见青楼、辍耕录诸书,说元代女优有称珠帘秀、赛帘秀、帘前秀……者,是演剧优伶当在帘前,犹昆戏之在红氍毹上也。复观潮州其他各戏之做场,台中咸挂红帐幕,与正音潮音迥异,是乃正音潮音之标帜相同也。其三,正音戏每唱词之句末曼声转折,或有帮腔,潮音戏也有帮腔。余固疑帮腔出于秧歌调,而渊源于湖南之花鼓调,粤北之春牛调,帮腔皆地方雏形剧共有之通则,而正音潮音乃受其混化而仿用之欤,是正音潮音之腔调相同也。其四,三四十年前潮音演唱旧编之戏目,所谓摘锦者甚多源于正音戏,如《刘咬脐》《打兔》(刘知远诸宫调、白兔记)、《包公会李后》《审郭槐》(抱盒剧金丸记)、《回窑》(薛仁贵衣锦回乡)、《认像》(琵琶记)、《和番》(汉宫秋)、《当妻》(风雪破窑记)、《破棺》(蝴蝶梦),均元剧也;《送寒衣》《冻雪》(韩湘子升仙记)、《高文举扫窗》(珍珠记)、《何文秀问卜》(玉钗记)、《活捉张三》(昆曲水浒),均明剧也。至若开锣戏之《八仙庆寿》(蟠桃会)、《京城会》(彩楼记)、《仙姬送子》《加官》以及《投江》《吊孝》等,莫不非元明杂剧传奇之旧,凡是皆正音戏之所擅演者,潮音戏或则袭其旧腔,或则以为蓝本。此正音潮音剧目之相同也。其五,现在潮剧仍其脚色为生、旦、丑、花面(净),戏剧术语如科、白、介、出、关目、装扮、起套、煞尾;称谓如员外、安人、梅香、小姐、老汉、老身、奴家、小人;口语如则个、少待、打听、打睡、怎生、知道;助字如用呵、了、生、的、吗,皆沿用正音戏之惯辞,与潮州方言迥不相侔。其行头(戏装)纯为明代衣冠,网巾尤为特征,更无论矣。其六,潮音正音,又曰白字正字,皆对举之名词,此显然系先有说正音之戏,后复有说白字之戏,白字盖因正字而生者也。余并谓正音之戏最先流入潮州,潮人听其唱白,为中原音韵,故命之为正音正字。西秦、外江接踵而至,其唱白亦雷同于正音者也,因其来晚,故各称之为西秦外江。唯潮音者正音之蝉脱化,乃用对举之字眼区别之,称白字戏。其七,正音戏之末流兼唱潮音,午夜顿改潮调,廿年前残存之老三胜班、新荣丰班皆如此,余曾及身听之,此亦正音演化为潮音,化蛹而尚未变为蛾之现象也。余推想潮音之入戏,其始系正音采编民间秧歌之类以为付剧,故在午夜以后演之,视为棚尾戏耳。后因妇孺喜此,且戏目渐编渐多,遂脱离正音班自立门户,组成潮音戏,此潮音产生之近因也。据上七点,其递嬗之迹,可以窥见潮音戏之主源矣。
潮音戏与秧歌之关系
当正音戏未曾播及潮境以前,潮州民间已有其原始之雏形戏剧若关戏童、揲三姑、斗畲歌、唱秧歌,乃其权舆。此种农家娱乐,常当农隙祭神欢庆,就田陇间行之。古者优出于巫,巫之事神必用歌舞,献神也以悦人,是时所谓歌舞,乃民间野生之艺术,秧歌、畲歌、打野胡、打夜胡之类是也。今日潮俗春二三月,农村游神赛会甚盛,游神岂古之傩乎?论语有“乡人傩”,傩,驱疫也,今游神常有秧歌舞,扮成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之队伍,打鼓击节,且舞且歌,此宋人笔记常称打夜胡、打野胡之遗也。秧歌之后列,又有扮为男女僧道之短剧短出,称秧歌后棚,是则湖南花鼓与本土畲歌疍歌合流之产物也。余疑湖南之花鼓流入潮州民间,应较正音为前,其通俗淫亵与农村环境吻合,最易为大众所接受,故在极短时间内即变为纯粹之风土艺术,粗忽视之,其本来面目,几无迹可寻。此种秧歌戏,初系农村岁时应景之娱乐,后逐渐演化,亦有就田野草草搭台演唱,其戏衣道具咸盛于农家摔谷之椭圆大桶中,台上以晒谷之竹席遮顶,廿余年前南山乡僻犹有此种戏存在,称摔桶戏,今日之竹装戏,亦蝉脱于摔桶戏者也。
故曰:正音、西秦、外江,贵族艺术也,其流入潮州,接受之者为士绅阶级。花鼓秧歌,民间艺术也,其流入潮州,接受之者则为农民大众。此雅俗贵贱,尽有分野。秧歌戏既融化花鼓调,最先成为纯粹之乡土戏,复窃取正音戏之戏剧组织,囊括其形式及内容,遂产生潮音戏。此为二百年以上之事,今日已数典忘祖,派衍绵邈,几于莫可诘究,然而仔细揣摩之,则其合之迹,显而易见。其一,今日凡潮音班俱祀有一神,称田师爷,或田元帅,史无可考。或云唐大宝时曲师,见宠于明皇者,更闻之老伶工,其言甚为诡异,谓相传最始之教戏者,授曲甫成,化为青蛙而隐。前说既属附会无稽,后说则是田元帅乃青蛙神也。凡潮音开班,必祀此神,初点香火,乃就田野取田土一块,归置香炉中,牲果香烛祭之,一谓之请元帅。乡俗每春间之起秧歌与秋季之关戏童,皆祀此神,请元帅之仪式亦如之。关戏童亦称关田元帅。此为潮音与秧歌及关戏童同出一源最现实之证据。窃疑此田元帅本来必为关戏童所先祀之神,由而传于秧歌,再传于潮音,以其为迷信风俗,历久未敢稍改,故一脉相承,至今弗变也。忆农家祀青蛙,蒲音仙聊斋志异数数言之,其为乡村淫祀,乃确切之证佐。其二,潮音戏中之小调,乃秧歌调也。如桃花过渡之“正月点灯笼”、十二月调,与清吴震方岭南杂记所举潮州秧歌采茶十二月调为一类。“桃花”调每段句末合以“倪了倪”之帮腔,邪许之声,尤为村歌之特征。(潮乐之曼,极似湖南之花鼓调,其稗贩此种花鼓调,入于潮音者,则秧歌戏也。此于前章已详阐之不赘。)
潮音戏与畲歌疍歌之关系
潮州之土著,陆为畲民,水为疍户,故畲歌疍歌,为最原始之潮州民歌,亦潮州民歌的主流。今日之一切民间歌谣,犹概称之为畲歌,畲民刀耕火种,原山居之农民,畲歌亦犹畲民种秧之歌也。此种本土之秧歌,后来与异方之秧歌(花鼓)合流,成为秧歌戏,复与正音戏合流,便成潮音戏。畲歌之与潮音混合,李调元南越笔记亦记及之,其叙潮州戏之歌云:“其歌轻婉,闽广相半,中有无其字而独用声口相授,曹好之以为新调者,亦曰畲歌”,按畲歌应为潮州戏本有之老调,李氏以为新调,乃倒果为因也。今日之潮音戏中,仍有畲歌之成分存在,如桃花过渡之桃花姐与渡伯“斗畲歌”全段,如滑稽戏中常见丑角出场打诨之“扣子”及百鱼名歌、百鸟名歌等,皆畲歌也。疍户舟楫而居,捕鱼为业,疍民最喜歌乐,女之妍者多流为倡。李调元南越笔记,有及于疍歌者,如曰:“风俗好歌,儿女子天机所触,虽未尝目接诗书,亦解百口唱和,自然合韵,说者谓粤歌始自榜人之女。”又曰:“疍人亦喜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近人钟敬文辑有疍歌一卷。顾潮州旧时疍歌甚盛,道光咸丰年间,潮安湘桥之六篷船,为烟花之薮,六篷船又呼疍家姨船,疍女多簪鱼卵兰,口嚼槟榔,度曲卖媚,歌舞侈丽,不让秦淮,黄剑有六篷船诗记其事。潮阳亦有此类船踪迹,道光时陈作舟潮阳竹枝词有云:“后溪水比前溪清,前溪月共后溪明,处处疍船争向月,三更不断管弦声。”是,疍歌必有影响于潮州戏,殆无可疑也。(有人疑今日潮音戏之做科,其台步恒三步踏前,三步踏后,摇曳动荡而进退之范围则甚固定,凡对唱单唱,莫不如是,极肖艇中唱戏之状,是岂疍女做科遗留之乎?姑志之以待证定。)
潮音戏与关戏童之关系
潮音戏班之组织,最特殊者,即脚色除丑、净、须生而外,全为童伶,此古代雏形戏剧关戏童之遗型也。按古之祀神歌舞,必以童稚充之。稗官小说,常记用童男女祭妖故事,史记本纪亦载秦始皇遣方士徐福以童男女五百人入海求仙药,皆取其为神圣纯洁之象征也。及巫之演变为优,依然尚童稚故习,古代以侏儒充倡优,注家多曰:“侏儒,短人也。”初常觉不能可解,岂世有短人若是之像耶?实则侏儒者,盖童稚之易词耳。今潮州之“关戏童”,仍承古代侏儒倡优之旧,潮音戏者,关戏童之再生孙也,亦仍关戏童之旧。此殆童伶来源所自来欤。再者,潮音戏以潮音平喉入调,亦关戏童之遗,因关戏童原始之乡土戏剧,其所唱若非疍民之歌,则为种秧之歌,皆以方言顺口唱出者也。及夫湖南之花鼓传入,其音调关目,虽为潮州乡土戏所吸收,但异方语言则非农民所能了解,故自始亦以本腔唱之,非若正音、外江、西秦诸戏,因鉴赏者系士绅阶级,始终保存其旧腔及其末流,虽渐变质,仍可见其潜移默化之迹也。关戏童吸收花鼓调,自始即取消其方言成分,保持吾固有之本音;迨与正音戏合流,亦仍一贯保持其固有之本音。且平喉出自童伶之口,清脆甜腻,听之醰然欲醉,最为妇孺及一般民众所爱尚也。
潮音戏与弹词之关系
潮音戏之戏文,与正音、外江、西秦以至平剧、昆剧等等殊异,其编剧之七言句何其多也。夫诗变为词,词变而为曲,今日各种戏剧之戏文,多金元词曲之变体,其脚本有唱有白。唱者,词曲之牌子也。而潮音戏之脚本,以余观之,应区别之为宾白、唱白、唱词三种,更为清楚。潮音之唱词即唱牌子及小调者,每出戏中人乐弹唱者多七言句,间有变为三言或十言者,三言乃七言之断截,十言则七言之附余也。顾是乃弹词之旧体,潮音戏大量仿谓之,余姑定此类之专称为唱白,以示别于牌子小调者也。潮州民间,自来唱弹词之风甚盛,俗呼为唱“歌册”(潮安李万利藏有潮州弹词“歌册”刻版数百种,据称现尚流行者约七十多种),今日之家庭妇女与南洋侨民犹悠扬吟诵,酷嗜未已,惟不协乐调,顺口朗歌而已,然弹词古盖亦可以协乐者,若南词、花调,可资借镜也。杭俗遗风:“南词者,说唱古今书籍,编七字句,坐中开口弹弦子,打横者佐以洋琴,每本四五回,称为唱书先生。”又云:“花调亦以五人分脚色,用弦子琵琶,洋琴鼓板,所唱之书,均系七字唱本, 其调缓而且烂,每本五六回”。今闽南之卖弹唱七脚戏,皆同此类。潮州走唱班亦弹唱之变象,旧时唱弹词,今则易唱潮曲耳。
潮州之有弹词,时间未可考,惟较先于潮音戏之组织,则毋庸置疑者也。潮音戏文之体裁,何以大部分模仿弹词?其主因不外惮于词曲之填制,必按宫谱,审音正纽,平仄抑扬,此在潮州之士大夫已非所长,况旧时潮音戏文之编制者,多为伶工乐工,浅学猥鄙,声律之道,更非所习者,手头之弹词,固可弹唱,复有脚本可循,因乃仿制之,甚或剽窃割裂,例证甚多,不胜枚举。最可笑者,则连与弹词形式同样之七言句,又系最通俗之版本,如唐诗,千家诗等等,亦搬入戏文,遍听潮曲,常突来“春宵一刻值千金”“云淡风轻近午天”之句,往往为之忍俊不禁。
潮音戏之兴起与其他戏剧所予之影响
自潮音以秧歌弹词,陶铸于正音戏之楷模,组织而成戏班,潮州境内流行之各种戏剧,渐受此新兴乡土艺术之打击,日趋没落。四十年前,外江戏风靡一时,正音、西秦即遭其排挤,江河日下,终成绝响。及夫潮音之起也,外江亦步正音、西秦之后尘,渐趋销沉之路。平心论之,正音、西秦、外江,其艺术水准高于潮音,然流尚所趋,已多倾向低级趣味,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抑又何故耶?此无他,潮音乃以独有之潮州乡土风格擅胜,土语土腔,非特妇孺易晓,即潮州人莫不好之,观众既伙,欲阻其勃兴,其可得乎?乡老告余,潮音戏初盛,乃在清季光绪间,方军门照轩绥靖潮州之际,是时仅普宁方氏一家,便拥有潮音二百余班。在今日言,外来诸戏虽相继衰落,然胜清中叶以后,固有甚长之时间予潮音以观摩借镜之作用,考今潮音戏中,仍含蕴有诸剧之成分也。正音系潮剧前,固已论之,而西秦之戏出,若《张古董借妻》《戏叔》《卖胭脂》《戏凤》等,外江之戏出,若《辕门斩子》《刺王僚》《黄巢试剑》《薛蛟收狐狸》《收浪子尸》《杨天禄招亲》《苍蝇记》等,潮音戏均有演唱,皆袭取为蓝本者也。从前黑净唱曲必转用外江腔,近更变本加厉,新编之全连剧出,常常外江调潮调轴轳参用,丑生旦亦唱外江调矣。晚近廿年来,潮音戏复受平剧、粤剧、电影、西洋剧之影响,其取于平剧者,若戏装、武行、锣鼓(有时亦改打京锣,以资醒目),剧出若《玉堂春》《红鬃烈马》《孟丽君》亦尽量搬演。其吸受于粤剧者,则惟音乐一道,盖粤曲喧阗,而潮音文静,本格格不能相入,然粤乐多奇彩泛艳,其声新美有逾于潮音。潮音戏之过门辄取以伴奏,乐器中新增之二胡,亦粤乐器也。潮音之时装剧多取材国产电影,若《孤儿救祖》《姐妹花》《空谷兰》《人道》《火烧红莲寺》,其尤著者也。戏帘之改用画幕,及立体布景,台前之增一垂幕,以为分幕启闭之用,即窃效法于西洋戏剧者也。如是,则吾人今日之潮音戏,实为中国戏剧艺术之混血儿,非复野生艺术之旧矣。
(原载《潮州志》1948年稿,《戏曲简讯·戏曲研究资料》1958年版转载)
京ICP备05007371号|京ICP证1508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编:100710|E-mail: bainianziyuan@cp.com.cn
产品隐私权声明 本公司法律顾问: 大成律师事务所曾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