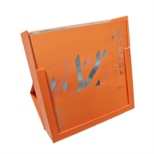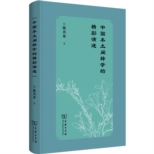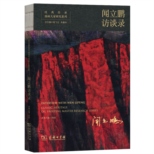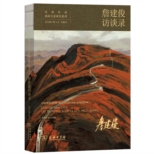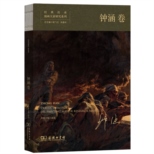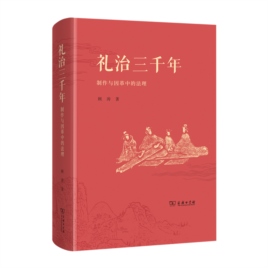以文学作品来讨论社会历史问题,法学界已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并有学者在理论上进行过总结与评论。我认为苏力以电影《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为对象展开的农村法治现状分析堪为成功的典范。在苏力看来,“以文学艺术作品作为素材来进行法社会学研究不仅完全可能和可行,而且具有一些独到的优点” 。哪些独到的优点,到了他十年后出版《法律与文学》的时候,做出了明确的交代:“文学作品或历史故事,由于其浓缩和象征性,反而可能为宏观理解和把握历史提供一种以史料为中心的传统史学难以替代的进路。” 如今我们要讨论的新乡绅问题,尤其是对于探索新乡绅的内心世界,以及乡绅与村民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文学作品的优势进一步显现出来,这是大部分史料,即使是回忆录、访谈和口述等都很难匹及的。
刘庆邦与贺享雍可以作为当代乡土小说家的两位重要代表。刘先生曾以《平原上的歌谣》(2004)、《遍地月光》(2009)等乡土小说享誉文坛,《黄泥地》的问世可以看作是他的乡村三部曲构建完成的标志。刘先生 19 岁之前在农村长大,之后又有煤矿工作的经历,多年来对乡村的体察与发掘到《黄泥地》中房国春形象的塑造,可谓臻于时代的巅峰。贺享雍则在 1996 年即创作出川味长篇乡村小说《苍凉后土》,同题 19 集电视连续剧使其在民间赢得了口碑。近五六年来,贺先生反刍前半生在农村务农、工作的切身经验,全力投入叙事体长篇系列小说《乡村志》十部的写作,《人心不古》即是其中第三部。两位作家一在北京,一在四川,几乎同时各自进行着独立的创作,两著差不多同时发表。《黄泥地》中的房国春和《人心不古》中的贺世普,一个是县第一高中的高级教师,一个是县重点中学的校长,两人均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县上的人脉与社会资源也比较丰富,一个在房户营村,一个在贺家湾,无疑都属于“功成名就的中老年人”的代表。刘庆邦在小说中已明确指认“房国春之所以热衷于管村里的事,是他有乡绅情结”,而贺世普,形象一呈现出来便被学者称之为“现代乡绅”。两个人物形象,基本上可以合二为一。
房国春与贺世普回乡后所取得的绩效,应当可为新乡绅们鸣锣开道。贺世普从县中校长的职位上退休,家乡的村书记便请他回老家,新成立村矛盾纠纷调解小组,并出任组长。贺世普回乡后确曾大展身手,在调解贺中华、贺长安两家纠纷(险些酿出人命)、整治村里公共卫生、组织春节戏班演出、阻挡强挖村头古树等村中大事上,体现出了连村书记在内任何一个村内人员都无法取到的成效。用村书记的话说:
贺中华和贺长安两家的纠纷我调解了大半年,路跑大了,嘴巴磨起了果子泡,他们一点也不理睬我。可昨天老叔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的纠纷给摆平了!所以我说老叔是啥子水平?那可是飞机上挂茶瓶—高水瓶(平)!老叔随便拿张纸画个人脑壳,都比我面子大!
贺世普的“面子大”“高水瓶”,在房国春身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由于房国春在房户营村德高望重,村里出现一些连村干部都处理不了的纠纷,他能妥善处理”,在村民们眼中,“他是房户营村最有胆量的人,最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堪称是房户营村的中流砥柱”。 这便是新乡绅所具备的典型特征,他们见多识广,曾经叱咤过风云,曾经站在聚光灯下过,如今回乡博得的面子、所具有的威望、背后的柱础正是来自徘徊在一亩三分地中的村民们对他们的钦慕、羡艳、攀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