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扎实、准确解读鲁迅与许广平通信的图书,一本揭示鲁迅内在精神的指南。
有一段时间,人们对于鲁迅的理解,还仅仅放在公共语境里进行的,不太注意其私人话语的意象所指。或者说,公与私的界限是朦胧的。理解鲁迅的难度,是话语带有界定性,分不清这种界定,意思可能就走向反面。记得四十多年前,王得后先生出版的《〈两地书〉研究》,就沉潜在博物馆的史料里,从手稿里摸索鲁迅思想的来龙去脉,理解方式发生了一丝变化。这一本书以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为基础,发现了别人很少注意的缝隙。我还记得初读它时的感觉,在正襟危坐的气候里,忽然有异样的光泽过来,调子有些不同了。
鲁迅之于后来的国人,牵扯着文化神经里敏感的部分,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也带着个体超时代的精神内力。认识他,倘没有对立的和回转的视角,其难度可想而知。王得后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绕过习惯的思维逻辑,放弃大词的使用,以文本为出发点,提出鲁迅存在一个人本的立场,即“立人”的思想,这对于后来的影响很大,以至我们几代人都在这个思路里。这“立人”的思想,是从鲁迅内部世界出发,考察思想者的一个心得。许多域外思想与本土话题都沉积在这里,构成互为透视的关系,公共语境和私人语境不同的隐含交织着,单一逻辑似乎无法对应其形态了。
正是考虑了这样的复杂性,王得后所悟之境就不是唯道德主义的,思考的焦点直指存在的本然。那便是:“人的第一大问题是生死,其次是温饱,再其次是男女关系。而人类又只能群居才得以生存,一切困境,由此滋生,由此蔓延。”理解孔子如此,感受鲁迅亦复如斯。只有阅读《两地书》,才看出鲁迅世界最为本然之所,如何看世,怎样对己,在不测的世间对付着各种潮流,保持自己的定力。他内心最为本色的部分和最为柔软的部分,于此都可感到。而智慧的光泽照例与其文学作品一般,有着罕有的内力。
好奇于鲁迅作品的人,常常会问,为什么他有如此的气质和风骨?这大约和自己的生命记忆有关吧。他的早年婚姻,是一个悲剧,母亲包办的结果,便是一个苦果,也只能吞下。许多文献记载了他对于无爱的家庭的态度,这些影响了他的生活状态也是自然的。当许广平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才发生了变化,这直接扭转了他后来的生活之路。他们由初识到交往,由师生之情到爱人关系,其实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沉重与苦楚之影依稀可辨。那些对话,带着丰富的内蕴,是极为特殊的文本。我们知道,鲁迅自己编辑出版的《两地书》,其实是有所增删的。但那并非私人的甜言,却多的是人生感叹。顺着其间的蛛丝马迹,看出两人对于读者和社会的态度。在私人文本进入公共空间时候,什么该保留,什么是要隐藏起来的,也看得出他们的为人之道的边界。
我们在鲁迅杂文里看到作者之影,是坚毅与决然的时候居多,但看他与许广平的通信,则感到其世界犹疑、悲悯和自我否定的情感的浓烈。王得后发现了这是研究其思想不能不面对的地方,许多在文学作品里没有的思想片段在此一一显露。那时候鲁迅手稿还没有公开,利用鲁迅博物馆原始资料和鲁迅墨宝,细心对校,有发现的欣慰,也多意外的所得。有许多空间没有被研究者注意,时代语境偏离了远去岁月里的遗痕。不仅同时代人理解鲁迅不易,后代人要走进他,亦有重重障碍。王得后从众多人的文字中感到了世间对于先贤的误读之深,因而要回到问题的原点中去,从最为基本的事实出发,考察人的心绪的变化。《〈两地书〉研究》在多方面显示了良好的风范,乃至成为研究鲁迅自我意识的标本之一。
从文本的变化看鲁迅的婚恋心理,推及精神的内质,是王得后这本著作的特色。经历了早期的婚姻,鲁迅对于自己是一度悲观的。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那篇《随感录四十》,就深叹于无爱的婚恋的残酷。当许广平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开始并没有勇气接受那巨大的暖流。但在渐渐交流中,彼此都感到内心呼应的地方殊多,不久已经可以进入深层的讨论了。王得后在原始稿件和发表的文字的对比中,看到了两人的情感的微妙变化,诚与真的词语,还有着智性的东西。鲁迅处理个人情感的方式,令人肃然 的地方殊多。怎样的相濡以沫,如何讨论“牺牲”的话题, 都触目可见。读这些文本,没有嗅到流行的意味,那些书信和旧式读书人的感觉也是有别的。既看到了鲁迅的敏感, 也指出那含蓄、委婉、朴素的风格的价值,“好用欲亲反疏 的曲笔”,多了表述的趣味。这需要慢慢品味才能感到。在 家庭问题上,鲁迅被新旧道德所吸引,妥协的一面也是有 的,由其有限性出发,而非圣人的角度阐释对象世界,所 得的结论也自然不同的。
在鲁迅那里,个人情感是与社会形态和历史形态交织在一起的。这让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观点,人是社会的动物,一旦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生命便被退到动物的层面。古今的社会,大约都是如此。所以,鲁迅在讨论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与情感问题时,背后都有长长的影子,历史的与时代的印记都可在此找到。在较为私人化的空间里,对于社会问题的描述反而更为真切,由此也可以感到那精神的深。当编辑《两地书》的时候,鲁迅也意识到自己所说的东西,未尝不是在文学作品里要表达的部分,只是倾听的对象有别罢了。翻阅他给许广平的诸多信件,就可以发现其内心鲜为人知的一面。也可以解释其杂文激烈的地方,其实也是最有爱意的表达。不懂此点,那是难以走进其世界的。
《两地书》闪动的思想,当可看成是理解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或可以注释鲁迅文本里深藏的思想。看他在《新青年》《语丝》上的文章,对于旧道德的批判,是带着痛感的低吟,有时候也夹杂着某些“抉心自食”之态。旧式生活,造成了无数无爱的婚姻,在女子方面,也多无辜,而觉醒了的青年寻自己自由的路,也常常有大的代价的。以清教徒的办法处理这个难题,乃大的不幸,人总要有自己的路径才是。我们看他的一些杂感和小说,每每涉及两性的爱,都拖着长长的历史之影,倘不是己身之苦的存在,自然不会有类似的感受的。而他在思考伦理与道德的时候,都非从外在概念出发,一部分来自自己的一些经验。有时候也可感到,他是带着肉身的痛感而面对人间的是非曲直的。当我们从流行的观念把握那些文本的时候,往往走到了对象世界的另一边,反而越发难见其意了。
人的生命之路,关联着思想与存在的诸多难题。鲁迅在己身中,意识到社会以及历史里的复杂之思,对于社会的许多看法,是从自我的生命体验里形成的。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都折射于此。所以,在爱情的对话里,没有那些卿卿我我的表达,而多是一种切实而无伪的谈吐。书信中透露的是对于生活的极为丰富的认识,至今阅读,亦幽思诱人。在道德观上,鲁迅认为:“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因了这样的基础,不论在后来的文明批评还是社会批评中,精神都是有一种定力的。看似偏颇的文字,其实有大爱精神。王得后一再感叹,在鲁迅的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中,人性的美质从来没有消失过。在为私与为公方面,有一个本色的东西在延伸着。不过,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时候,鲁迅的精神表达并非私人对话那么平和,
激愤的调子反而更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在精神放达、飘动的时候,初始的逻辑是不变的。不然可能被文章的表象所惑。优秀的思想家绝不是在流行的模式里陈述人间是非,而是有着深的精神内省与突奔。在词语微妙变化中看世界观与审美观的原色,是十分重要的。
从词语改动中看修辞的策略,是走进鲁迅的办法之一。流传中的鲁迅的样子看似狂狷,而发表的文章,也是顾及社会效果的。第一封信中,许广平的话很锐利,毫不掩饰对于时局与学界的看法,用词也比较生猛。她将教育界佞人说成“猪仔行径”,发表时删掉了。鲁迅以为文字要有分寸,不可过于猛烈。王得后说这是鲁迅“壕堑战”理念的折射,这是对的。第五封信中,原稿“现在固然讲不到黄金世界”后加上“却也已经有许多人们以为是好世界了”。此句改得更有逻辑性,是对于麻木于现状的人们的一种批评,阅读此处,能够发现表达的周密,而现实情怀渗透于纸面。第四十七封信,原稿“右派”改为“旧派”,“右倾”改为“顽固”,王得后以为是鉴于国民党已经背叛了自己,词语的含义就不同了。旧文新刊,与环境的对话性也是必要的。第五十七封书信中,提及“研究系”的地方,后来出版时都删掉了,主要是考虑环境有所变化,便以“现代评论派”代之。王得后的解释是:“显然是在文网极密的时候为了隐去政治色彩的做法。”从这类改动里,有时空变化中的表达位移,也多社会责任的一种。其中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热心,依稀可辨。
《两地书》是深入了解鲁迅私人语境的典型文本。鲁迅关爱人,并不强加什么己见,充分理解青年的心。许广平在第二十三封信中说,有同学要介绍自己加入一个政治团体,虽然兴趣有所接近,但害怕自己被过多束缚。鲁迅的回答是:“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只有‘安那其’是没有规则的,但在中国却有首领,实在希奇。”书稿发表时,这一段被删掉了。而王得后则感到,这里有鲁迅对于政党文化的态度,在二十年代的中国,进步的青年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鲁迅是别有看法的。由此可以生发出思想者鲁迅颇为主要的意识。他在杂文中所强调的诚与爱,其实也是做人标准。联想起他后来在左翼联盟中的表现,依然如此。多年前在爱人面前的真言,多年后也贯穿始终。人很容易在职业选择中迷失自己,在社会大潮里,保持自我个性与社会责任感的统一,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
从增删之处看出鲁迅对待自我的态度,也是《〈两地书〉研究》十分注意的部分。有一些话,因为涉及许多人际关系,成书时被删掉了。比如第六十六封信,鲁迅说“因为我太不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所以看不完”。这是自我批评的话,说明在与他人出现矛盾的时候,自己也并非不知道一些自身的问题。第七十九封信,谈及“不过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愤话”,对于内心的灰暗感是有所警觉的。原信与修改的文字对比后,发现界定更为清楚,表述是带有分寸的。王得后认为都涉及自我解剖,值得注意,并非没有道理。第一百〇四封信则说到在厦大独来独往的样子,一方面认为“旧性似乎并不很改”,一方面还得意自己对于校方的搅乱。作者清楚,这种性格带有两面性。鲁迅既释放着忧愤之情,也意识到具有破坏性。这种悖反的情形,在自己是一种无奈。删去此类文字,也许觉得不要过于炫耀自己也未可知。《两地书》的对话,是深的、真的表露,鲁迅对于自己的问题的袒露,也惊人得可爱。在人间的难题里,重要的是寻找克服的方式,其间也有对于自身弱点的剖析。王得后在研究此书过程中,一再惊讶于鲁迅的坦诚,以至感叹之音飘出,中国古代的许多先贤,何曾这样表述过内心的原态呢?
在《两地书》中,除了个人感情,对于教育、学术、政治文化多有涉猎。在梳理其间的观点时,王得后感慨那些论述的精神之深。比如言及大学的教育,就认为是适应环境的工具,且与人性的全与美,都有很大的差异。重要的在于“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但这不过还是理想的憧憬。“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将叛徒处死”。在“五四”过后,舆论界的复古之风很盛。比如“坚壁清野”主义,就是以“收起来”的方式,防止男女接触,所谓避免有碍风化之事。鲁迅以为殊为可笑。人的个性发展,做好性教育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之一。如果人人都成了呆相,那是十分可怜的。而他的主张学生做好事之徒,与流行的教育方式是有别的。看鲁迅与许广平间的通信,主要提倡的是个性精神,对于旧文明的攻击不遗余力。他们要在没有绿色的地方犁出春之生机,都是和环境格格不入的。而那种突围的方式,都是颇可借鉴的。
应当说,在众多书信里,虽说是十分私密的对话,而从中折射的社会性的话题,是那么丰富。王得后的许多论述,都是由近及远,从私到公,深深浸在那阔大的世界间。他对于鲁迅“心灵深处的政治意识”的把握,颇多感慨,是进入先生世界的重要入口。因为那时候彼此都在教育界,涉及学界的当然很多。从大量对话中,可以看到鲁迅与学界之关系,他对于“研究系”“现代评论派”都有警惕,批判的语气是重的。在北师大风潮中,国民党与“研究系”之间的斗争是激烈的,知识人在那时候不可能不有自己的立场。但后来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立场发生变化,鲁迅与许广平受到的冲击亦可想而知。从他们的交流可以看到,鲁迅曾希望革命党人开拓一个新天地的,所以对于守旧的“研究系”颇多反感。而那时候的知识人,倘有良知,不能有自己的现实态度。所以鲁迅说,“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顾颉刚虽然声称不谈政治,但看他与胡适通信,也不无趋时之言;胡适不是想专心著述吗,看他后来的文章,与政治纠葛也是深的。
钱理群曾将王得后视为自己的几个重要知己之一,他在点评《〈两地书〉研究》时说,作者不仅细读颇有功夫,关键是不断提出各种问题,在新时期为鲁迅研究开了好头。这是中肯的。许多研究鲁迅的书,时过境迁,已经无人问津了。但像《〈两地书〉研究》提出的问题,今天依然困扰着知识界。比如如何面临人生的“歧途”与“穷途”?怎样坚持“壕堑战”?“人道主义”与“个人无治主义”平衡点在哪里?这里不仅仅牵扯到人生哲学,其实也有生存智慧的问题。王得后是带着自己的这代人的疑问走进鲁迅的,要疗救的也有自己的痼疾。这个过程,也推及社会的改造诸类话题。每个细节的追问都非空泛之思,先贤的遗产被一点点凝视着,一些心得也可视为《鲁迅全集》的注释。我一向认为,研究历史与个人,远远的静观还很不够,需要的是生命内觉的拷问和周围世界的考索。王得后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那一代人对先贤的体味有特别的角度,根底是要改造社会。现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此大抵是隔膜的。
孙郁
二〇二三年三月四日
序 言
当这些芳泽杂糅的文字即将问世的时候,我感到高兴,感到惭愧,感到不安。尤其怕想象师长、朋友和熟人翻看这本书时的眼睛,可这样的眼睛偏偏常常闪烁在我的心头。
一九七六年暮春三月,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到了在北京的鲁迅研究室。我怀着感激,也异常兴奋,现在想起来也还是这样。大概这一辈子是忘不了的了。
由于参加编辑《鲁迅手稿全集》(书信),我读到了鲁迅与景宋的通信的手稿复印件,才知道他们在编定《两地书》的时候,对原信作了许多增删修改,特别是景宋的信,文字的修改很多,内容的删削也较多,有的信常常是整段整段地删去。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不是为了藏匿什么隐私,因为所谓隐私的东西,原信中一点也没有。为了了解编者作了怎样的增删修改以及为什么这样增删修改,我于是作校对,并尽量写出两者不同的地方。
那年秋天还争论了一个问题,就是鲁迅致景宋的书信即《两地书》中他的原信,收不收入《鲁迅手稿全集》。不收很可惜,又使《全集》不“全”;收嘛,又与《两地书》不同,而且既然修改后才出版,意在不按原信发表是显然的。我当时是不赞成收的。除尊重原编者所作的增删修改而外,还想到鲁迅说的“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这样的话,以为增删修改的文字就是留在身上的铠甲,给他们脱掉,似乎还不到时候。
结果是决定收。而且有同志陆续引用这批信作为资料在自己的文章中发表了。
比起《两地书》来,原信自然更丰富,更生动,特别是有更多的细致的心理活动的表现。但《两地书》却更准确,更精练。我想,假如把这两部分合成一本书,一定会很有意思的。
胆子大一点,放肆一点,把这两部分放在一起研究研究,怎么样呢?
鲁迅真是把现代中国人看透了。他说他写小说,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他感到“隔膜”,他觉得没有十分“把握”,“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结果他是成功了。惭愧也罢,愤怒也罢,同情也罢,厌弃也罢,读过《阿 Q 正传》之后,谁能从自己心里驱逐阿 Q 的影子?想自新的人,想中华民族振兴的人,清夜扪心,多少会栗栗危惧,深恐自己血管里仍然流着阿 Q 的血液吧?谁能忘了闰土?谁能忘了祥林嫂?谁能忘了夏瑜?谁能忘了那个人力车夫的背影?还有那帮太爷们……鲁迅写了那么多的杂文,有人恨,也有人爱;这是最牵动中国人的感情的。我们自己也许稍稍好一点,听说,国外的读者就不很注意鲁迅的杂文,翻译得也最少。其实,鲁迅自己不仅十分看重,并且特别表示自信:“‘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你想了解现代中国的民情和民心吗?你真的想移风易俗,改造中国吗?请读一读鲁迅的杂文吧!
我想:一个看透了大众的灵魂的人的灵魂,是怎样的呢?
没有比《两地书》及其原信更丰富更深刻更细致入微地表现了鲁迅的个性和心理特征的了。景宋为鲁迅织了一件毛线背心,鲁迅穿上感到格外温暖,他也说“或者也许还有别种原因”哩。有人会说:这像快五十岁的人吗?这就是赤子之心。鲁迅爱景宋,又深恐景宋为他牺牲,双方曾反复辩论。十年以后,鲁迅在“遗嘱”里对景宋说:“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这当中没有联系吗?鲁迅痛恨研究系比狐狸还坏,意欲痛击。可他说他自己太不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看不完,结果就只好乱打一通。这与所谓鲁迅是冷静,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的评论,有多么不同。鲁迅母亲将周作人的孩子的相片挂在墙上,将海婴的相片放在床头,逢人即献出,你道怎样,起初,鲁迅竟“颇不平”!待知道这是母亲的一种外交手段,他才释然,且对景宋说,他心里“便无芥蒂了”。鲁迅第二次回北平省母,几位老朋友待他甚好,他是那么深情地慨叹: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总之,鲁迅的杂文本来就是那么以平等的态度和读者谈心交心,辛辣而犀利的笔锋中凝聚着真情,而《两地书》及其原信,更是信笔写来,感情洋溢,一颗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我想,把书信中所涉及的思想和着他的品性以及心理特征,一并研究研究,也许别有兴味的吧?
景宋所写的书信,无疑是她一生中重要的文字,即使说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字之一,我想,也不为过吧?特别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删去的许多内容,对认识她,实在太重要了。仅仅为了了解她对鲁迅的深情的基础,她料理鲁迅的生活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为了这贡献而付出的牺牲,这一部分也是非读不可的。鲁迅说过,他俩的相爱,实有深因;并感叹有的人以他们自己的心去相窥探猜测,不会明白;并确信他俩之并不渺小。鲁迅又有诗曰:“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我想,许先生是欣慰的,能与鲁迅相遇,相识,相爱,并获得鲁迅这样推心置腹的相知,也就足矣了。世事这样纷繁,人生本多隔膜,在理想的社会到来之前,谁个能得到人人的了解与谅解?
我在这后半本书中努力写出我想到的话。我不敢说有多少可取的心得。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可读性。我只确切地知道,一定有不少失误。我的惭愧和不安就是由此产生的。特别是我早已过了可以以幼稚自谅的年岁,实在无可奈何。
我感谢培育、指导和帮助我的前辈和同志,还有几位朋友,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音容笑貌都铭刻在我心上。
王得后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夜
重印后记
人的第一大问题是生死,其次是温饱,再其次是男女关系。而人类又只能群居才得以生存,一切困境,由此滋生,由此蔓延。
人类既然群居,男女关系于是深深牵动人心。因为这是最自然的关系,最基本的关系。又因为这是当事人极想排他的私事,而他人却又偏偏极关注,极感兴趣,极想干涉。倘在社会发展变革的关头,就更加是这样。也因此,这是了解一个人和观察一个社会的基本窗口,是人类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尺。
《两地书》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品。渗透着一代人的血泪,饱含一种社会的意义。固然,这是鲁迅与朱安生逢其时的不幸,是鲁迅与景宋生不逢时的幸会,有鲜明的个人性色彩,鲁迅与景宋生前为此遭到笑骂、诬蔑和攻击。鲁迅死后,却又讳莫如深,并不正常。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渐渐开放,渐渐醒悟,渐渐开明。然而,人生就是这样,无聊之徒也即随时浮沉,说三道四,唾沫横起。
初版《序言》提到的“几位朋友”,其一是福田。一天,他和我谈了一个下午又一个大半夜的鲁迅研究,于是有这本小书的写作。他又亲任责编,于是有这本小书的出版。
第二年说要重印,我不以为然。又二年希望再版,我也有意加写《兄弟,兄弟》,《朋友,老的和少的》两章,想来想去,别有心绪,终于碌碌无为,不了了之。
十年过去了,朋友不弃,旧书重印。今年,罕为人知的《两地书》鲁迅手抄本,还有原信,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这比什么都好,实在不必再多说了。唯有想到能把旧作奉呈给几位新朋友,确也“不亦乐乎”。旧时“怕想象师长、朋友和熟人翻看这本书时的眼睛”的心情,已为风沙吹打得荡然无存。—人就这样老了。
王得后
一九九五年三月三日
王得后,谱名王德厚,江西永新人,一九三四年出生于汉口。退休前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著有《《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三)、《鲁迅心解》(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人海语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八)、《世纪末杂言》(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呐喊)导读》(中华书局,二〇〇二)、《垂死挣扎集》(中国文联出版社,二〇〇六)、《鲁迅教我》(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鲁迅与孔子》(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〇)、《今我来思:王得后杂文自选集》(金城出版社,二〇一五)、《我哪里去了》(花城出版社,二〇一五)、《刀客有道》(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等。
本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鲁迅与许广平通信的校读,作者细致标记了原信与鲁许二人修改稿增删改动的内容,并附有简短的评述。作者认为,原信内容丰富、生动,通信人细致的心理活动在其中有更多表现。后一部分是作者基于《两地书》生发出的八篇文章,剖析处于母子、夫妻、父子关系中的鲁迅的情感生活与灵魂样态,以及他对教育、政治和旧中国之改造的看法,想回答“一个看透了大众灵魂的人的灵魂,是怎样的”这个问题。
序(孙郁)
序 言
甲编 鲁迅和景宋的通信与《两地书》校读记
几句说明
第一集 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
第二集 厦门—广州(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
第三集 北平—上海(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
又集 未编入《两地书》的北平—上海的通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乙编 鲁迅与景宋的通信《两地书》读后记
几句说明
一、信笔写出的真相
“情书一捆”
“革命的爱在大众”
二、爱的影子:朱安女士
不可忽视的影响
你赞成回避吗?
鲁迅性格中的妥协面
历史性的婚姻悲剧
景宋的考虑与支持
三、“相依为命,离则两伤”
“我们之相处,实有深因”
爱情:油然而生,沛然而长
从“牺牲论”看鲁迅的婚姻观
四、在母亲和儿子之间
“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梦里依稀慈母泪”
因袭的重担
后顾之忧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遗 嘱
五、走人生的长途……
苦闷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密
专与苦痛捣乱或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
“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
六、“究竟教育是怎么一回事?”
“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
反“坚壁清野主义”和“寡妇主义”
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
七、心灵深处的政治意识
“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
“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
“这一回的战斗……”
“‘钻网’的法子”
八、对于改造旧中国的道路的探索
改变人的精神是救国的“第一要著”
“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在改造旧中国的过程中改造人
重印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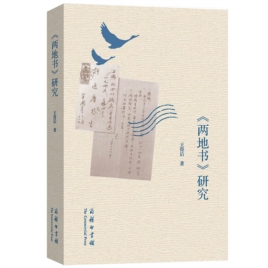
![]()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 版权所有 2004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