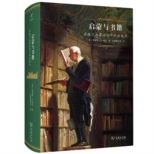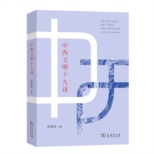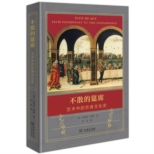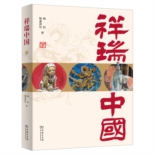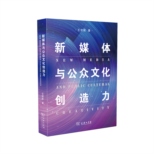显示全部前言
经历六载春秋,我的博士论文修改稿即将付印,原来想象中觉得应该写篇像样的后记,一旦提笔,竟然难以下手,思索再三,决定改繁琐为简洁,以“前言”代“后记”。
本书的出版,使我有一种完成使命的感觉。早年在工厂做工、在中学教书、在饭店打工的时候,我脑子里盛放着一个“远大志向”,就是能够考取大学,考取研究生,成为一名斯文学者。及至20余年过去,历经坎坷,终于由硕士而博士、而博士后,才发觉进入“学者”行列实非易事,一是这个社会伪学者太多,真学者太少;一是我觉得自己离一个真学者还有很大差距。以这两点警醒、鞭策自己,我仍然把“成为一名斯文学者”当成自己今后的理想。
这本书从萌芽到定稿,到出版,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我特别对以下单位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江苏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培养基金
在过去几年难忘的日子里,我从一个步入史学之门不久、根基浅薄的学生到稍稍领略史学“三昧”,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老师们的点拨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我的导师秦宝琦教授为我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在学术研究、道德风范上为我表率,在具体的学术观点探讨上也表现出宽宏的学术风度。
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徐艺圃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等反复辩难,历时四小时,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在通讯评阅人中,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程歗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教授与常建华教授等也都予以很多鼓励,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尤其是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历史系蔡少卿教授(我的硕士生导师与博士后联系导师)认为我的论文“把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评语虽然过誉,对我却是莫大的激励。
三年里,清史所96级9名博士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生活画面,我应该感谢他们——朱杰军、迟云飞、林乾、张永江、陈连营、张小也、董建中、赵晓华。
本书英文提要由著名汉学家、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教授撰写,其文笔形神俱备,特此致谢。
这些年,我的妻子朱明清承受了巨大压力,含辛茹苦,支撑家庭,支持我的学业,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包含了她的心血,这本书更是她与我共同劳动的成果。
我的书能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感到十分荣幸。还在十几年前读硕士的时候,我曾经收集资料,想为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的夏瑞芳写传;后来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100年来出版的经典书籍、资料为我提供了极大便利。
这几年冥思苦想、闭门造车,一旦成书,难免敝帚自珍,其中缺点一定很多。我知道,一本好书,必须经得起时间的磨洗。我期待着同行们的批评。
本书的出版,使我有一种完成使命的感觉。早年在工厂做工、在中学教书、在饭店打工的时候,我脑子里盛放着一个“远大志向”,就是能够考取大学,考取研究生,成为一名斯文学者。及至20余年过去,历经坎坷,终于由硕士而博士、而博士后,才发觉进入“学者”行列实非易事,一是这个社会伪学者太多,真学者太少;一是我觉得自己离一个真学者还有很大差距。以这两点警醒、鞭策自己,我仍然把“成为一名斯文学者”当成自己今后的理想。
这本书从萌芽到定稿,到出版,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我特别对以下单位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江苏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培养基金
在过去几年难忘的日子里,我从一个步入史学之门不久、根基浅薄的学生到稍稍领略史学“三昧”,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老师们的点拨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我的导师秦宝琦教授为我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在学术研究、道德风范上为我表率,在具体的学术观点探讨上也表现出宽宏的学术风度。
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徐艺圃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等反复辩难,历时四小时,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在通讯评阅人中,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程歗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教授与常建华教授等也都予以很多鼓励,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尤其是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历史系蔡少卿教授(我的硕士生导师与博士后联系导师)认为我的论文“把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评语虽然过誉,对我却是莫大的激励。
三年里,清史所96级9名博士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生活画面,我应该感谢他们——朱杰军、迟云飞、林乾、张永江、陈连营、张小也、董建中、赵晓华。
本书英文提要由著名汉学家、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教授撰写,其文笔形神俱备,特此致谢。
这些年,我的妻子朱明清承受了巨大压力,含辛茹苦,支撑家庭,支持我的学业,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包含了她的心血,这本书更是她与我共同劳动的成果。
我的书能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感到十分荣幸。还在十几年前读硕士的时候,我曾经收集资料,想为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的夏瑞芳写传;后来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100年来出版的经典书籍、资料为我提供了极大便利。
这几年冥思苦想、闭门造车,一旦成书,难免敝帚自珍,其中缺点一定很多。我知道,一本好书,必须经得起时间的磨洗。我期待着同行们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