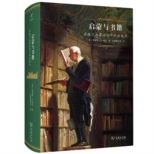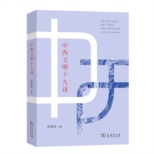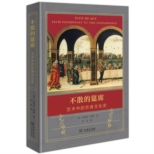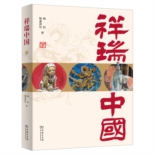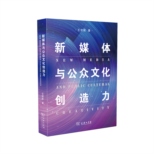显示全部序言
本书作者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 l870.9.18—1947.8.25)是著名美国人类学家,曾任纽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近四十年并任教于耶鲁大学(1924—1940年)。他原先攻读心理学,并获博士学位。因受F.博厄斯(1858—1942年,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影响而对人类学发生兴趣。早期他在体质人类学著作中论述了人体测量问题。他的《北美平原的印第安人》一书反映了他实地考察的重点所在。他后来成为达科他部落和黑脚部落问题的权威,写有两百多篇学术论文和普及文章。威斯勒的人类学著作着重描述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伦理标准、神话传说和艺术图案。其主要著作有《北美平原的印第安人》(1912年)、《美洲印第安人》(1917年初版,1922年再版)、《印第安马队》(1938年)和《美国印第安人》(1940年)等。其中《美洲印第安人》一书至今仍是北美人种学的经典著作。
《人与文化》初版于1923年,先后四次再版。本书是根据他1921—1922年在美国几所州立大学和一些学会专题讲演汇编而成的。全书分三部分共十七章,层层递进,所言中心如题所示,乃是人与文化的关系。作者的一个主要命题是:文化是由人类的反思性思维发展出来的积累性结构。实施这种思维的机制是每个人的内在素质的一部分;文化因素的积累主要是这类反思性行为在语言和客观性物质操作中的表达。作者在对古今文化做了比较之后,论述了文化的含义及其形式和内容。按照作者的观点,从狩猎采集到宗教战争,人类的一切社会性活动都属于文化范畴。
只是由于种族之间以及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化类型与进化程度上的差异,从而驱使着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劳心费神。为了寻求相对客观的视点,作者不仅描述了他所熟悉的印第安文化,而且还领着读者试图以印第安人的眼光反观作者本人所隶属的文化(即他所说的欧美文化)。通过这种显然是比较学的叙述,作者把造成文化差异的外部原因也就是环境因素展示出来。该因素分为自然环境与种族环境。人不能没有自然环境与种族环境,人的降生与成长也不能选择自然环境与种族环境。作者没有在这里深究何者为终极原因,他不过是为文化的地理分布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
本书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文化区域(Culture Area)的概念。作者用自己手头上的材料显示,作为一般的、理想的情况,文化区域应呈同心、圆形分布。而地理障碍、动植物分布等因素对文化区域的形成产生扭曲作用。作者列举了北美史前石器装饰的分布为例。在其中心地带能发现各个时期的遗迹,而在向外扩散的各个区域里分布类型呈递减态势,其遗迹年代的上限逐渐远离我们的今天。作者用这类例子表明“文化中心传播”的历史事实。
本书提到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文化一般模式”。作者从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到风俗仪式特质综合体,归纳出了他所说的“文化一般模式”,认为这是古今一切文化之共性所在。每种文化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按照模式可以从每种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表现。此外,作者就整个世界的环境提出了与人类聚集区及文化相联系的三大地理范围,即丛林、台地、苔原。从他所展示的地图来看,丛林地带包括热带非洲、南亚、东南亚大部、澳洲、加勒比、亚马逊;台地地带包括南欧、地中海南岸、小亚细亚、中国、西伯利亚南部,直至白令海峡,然后纵贯南北美洲的中西部(其中尤卡坦和秘鲁最为著名)。它从北至南越过巴拿马地峡,沿安第斯山直抵南方巴塔哥尼亚大草原;苔原地带包括欧亚的北部、加拿大、美国北部、巴塔哥尼亚的南部。与这三大区域相对应的人种是黑种人、红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其中前两种人从地域上讲非常接近。那么,文化类型就此分成丛林文化、台地文化、苔原文化。作者的这种划分与当今流行的东西方文化相比较,后者似乎更侧重于政治与经济、伦理与风俗,前者似乎更侧重于地理学和人类学。
三种文化的划分只是最大范畴的分类。实际上部落之间、地区之间、类型之间相互扩散、相互渗透,因为每种文化都要求传播自己的特质综合体(trait complex)。比如说马的存在就是一种特质。围绕着马的使用发展出相应的风俗习惯、机械装置、文学艺术、宗教禁忌、社会差别。对于所有这些,可称之为马文化。总之,由于所有依赖于马的功用以及必须依靠马来完成的活动都彼此交织,显示为一种综合体。特质综合体的传播可分为自然的传播和有意识的传播。自近代以来,它是通过探险家、传教士、私酒贩、商人、军队这些人物来完成自己的使命的。“文化传播”常常与武力征服互为补充。不过,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格外冷静。他认为“征服是一种从文化中心的正常的向外投射”。作者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他从民族杀戮、宗教战争、种族灭绝当中看到的是文化。如果是文明征服野蛮,无异于扩散了先进的文化;如果是野蛮征服文明,胜利者被同化,出现中心的转移或合并。总之,无论历史怎样运作,文化向全球的传播似乎是左右逢源。从字里行间看得出作者对此感到欣慰。
应该看到,作者治学的出发点如他自己所说,是“建立在文化与它的生物学背景上的”(作者前言)。这就意味着对于人类文化现象的研究如同对植物、动物现象的研究一样,不存在价值的评估。作者好像只意识到,每当他在考虑文化现象的生物学意义时,就看出地域、人种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比如说关于人种问题。作者认为由环境造成的人种无论是民族之间还是个人之间,在心理素质上是存在差异的。他把天才个人以及天才所在的群体当作一个源泉。“在文化中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就是那些曾想出优越的处理方法的人”(第十三章)。因此效率使时间相形见绌。后来者居上被视为常规。作者举例,印第安人弓箭手与美国现代人射手比赛,后者胜前者。这决不是由于历史短的美国人获得了更多的遗传因素所致,而是在处理情况的方法上要比前者优越。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在本书中,作者还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文化传播、武力扩张、文化趋同等现象的看法。其中尤对文化是独立起源还是通过一个中心传播而成的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威斯勒和他的老师F.博厄斯同被视为文化人类学当中持广义传播论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文化传播”这一论题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屡被提及,也曾经展开过近乎失去理智的激烈争论。该流派名重一时,以至当时的反对者不得不强调:传播主义绝非是必须都要遵守的教条,而应只是一种可以解释文化现象的方法。另外,在对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趋同现象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分歧也是重大的。进化论者认为这是人类同种共性的表现,由此把世界文化视为单线进化的过程。每个民族都将是按照一条路线走完各个历史文化阶段的;而文化传播论者把趋同现象说成恰恰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他们认为正是因为由同一个发源中心向外扩散才能形成不同地区的文化趋同现象。上述两种观点所存在的理论失误在今天看来是比较明显的。读者可以从本书有关问题的系统论述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国近年编译出版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例如日本等国学者的有关论述)在提到克拉克•威斯勒时,多只限于把他和他的理论思想与其他十几种流派放在一起做概论式的介绍。因此不易窥其全貌。而《人与文化》一书与威斯勒的经典名著《美洲印第安人》一样,其中的许多数据和概念仍被广泛引用着。因此今天出版它的中译本依然是很有意义的。
在全书的末尾,作者指出,我们与原始群体之间的区别在于群体生活的合理化程度。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包含有对科学性与现实性的要求,包含着对今天的行为将产生何种结果的预见。一个民族对自身的文化要有清醒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常常是以比较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这个民族要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有清醒的认识。这里且不论开放性与兼容性会给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能带来的优势,而是说人与文化的上述关系在经历了血与火的劫难之后,理性的内容也就愈见增多。由于几乎每个民族都把自己的文化视为自己生命的同义语,都会热衷于传播扩散自己的文化。对世界负有责任的民族在其文化扩散过程中必须对可能的结果有清醒的合乎逻辑的认识,也就是应当考虑到不要铸成如下大错:迫使其他民族除了战斗之外别无选择(第十六章)。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只要有一个以上的民族,一个以上的文化存在,它就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至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的今天,有助于我们的未来。或许这也是我们今天把本书献给读者的意义所在吧。
《人与文化》全书共分十七章。钱岗南译序言,第一至第十章,第十五章,第十七章及索引部分;傅志强译第十一至十四章,第十六章,并审校了全书;田小文负责整理了部分文稿和图稿;钱岗南撰写了译者序,傅志强撰写了译后记。
关于书中一些名词术语的译法颇费斟酌。像diffusion,adhesion,trait等词都按国内已有的译法分别译为“扩散”、“粘合”、“特质”等等。“文化综合体”这个概念最早出自于威斯勒的著作。而人类学当中的complex一词,国内译法不一。有的译为“丛”或“丛体”,本书译为“综合体”。
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予以指正。
译 者
1991年10月
《人与文化》初版于1923年,先后四次再版。本书是根据他1921—1922年在美国几所州立大学和一些学会专题讲演汇编而成的。全书分三部分共十七章,层层递进,所言中心如题所示,乃是人与文化的关系。作者的一个主要命题是:文化是由人类的反思性思维发展出来的积累性结构。实施这种思维的机制是每个人的内在素质的一部分;文化因素的积累主要是这类反思性行为在语言和客观性物质操作中的表达。作者在对古今文化做了比较之后,论述了文化的含义及其形式和内容。按照作者的观点,从狩猎采集到宗教战争,人类的一切社会性活动都属于文化范畴。
只是由于种族之间以及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化类型与进化程度上的差异,从而驱使着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劳心费神。为了寻求相对客观的视点,作者不仅描述了他所熟悉的印第安文化,而且还领着读者试图以印第安人的眼光反观作者本人所隶属的文化(即他所说的欧美文化)。通过这种显然是比较学的叙述,作者把造成文化差异的外部原因也就是环境因素展示出来。该因素分为自然环境与种族环境。人不能没有自然环境与种族环境,人的降生与成长也不能选择自然环境与种族环境。作者没有在这里深究何者为终极原因,他不过是为文化的地理分布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
本书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文化区域(Culture Area)的概念。作者用自己手头上的材料显示,作为一般的、理想的情况,文化区域应呈同心、圆形分布。而地理障碍、动植物分布等因素对文化区域的形成产生扭曲作用。作者列举了北美史前石器装饰的分布为例。在其中心地带能发现各个时期的遗迹,而在向外扩散的各个区域里分布类型呈递减态势,其遗迹年代的上限逐渐远离我们的今天。作者用这类例子表明“文化中心传播”的历史事实。
本书提到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文化一般模式”。作者从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到风俗仪式特质综合体,归纳出了他所说的“文化一般模式”,认为这是古今一切文化之共性所在。每种文化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按照模式可以从每种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表现。此外,作者就整个世界的环境提出了与人类聚集区及文化相联系的三大地理范围,即丛林、台地、苔原。从他所展示的地图来看,丛林地带包括热带非洲、南亚、东南亚大部、澳洲、加勒比、亚马逊;台地地带包括南欧、地中海南岸、小亚细亚、中国、西伯利亚南部,直至白令海峡,然后纵贯南北美洲的中西部(其中尤卡坦和秘鲁最为著名)。它从北至南越过巴拿马地峡,沿安第斯山直抵南方巴塔哥尼亚大草原;苔原地带包括欧亚的北部、加拿大、美国北部、巴塔哥尼亚的南部。与这三大区域相对应的人种是黑种人、红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其中前两种人从地域上讲非常接近。那么,文化类型就此分成丛林文化、台地文化、苔原文化。作者的这种划分与当今流行的东西方文化相比较,后者似乎更侧重于政治与经济、伦理与风俗,前者似乎更侧重于地理学和人类学。
三种文化的划分只是最大范畴的分类。实际上部落之间、地区之间、类型之间相互扩散、相互渗透,因为每种文化都要求传播自己的特质综合体(trait complex)。比如说马的存在就是一种特质。围绕着马的使用发展出相应的风俗习惯、机械装置、文学艺术、宗教禁忌、社会差别。对于所有这些,可称之为马文化。总之,由于所有依赖于马的功用以及必须依靠马来完成的活动都彼此交织,显示为一种综合体。特质综合体的传播可分为自然的传播和有意识的传播。自近代以来,它是通过探险家、传教士、私酒贩、商人、军队这些人物来完成自己的使命的。“文化传播”常常与武力征服互为补充。不过,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格外冷静。他认为“征服是一种从文化中心的正常的向外投射”。作者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他从民族杀戮、宗教战争、种族灭绝当中看到的是文化。如果是文明征服野蛮,无异于扩散了先进的文化;如果是野蛮征服文明,胜利者被同化,出现中心的转移或合并。总之,无论历史怎样运作,文化向全球的传播似乎是左右逢源。从字里行间看得出作者对此感到欣慰。
应该看到,作者治学的出发点如他自己所说,是“建立在文化与它的生物学背景上的”(作者前言)。这就意味着对于人类文化现象的研究如同对植物、动物现象的研究一样,不存在价值的评估。作者好像只意识到,每当他在考虑文化现象的生物学意义时,就看出地域、人种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比如说关于人种问题。作者认为由环境造成的人种无论是民族之间还是个人之间,在心理素质上是存在差异的。他把天才个人以及天才所在的群体当作一个源泉。“在文化中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就是那些曾想出优越的处理方法的人”(第十三章)。因此效率使时间相形见绌。后来者居上被视为常规。作者举例,印第安人弓箭手与美国现代人射手比赛,后者胜前者。这决不是由于历史短的美国人获得了更多的遗传因素所致,而是在处理情况的方法上要比前者优越。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在本书中,作者还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文化传播、武力扩张、文化趋同等现象的看法。其中尤对文化是独立起源还是通过一个中心传播而成的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威斯勒和他的老师F.博厄斯同被视为文化人类学当中持广义传播论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文化传播”这一论题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屡被提及,也曾经展开过近乎失去理智的激烈争论。该流派名重一时,以至当时的反对者不得不强调:传播主义绝非是必须都要遵守的教条,而应只是一种可以解释文化现象的方法。另外,在对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趋同现象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分歧也是重大的。进化论者认为这是人类同种共性的表现,由此把世界文化视为单线进化的过程。每个民族都将是按照一条路线走完各个历史文化阶段的;而文化传播论者把趋同现象说成恰恰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他们认为正是因为由同一个发源中心向外扩散才能形成不同地区的文化趋同现象。上述两种观点所存在的理论失误在今天看来是比较明显的。读者可以从本书有关问题的系统论述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国近年编译出版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例如日本等国学者的有关论述)在提到克拉克•威斯勒时,多只限于把他和他的理论思想与其他十几种流派放在一起做概论式的介绍。因此不易窥其全貌。而《人与文化》一书与威斯勒的经典名著《美洲印第安人》一样,其中的许多数据和概念仍被广泛引用着。因此今天出版它的中译本依然是很有意义的。
在全书的末尾,作者指出,我们与原始群体之间的区别在于群体生活的合理化程度。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包含有对科学性与现实性的要求,包含着对今天的行为将产生何种结果的预见。一个民族对自身的文化要有清醒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常常是以比较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这个民族要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有清醒的认识。这里且不论开放性与兼容性会给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能带来的优势,而是说人与文化的上述关系在经历了血与火的劫难之后,理性的内容也就愈见增多。由于几乎每个民族都把自己的文化视为自己生命的同义语,都会热衷于传播扩散自己的文化。对世界负有责任的民族在其文化扩散过程中必须对可能的结果有清醒的合乎逻辑的认识,也就是应当考虑到不要铸成如下大错:迫使其他民族除了战斗之外别无选择(第十六章)。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只要有一个以上的民族,一个以上的文化存在,它就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至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的今天,有助于我们的未来。或许这也是我们今天把本书献给读者的意义所在吧。
《人与文化》全书共分十七章。钱岗南译序言,第一至第十章,第十五章,第十七章及索引部分;傅志强译第十一至十四章,第十六章,并审校了全书;田小文负责整理了部分文稿和图稿;钱岗南撰写了译者序,傅志强撰写了译后记。
关于书中一些名词术语的译法颇费斟酌。像diffusion,adhesion,trait等词都按国内已有的译法分别译为“扩散”、“粘合”、“特质”等等。“文化综合体”这个概念最早出自于威斯勒的著作。而人类学当中的complex一词,国内译法不一。有的译为“丛”或“丛体”,本书译为“综合体”。
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予以指正。
译 者
199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