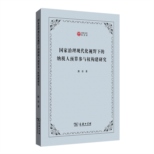显示全部后记
多年来,我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
芸芸众生皆性恶,人不是尽善尽美的天使。因此之故,当他们组成社会、组成国家的时候,就必须对社会和国家进行“管理”。这种管理职责的主要承担者,近现代叫做公务员(或文官),在中国古代则主要叫做“职官”。要管理社会和国家,就首先必须对管理者加以“管理”。后一种管理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事实上它是决定社会管理成败的关键。“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康熙语)。“国家大体所关,惟贤不肖之辨”(《清史稿•选举七》语)。“不论政府组织如何健全、财力如何充足、工作方法如何精当,但如果不能获得优秀人才到政府中供职,仍不能对公务作有效的实际推行”(梅耶士语)。这些言论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能不信。古今中外社会虽然各有差异,但也有“一以贯之”之“道”。可以说,如何有效地对管理者加以管理,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大学问。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成就举世公认,而清朝文官制度是其最后形态。人们常说,中国古代发展到清朝,专制制度已经极为腐朽没落。但是,清朝却存在了260多年,而且又是少数民族主政。这种现象绝非偶然,个中原因必然与当时的文官管理密切相关。清朝文官制度究竟有何成功之处?同时,它毕竟生长在专制体制之下,因而必然有致命的缺陷。清朝文官制度究竟有何失败之处?正是这种探知欲,使我将目光投向了清朝文官制度。
涉及史论的著述,求真、求实、求信是第一要义。为此,我花了大量时间收集第一手原始材料。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仅《大清会典》和《会典事例》,摞在桌上就有几尺高,上面积满了尘埃,刚开始时真有点望而生畏,但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埋进书堆里。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书中的材料基本上是翔实和可信的。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由于我主观上希望尽可能在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做出独立的分析和阐述,所以虽然阅读了一些有关研究著作,但坦率地说并不很多,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已有学术成果的借鉴。
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我在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做客座研究员。书稿是从2001年7月开始动笔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几乎天天伏案近10个小时。那年七、八月份恰遇日本近几十年中最炎热的夏天,40度左右的高温天气持续了近一个月。另外,在我卧室的前面有块学校的网球场,几乎天天都有学生在那里训练,他们训练有个特点,就是连续不断地狂叫。那叫声,用声嘶力竭来形容恐怕也不算过分;听到那叫声,我总觉得好像是世界末日到了。这种叫声常常将我苦苦整理好的思绪打断。由于长期伏案书写,加之恶劣的气候和环境,两个月下来,我的肠胃出现了怪异的感觉。起初我以为得了大病,好在检查下来根本无病。但从此以后,只要伏案时间稍长,那怪异的感觉就会出现。这种经历,再一次让我尝到了“爬格子”的艰辛。
在研究清朝文官制度的过程中,我愈益觉得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由于才疏学浅,加之许多制度非常具体、细致,仅从文献分析很难弄得明白,至今仍有许多问题未能真正理清。所以,虽然书稿写完了,但心中总有惴惴不安之感。我期待着学界同仁的批评和匡正。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要感谢苏州大学杨海坤教授,他为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朱绛副编审,他认真审阅了书稿并且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为本书顺利出版给予了真诚的帮助,他的严谨、求实和敬业精神令我至为钦佩,从他身上,我感悟到了商务印书馆的优良传统和高尚风格。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图书馆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和热忱服务,在此也一并致谢。当我在日本独自专心写作时,我的妻子承担起了育子重任和繁重的家务,本书自然也凝聚着她的心血。
作 者
2003年4月于苏州北沿河
芸芸众生皆性恶,人不是尽善尽美的天使。因此之故,当他们组成社会、组成国家的时候,就必须对社会和国家进行“管理”。这种管理职责的主要承担者,近现代叫做公务员(或文官),在中国古代则主要叫做“职官”。要管理社会和国家,就首先必须对管理者加以“管理”。后一种管理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事实上它是决定社会管理成败的关键。“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康熙语)。“国家大体所关,惟贤不肖之辨”(《清史稿•选举七》语)。“不论政府组织如何健全、财力如何充足、工作方法如何精当,但如果不能获得优秀人才到政府中供职,仍不能对公务作有效的实际推行”(梅耶士语)。这些言论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能不信。古今中外社会虽然各有差异,但也有“一以贯之”之“道”。可以说,如何有效地对管理者加以管理,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大学问。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成就举世公认,而清朝文官制度是其最后形态。人们常说,中国古代发展到清朝,专制制度已经极为腐朽没落。但是,清朝却存在了260多年,而且又是少数民族主政。这种现象绝非偶然,个中原因必然与当时的文官管理密切相关。清朝文官制度究竟有何成功之处?同时,它毕竟生长在专制体制之下,因而必然有致命的缺陷。清朝文官制度究竟有何失败之处?正是这种探知欲,使我将目光投向了清朝文官制度。
涉及史论的著述,求真、求实、求信是第一要义。为此,我花了大量时间收集第一手原始材料。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仅《大清会典》和《会典事例》,摞在桌上就有几尺高,上面积满了尘埃,刚开始时真有点望而生畏,但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埋进书堆里。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书中的材料基本上是翔实和可信的。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由于我主观上希望尽可能在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做出独立的分析和阐述,所以虽然阅读了一些有关研究著作,但坦率地说并不很多,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已有学术成果的借鉴。
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我在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做客座研究员。书稿是从2001年7月开始动笔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几乎天天伏案近10个小时。那年七、八月份恰遇日本近几十年中最炎热的夏天,40度左右的高温天气持续了近一个月。另外,在我卧室的前面有块学校的网球场,几乎天天都有学生在那里训练,他们训练有个特点,就是连续不断地狂叫。那叫声,用声嘶力竭来形容恐怕也不算过分;听到那叫声,我总觉得好像是世界末日到了。这种叫声常常将我苦苦整理好的思绪打断。由于长期伏案书写,加之恶劣的气候和环境,两个月下来,我的肠胃出现了怪异的感觉。起初我以为得了大病,好在检查下来根本无病。但从此以后,只要伏案时间稍长,那怪异的感觉就会出现。这种经历,再一次让我尝到了“爬格子”的艰辛。
在研究清朝文官制度的过程中,我愈益觉得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由于才疏学浅,加之许多制度非常具体、细致,仅从文献分析很难弄得明白,至今仍有许多问题未能真正理清。所以,虽然书稿写完了,但心中总有惴惴不安之感。我期待着学界同仁的批评和匡正。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要感谢苏州大学杨海坤教授,他为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朱绛副编审,他认真审阅了书稿并且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为本书顺利出版给予了真诚的帮助,他的严谨、求实和敬业精神令我至为钦佩,从他身上,我感悟到了商务印书馆的优良传统和高尚风格。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图书馆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和热忱服务,在此也一并致谢。当我在日本独自专心写作时,我的妻子承担起了育子重任和繁重的家务,本书自然也凝聚着她的心血。
作 者
2003年4月于苏州北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