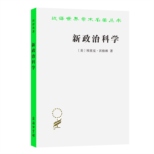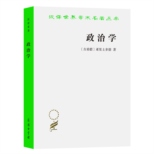显示全部出版说明
<STRONG><FONT size=3> 《社会政策译丛》出版说明
</FONT></STRONG>
经过不懈的努力,《社会政策译丛》终于面世了。作为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学者,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协助广大同行学者、学生、政策实践者以及对社会政策有兴趣的朋友,在浩如烟海的学术著作中,找到一些可供学习或借鉴的线索。
<STRONG>1</STRONG>
“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的概念一般有三个涵义:(1)政府用于福利和社会保护的政策,特别是有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的政策;(2)福利在一个社会中发展的方式。其涵义比(1)更为广泛,大大超出了政府行为的范畴,包括福利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在内的诸多社会及经济条件;(3)针对上述主题的学术研究。
作为政府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如何为其公民提供必要福利和保障的问题,并不可避免地遇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约束,但是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社会政策并没有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发展。当然,这一现象的存在与“社会政策”概念形成的历史和发展有关。
学术界对社会政策的密切关注,始于战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建构。由于各国在意识形态、历史、经济,以及社会条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对福利国家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于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因而,早期针对福利国家的研究带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并多半针对具体的政策。例如,在最先开始系统性研究社会政策的英国,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工作与行政管理。主要针对专门从事福利提供、管理和政策执行的人员。实践的发展对理论建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同时,随着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在很多欧洲国家受到挑战,以福利国家的社会工作和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社会政策研究首先遇到理论方面的挑战。传统社会福利体系为什么会面临危机?到底什么样的福利体系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福利体系背后的意识形态标准是什么,又如何影响福利体系的构成?这些问题都不断困扰着社会政策研究人员。
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政策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外延在扩大。其中涉及了社会服务领域的政策及管理实践(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就业、社区照顾和住房等),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犯罪、身残智残、失业、老龄问题等),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包括种族、性别、贫困等)以及对相关问题的集体性社会反映。二是理论向纵深拓展。突破了国家―市场的简单对立,进一步探讨国家―市场的结合(如准市场、公私合营、合作等),加强了对各种非国家因素在社会保障和救助过程中的角色(如志愿及互助机构的福利提供、亲朋及邻里等非正式的救助形式)的研究,从以补偿收入为目标的福利提供向非收入补偿转化(如对社会排斥问题的关注),等等。
迄今为止,社会政策已经发展成一个跨学科的应用研究领域。它广泛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史学、哲学以及法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社会对社会需求的反应。它主要关注经济、社会及政治领域中与人类所必需的生存条件及其提供方法有关的问题,所涉及的人类基本需求(或福利)包括:食物及居住、可持续性及安全的环境(包括就业、犯罪、环境等)、增进健康及医治病患、对无独立生存能力者提供照顾和支持(包括社区服务)、对个人提供教育和培训,使其有能力融入社会。
<STRONG>2
</STRONG> 伴随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新型社会关系的产生和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政策理论研究正面临新的挑战和机会。
首先,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策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转型国家和若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使它们需要且可能对社会政策给予充分的关注,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度的扩大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如何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进行协调,进而实现国际合作,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方面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如,移民管理、反贫困、最低工资待遇、最低劳动保护标准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完善的社会保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在国际发展中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其次,对国际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尽管较早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对不同国家社会政策的比较,但比较研究的意义历来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和社会特点均有不同,把两个或多个国家的政策进行横向比较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但随着国际或地区间经济一体化的加强,社会政策的相互隔绝似乎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合作的障碍。特别是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跨国流动已经不可避免地把社会政策纳入一国国际竞争力的组成中来。在社会政策领域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是艾斯平—安德森(G Esping Andersen)。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把福利国家划分为三种主要模式:以工作和个人贡献为主导的法团模式(corporatist regimes),遵循普遍原则的社会民主模式(social democratic regimes),遵循补余原则(residualism)的自由主义模式(1iberal regimes),为国际社会政策的比较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使其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并引导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除此以外,在艾斯平—安德森前后还有一些对具体政策的比较,对政策投入产出的比较,对政策执行和政策效果的比较等。
<STRONG>3
</STRONG>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许多经济及社会问题已经难以为经济快速增长这个单一的指标所涵盖,摸索中的改革实践显然已经大大超前于理论的发展。当前,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改革的推进要求跨学科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要求针对我国的特点,对改革提供具有预见性和实践意义的指导,从而达到建设小康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目的。
如前所述,当今社会政策研究的动态体现了社会政策自身的跨学科、开放和适应性的理论灵魂。作为本丛书的编者,我们力图在选题过程中体现当前国际社会科学(不仅限于社会政策)发展的这些特征,向人们展示各国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如何面对社会政策研究的需要,跨越学科壁垒,追求实现社会保护的共同目标。
值得指出,社会政策与一国的文化、历史、经济、社会背景紧密相联。各国社会政策方面的学术文献不计其数,由于人力及财力所限,本丛书只可能使读者对这一庞大领域窥见一斑。参与编译工作的各位同仁,以及积极支持本丛书出版的海内外学者的一个最大愿望是,本丛书能够激发读者的兴趣,并鼓励他们沿着书中所能提供的线索攀登社会政策研究的重重山岭。同时,我们以及丛书的若干作者都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够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评论和批评指正,在探讨的过程中共同进步。
借此机会,我们特别感谢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会政策系的Alan Walker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系的Howard Glennerster教授、Julian Le Grand教授、德国Bielefeld大学社会学系的Lutz Leisering教授、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熊性美教授。他们在本丛书的选题和出版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无私的帮助。商务印书馆的张胜纪先生,在丛书的筹划阶段抱病坚持工作,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最后,编者对商务印书馆在关注并推动社会政策研究方面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表示崇高的敬意。
李秉勤 贡 森
2002年4月5日
</FONT></STRONG>
经过不懈的努力,《社会政策译丛》终于面世了。作为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学者,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协助广大同行学者、学生、政策实践者以及对社会政策有兴趣的朋友,在浩如烟海的学术著作中,找到一些可供学习或借鉴的线索。
<STRONG>1</STRONG>
“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的概念一般有三个涵义:(1)政府用于福利和社会保护的政策,特别是有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的政策;(2)福利在一个社会中发展的方式。其涵义比(1)更为广泛,大大超出了政府行为的范畴,包括福利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在内的诸多社会及经济条件;(3)针对上述主题的学术研究。
作为政府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如何为其公民提供必要福利和保障的问题,并不可避免地遇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约束,但是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社会政策并没有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发展。当然,这一现象的存在与“社会政策”概念形成的历史和发展有关。
学术界对社会政策的密切关注,始于战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建构。由于各国在意识形态、历史、经济,以及社会条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对福利国家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于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因而,早期针对福利国家的研究带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并多半针对具体的政策。例如,在最先开始系统性研究社会政策的英国,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工作与行政管理。主要针对专门从事福利提供、管理和政策执行的人员。实践的发展对理论建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同时,随着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在很多欧洲国家受到挑战,以福利国家的社会工作和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社会政策研究首先遇到理论方面的挑战。传统社会福利体系为什么会面临危机?到底什么样的福利体系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福利体系背后的意识形态标准是什么,又如何影响福利体系的构成?这些问题都不断困扰着社会政策研究人员。
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政策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外延在扩大。其中涉及了社会服务领域的政策及管理实践(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就业、社区照顾和住房等),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犯罪、身残智残、失业、老龄问题等),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包括种族、性别、贫困等)以及对相关问题的集体性社会反映。二是理论向纵深拓展。突破了国家―市场的简单对立,进一步探讨国家―市场的结合(如准市场、公私合营、合作等),加强了对各种非国家因素在社会保障和救助过程中的角色(如志愿及互助机构的福利提供、亲朋及邻里等非正式的救助形式)的研究,从以补偿收入为目标的福利提供向非收入补偿转化(如对社会排斥问题的关注),等等。
迄今为止,社会政策已经发展成一个跨学科的应用研究领域。它广泛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史学、哲学以及法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社会对社会需求的反应。它主要关注经济、社会及政治领域中与人类所必需的生存条件及其提供方法有关的问题,所涉及的人类基本需求(或福利)包括:食物及居住、可持续性及安全的环境(包括就业、犯罪、环境等)、增进健康及医治病患、对无独立生存能力者提供照顾和支持(包括社区服务)、对个人提供教育和培训,使其有能力融入社会。
<STRONG>2
</STRONG> 伴随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新型社会关系的产生和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政策理论研究正面临新的挑战和机会。
首先,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策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转型国家和若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使它们需要且可能对社会政策给予充分的关注,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度的扩大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如何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进行协调,进而实现国际合作,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方面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如,移民管理、反贫困、最低工资待遇、最低劳动保护标准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完善的社会保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在国际发展中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其次,对国际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尽管较早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对不同国家社会政策的比较,但比较研究的意义历来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和社会特点均有不同,把两个或多个国家的政策进行横向比较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但随着国际或地区间经济一体化的加强,社会政策的相互隔绝似乎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合作的障碍。特别是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跨国流动已经不可避免地把社会政策纳入一国国际竞争力的组成中来。在社会政策领域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是艾斯平—安德森(G Esping Andersen)。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把福利国家划分为三种主要模式:以工作和个人贡献为主导的法团模式(corporatist regimes),遵循普遍原则的社会民主模式(social democratic regimes),遵循补余原则(residualism)的自由主义模式(1iberal regimes),为国际社会政策的比较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使其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并引导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除此以外,在艾斯平—安德森前后还有一些对具体政策的比较,对政策投入产出的比较,对政策执行和政策效果的比较等。
<STRONG>3
</STRONG>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许多经济及社会问题已经难以为经济快速增长这个单一的指标所涵盖,摸索中的改革实践显然已经大大超前于理论的发展。当前,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改革的推进要求跨学科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要求针对我国的特点,对改革提供具有预见性和实践意义的指导,从而达到建设小康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目的。
如前所述,当今社会政策研究的动态体现了社会政策自身的跨学科、开放和适应性的理论灵魂。作为本丛书的编者,我们力图在选题过程中体现当前国际社会科学(不仅限于社会政策)发展的这些特征,向人们展示各国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如何面对社会政策研究的需要,跨越学科壁垒,追求实现社会保护的共同目标。
值得指出,社会政策与一国的文化、历史、经济、社会背景紧密相联。各国社会政策方面的学术文献不计其数,由于人力及财力所限,本丛书只可能使读者对这一庞大领域窥见一斑。参与编译工作的各位同仁,以及积极支持本丛书出版的海内外学者的一个最大愿望是,本丛书能够激发读者的兴趣,并鼓励他们沿着书中所能提供的线索攀登社会政策研究的重重山岭。同时,我们以及丛书的若干作者都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够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评论和批评指正,在探讨的过程中共同进步。
借此机会,我们特别感谢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会政策系的Alan Walker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系的Howard Glennerster教授、Julian Le Grand教授、德国Bielefeld大学社会学系的Lutz Leisering教授、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熊性美教授。他们在本丛书的选题和出版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无私的帮助。商务印书馆的张胜纪先生,在丛书的筹划阶段抱病坚持工作,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最后,编者对商务印书馆在关注并推动社会政策研究方面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表示崇高的敬意。
李秉勤 贡 森
2002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