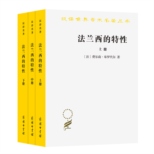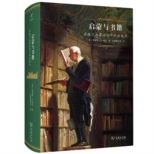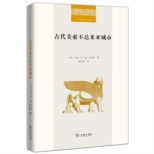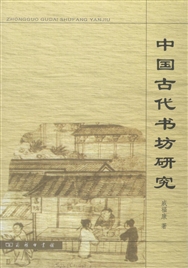显示全部后记
本书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出版的。1999年,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出于对古文献学研究的浓厚兴趣,报考了苏州大学文学院潘树广教授的博士生。
我在硕士期间攻读的是史学,因此,在著本书的时候,常常感到对古文献学的学习和研究进展缓慢而又有所力不从心。所幸的是,恩师潘树广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导我、点拨我,使我的学习和研究有了较快的进步。在恩师的指点下,我阅读了较多的有关出版、印刷史的专著和资料,使我逐渐认识到我国学界对书坊研究的薄弱性。因此,古代书坊研究,就成了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内容。不幸的是,恩师潘树广先生于2003年6月已仙逝,使我失去了一位慈父般的恩师。每想起恩师的教诲,我不敢有半点懈怠,为此,将论文重新修改并出版,以告慰于恩师。
本书对书坊的研究仅为初涉其源,梳理其流,论述其中,略存己见,故尚多有不足之处,以待方家、同仁乃至读者的批评,使书坊研究得以推进。
戚福康记于苏州葑谊陋室
2005年10月1日
我在硕士期间攻读的是史学,因此,在著本书的时候,常常感到对古文献学的学习和研究进展缓慢而又有所力不从心。所幸的是,恩师潘树广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导我、点拨我,使我的学习和研究有了较快的进步。在恩师的指点下,我阅读了较多的有关出版、印刷史的专著和资料,使我逐渐认识到我国学界对书坊研究的薄弱性。因此,古代书坊研究,就成了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内容。不幸的是,恩师潘树广先生于2003年6月已仙逝,使我失去了一位慈父般的恩师。每想起恩师的教诲,我不敢有半点懈怠,为此,将论文重新修改并出版,以告慰于恩师。
本书对书坊的研究仅为初涉其源,梳理其流,论述其中,略存己见,故尚多有不足之处,以待方家、同仁乃至读者的批评,使书坊研究得以推进。
戚福康记于苏州葑谊陋室
2005年10月1日